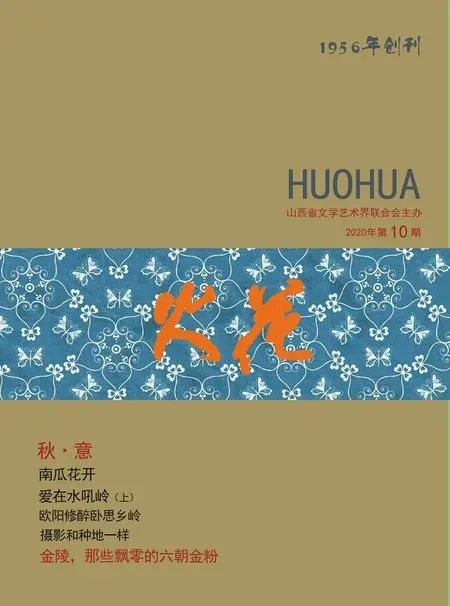金陵,那些飄零的六朝金粉
許宇杭
素有“六朝古都”“十朝都會”之譽的南京,彌漫著一股幽深的歷史云煙。我徜徉在古都幽靜的角落,尋覓蜷縮在那個舊籍故紙中的背影,揀拾那些飄零的六朝金粉,一瞥曾經驚鴻的絢麗。
煙雨雞鳴寺
煙雨飄渺中的雞鳴寺,飄溢著一縷幽幽的古香禪意。雨中造訪,游人寥寥,遠離了往日的喧囂浮躁,一切都是那樣的清凈安逸。我輕輕地邁進寺院,尋訪千年前杜牧妙手營造的詩意畫境。
細細的雨絲,如同編織了一件空靈的輕紗,披蓋在禪寺身上,愈發顯得空蒙靈動。細雨輕斜,風鈴微顫,那首流傳了千年的《江南春》絕句,頓時襲上心頭: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
我想,那也是一個“江雨霏霏江草齊”的時節,那個“千首詩輕萬戶侯”的小杜,一襲青衣,從夜泊秦淮“隔江猶唱后庭花”的踏歌聲中,飄然而至,一聲悠然詠嘆,將南朝風云變幻定格在江南的煙雨畫卷之中。
“南朝四百八十寺”,小杜的詩句極言南朝古寺之多,然而,南朝佛寺遠遠不止這些,“四百八十寺”,只不過是南朝京城的佛寺數目。據《南史·郭祖深傳》記載,蕭梁時期僅京城建康(今南京)就有“佛寺五百余所,窮極宏麗;僧尼十余萬,資產豐沃”。而蕭梁所在郡縣,全部佛寺更是多達2846所,雞鳴寺則是其中最有盛名的一座。
“雞籠山下,帝子臺城,振起景陽樓故址;玄武湖邊,胭脂古井,依然同泰寺舊觀。”雞鳴寺中的一副對聯,道出了寺院的前世今生。位于南京雞籠山東麓的雞鳴寺,是南京最古老的梵剎之一。它的前身是南朝“皇帝菩薩”梁武帝興建的“同泰寺”。明朝朱元璋改“雞籠山”為“雞鳴山”,于是寺隨山名,稱為“雞鳴寺”。由于時代久遠,它曾經的輝煌已被湮沒,只能從舊籍故紙中去尋覓。
建造此寺的梁武帝,無疑是中國歷史上最篤信佛教的帝王,在位時廣建佛寺。為方便自己吃齋念佛,他在臺城(皇宮)一路之隔的地方,修建了同泰寺。整個寺院依皇家規制而建,規模宏大,殿堂壯麗,盛極一時,成為當時南朝的佛教中心,素有“南朝四百八十寺”首剎之譽。
宏偉壯麗的同泰寺建成后,梁武帝特意在宮后開了一門,直通寺院南門。“吱溜”一聲,他出宮門即入寺門,真是方便極了。
梁武帝是位知識淵博的學者型皇帝。他口若懸河,經常到寺里說法講經,講得活靈活現,聽眾逾萬。曾先后四次舍身到同泰寺為僧,脫下皇帝的龍冠莽袍,穿上僧衣,在寺中過起普通僧人生活。他“舍身”時,便房瓦器,素床葛帳,獨對青燈古佛,“刺血經書,坐禪不食”,禮佛真正達到了“無我”境界。但他又是一個勤奮的皇帝,即使在寺院里當和尚,依然勤于政務,孜孜不怠,四更即起,便對著燭光批閱奏章。這位皇帝每逢禮佛,都身著“乾陀袈裟”,連他的臣子上表奏章亦稱其為“皇帝菩薩”。
一次次的“舍身”,就有一次次的“贖身”。每次贖身,“于是內外百官共斂珍寶而贖之”,贖價高達“錢一億萬”。自然這些贖金都是百官向老百姓搜刮而來的。
如此篤佛,菩薩并沒能保佑他。就在梁武帝最后一次從同泰寺贖身的當天夜晚,寺里突發火災,燒毀了宏偉佛塔。在新建佛塔還沒有完工時,他就被侯景拘禁餓死在臺城,上西天去見他的老佛爺了。
如今“南朝四百八十寺”之首的雞鳴寺,遠沒有南朝鼎盛時的規模。它飽經滄桑,屢毀屢建,成了從南朝風雨中一路走來的歷史遺物,早已融入美麗江南的水墨畫中。
登上景陽樓遠眺,煙雨中依稀可見一段破敗的宮墻,殘留在那里,如一聲幽嘆,穿越時空,彌久不散。那里曾經是富麗堂皇的臺城,如今瓦礫成灰,舊跡難以辨認。“無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煙籠十里堤”,臺城就這樣靜靜地佇立在煙雨之中,聽一夜春雨,看十里煙籠。
寂寞烏衣巷
高聳的石坊,阻隔了夫子廟人流如潮的熱鬧,狹窄的烏衣巷顯得格外靜寂。一抹殘陽安謐地映照在馬頭墻上,灑下一地斑駁的滄桑。
造訪烏衣巷,是在一個夕陽西下的傍晚,正應了“烏衣巷口夕陽斜”的詩境。那年在南京,逛了一下午的夫子廟,正欲離去,跨過秦淮河上的文德橋,往西南走上幾步,抬頭便見高大的“烏衣巷”石坊。
知道烏衣巷,是幼時讀過的唐代“詩豪”劉禹錫《烏衣巷》詩:“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如今的烏衣巷,只剩下350米長,倘若不是這首流傳千古的絕句,恐怕早已湮滅在歷史風雨之中。
烏衣巷原為“烏衣營”,是三國時期吳國都城建業(今南京)守城部隊的兵營所在地,當時守城將士都穿著黑色的衣服,當地人便稱此地為“烏衣營”。東晉南渡后,定都建康(今南京),烏衣營舊址又成了高門士族的聚居區。東晉兩大“擎天之柱”王導、謝安的府第,就建在此地。巷內高第華宅,鱗次櫛比,進進出出的高門士子,為了彰顯門第,個個峨冠博帶,黑衣華服,一時風流倜儻,招搖過市,號為“烏衣郎”,他們居住的巷子自然也成了“烏衣巷”。
遙想當年,烏衣巷內車水馬龍,絲弦繚繞,多少達官貴人出入此巷,多少富麗堂皇的府第鶴立其中。這里有東晉開國元勛王導輔助三朝、推行“僑寄法”的相府,有“東山再起”后的謝安談笑風生指揮淝水之戰的中樞,有“書圣”王羲之坦腹東床的舊所。
如今巷子的中段,建有王導謝安紀念館。館前一副楹聯:“歸燕幾番來作客,鳴箏何處伴隨云。”正是點化劉禹錫詩意而成。“舊時王謝”,顯赫一時。“王與馬,共天下”,東晉南渡后,王導輔佐司馬睿創立了延續百年的東晉王朝。謝安“談笑間”指揮淝水之戰,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打敗了“投鞭斷流”的前秦符堅百萬大軍,成為古代軍事史上以少勝多的典型戰例,也使流落到南方代表漢族中原文化的東晉政權得以延續和發展。
千古風流人物,當推六朝王謝家族。“王家書法謝家詩”,王謝家族人才輩出,俊采星馳,各領風騷。王導家族,王羲之、王獻之、王珣“三王”書法登峰造極,無與倫比,尤其書圣王羲之,是一代書法的集大成者,《蘭亭序》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謝安家族,謝靈運、謝惠連、謝朓“三謝”詩文珠璣錦繡,風流醞藉,特別是“吐語天拔,出于自然”的謝靈運詩歌,開創一代詩風,尊為山水詩派的鼻祖。在中國歷史上,恐怕難以找出像王謝家族這樣在大富大貴中依然能將中國文化玩出極致的家族。
巷子盡頭處,殘存一口六朝時期的古井,這也許是烏衣巷唯一幸存的古跡。沒有了“舊時王謝”,也沒有了“尋常百姓”,那口古井只是默默地藏在小巷深處,日復一日地等待筑巢歸棲的燕子。井圈上的道道繩跡劃痕,猶如一位飽經風霜的殘燭老人,無聲地訴說滄桑變幻的身世,孤寂地追思逝去的韶華歲月。千年的時光流轉,只留下了那一道道世事沉浮的痕跡。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如今的烏衣巷,沒有了六朝金粉的那份靡麗繁華,也沒有了魏晉風度的那份仙風道骨。當年王謝的豪華府第,連同堂前飛入的春燕,都成了歷史煙云,只留下一個“烏衣巷”的名字,孤寂地佇立在夕陽之中,凝望著流光溢彩的秦淮河。
落日的余暉,鋪滿了巷外粼粼的秦淮河水。在漿聲燈影的秦淮河畔,一條寂寞的巷子,一條光滑的青石板,不知藏匿了多少故事,也不知隱含了多少歷史。
風月秦淮河
月光溶溶,水波搖拂,站立船頭,我隱約聽到縷縷歌聲從樓榭中飄來,夾著微風與槳聲的私語。十里秦淮,六朝金粉,沉迷在槳聲燈影的粼粼波光中。千百年的歷史風云,幻化成一縷淡淡的煙靄,散逸在亦夢亦幻的夜色之中。
秦淮河靜靜地流淌,畫舫悠悠地游弋。入夜的秦淮河,燈光璀璨,霓虹閃爍。粉墻黛瓦的“秦淮人家”照壁上,一串串紅紅的燈籠垂掛而下,宛如燈光畫幕上流淌著一顆顆璀璨的明珠。大大小小的船舫亮起了燈火,在微風拂漾的漣漪中,泛著朦朧的光彩燈影。倏忽間,我從槳聲燈影中,恍惚看見那畫舫凌波的歷史畫卷。
也許就是這樣一個夜晚,月朗星稀,秦淮河籠罩在一層朦朧的煙靄中,彌漫著一種淡淡的惆悵與寂寞。一葉扁舟,一襲青衣,風流倜儻的杜牧從“十年一覺揚州夢”中醒來,在船槳的欸乃聲中,夜泊秦淮,淺斟低吟: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
闌珊的燈火映照在秦淮河上,輕蕩起粼粼波光。欸乃槳聲劃過的柔波漾在船尾,波光隨著畫舫的游動時而閃爍時而跳躍。槳聲燈影中的秦淮河,如一簾幽夢,朦朧纏綿;似十里煙籠,迷離恍惚。
銀輝瀉灑,光暈交融,酒肆茶樓的杏簾飄拂依然,槳聲燈影的脂粉濃艷依然。絲竹悠悠,衣袂飄飄,多少達官貴人、才子佳麗從塵封的歷史中穿越回來,在秦淮河畔演繹了一曲曲風花雪月。
陳后主“玉樹流光照后庭”的沉迷,李后主“一江春水向東流”的悲嘆,六朝如夢,一曲靡音,昔日繁華頓作隨風而去的云煙,歷史的殘卷總是讓人廢書長嘆。
畫舫樓臺水榭,六朝金粉秦淮。秦淮河原名淮水,相傳秦始皇東巡認為此地有“王氣”,便下令“鑿方山,斷長垅為瀆”,引入長江以破之,后代根據此傳說,改稱為“秦淮”。六朝時,秦淮兩岸一直是名門望族聚居之地,明清兩代因設有貢院與教坊,更是繁華至極,可謂綺窗絲幛,十里珠簾,燈船之盛,甲于天下。
是六朝粉黛的胭脂豐盈了秦淮河的香柔,還是八艷絕代的風華豐滿了秦淮河的神韻?李香君血濺桃花扇的堅貞,柳如是怒斥“水太涼”的骨氣,使溫柔如水的秦淮多了一種血氣方剛。佳人已逝,古韻猶存,唯有秦淮悠悠流淌。
畫舫悠然地穿過“桃葉復桃葉”的桃葉渡,從東水關掉頭又回到了觀賞“秦淮分月”的文德橋。文德橋將秦淮河與夫子廟相連,試想古時,一邊是步入貢院博取功名的謙謙君子,一邊是墜入青樓倚門賣笑的風塵女子。在風塵與風雅的掙扎中,多少道貌岸然的君子,抖落塵世浮名,換作溫柔夢鄉。
千年流淌的秦淮河水,早已洗盡了歷史的鉛華。那些曾經彌漫在秦淮河邊的脂粉艷香,只好纏綿在唐詩宋詞中淺唱。清風明月,燈火璀璨,臨水的歌舫,有人撫弦輕唱,猶如當年小杜隔江猶聽商女輕唱后庭花一般。
夜色朦朦,弦音戚戚,河畔迷離的燈光,閃爍著歷史歲月的風華。“只留一井屬君主”的胭脂井,“桃花扇底送南朝”的媚香樓,“隔江猶唱后庭花”的商女,還是烏衣巷中“飛入尋常百姓家”的春燕,構成了一幅時空交錯的畫卷,供后人覓蹤憑吊,發思古之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