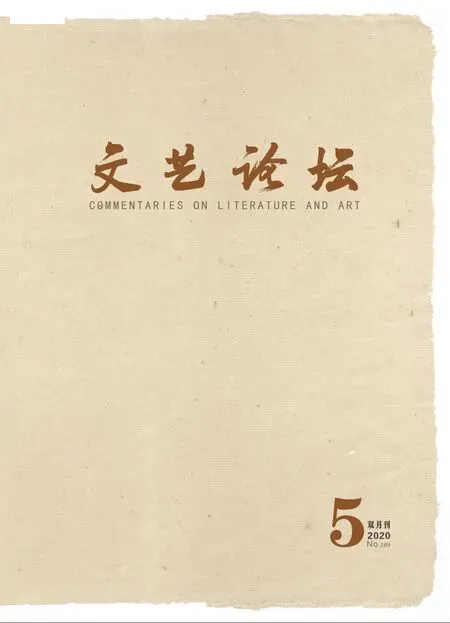重復與上升:男頻小說的結構
◎ 賈 想
一、頻道劃分與結構固化
網絡小說很早就完成了“看人下菜碟”的任務,將小說這一中性的、雌雄同體的文學體裁,劈成兩個頻道,分成了男頻小說和女頻小說。嚴格來說,這種一刀切的分類學不是藝術規律支配的結果。藝術恰恰致力于彌合天與地的分裂,溝通黑夜與白天,混淆男性與女性。藝術家是不同事物乃至敵對事物之間的通靈者,借助想象力與審美感性,抵抗著世間萬物分散的大勢。
這種分類學遵循的是市場的規律。市場經濟的大手伸入文學領域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將混沌的文學作品重新分類、整理、碼放、貼上標簽。分類的標準,并不是藝術價值的高下,而是作品所能滿足的讀者需求的不同,首先就是男性讀者和女性讀者需求的不同。由此,文學進入了“需求—供給”的消費邏輯。麥克盧漢曾分析美國電視工業時代的消費兩極化:男人喜歡西部片,女人喜歡肥皂劇。男頻小說與女頻小說的分類,正是同理。
需求的細化帶來商品的細化,商品的細化帶來職業分工的細化,分工的細化帶來工種、技術的固化。網絡小說界也是如此,男頻小說家不會輕易“換頻道”寫女頻,女頻小說家也不會同時涉足男頻。這兩撥人,一撥專注為男性讀者生產“文化蛋白粉”,一撥專注為女性讀者生產“文化甜品”,井水不犯河水。分工的固定,久而久之,帶來了敘事模式的固化。男頻小說已經形成了一套非常穩固乃至僵化的結構學。研究者對此進行了一些零散的描述,譬如“瀕死重生”“屌絲逆襲”“升級打怪”“一路開掛”,等等。總結起來,男頻小說的結構呈現出兩個典型特征:局部重復,總體上升。
二、重復與冒險
重復,是理解包含男頻小說在內的通俗小說的鑰匙。在具體的故事中,重復表現為某些“情節鏈”的反復出現。比如經典化了的通俗小說《西游記》中,“唐僧被抓—孫悟空搬救兵”的情節鏈,《鬼吹燈》系列中,“遇險—意外落入古墓—盜墓取寶—逃出生天”的情節鏈。更有《慶余年》《我真沒想重生啊》這樣的“重生文”,直接將“暴死—重生”這個巨型情節鏈,當作小說的基本結構。這些情節鏈經過進一步抽象,可以提煉為“輸—贏”“失—得”“散—聚”這樣的二元結構。一部通俗小說的結構,正是由一個或多個二元結構在局部反復擺列,最后連綴而成。
這二元結構在局部的重復,根本上看,都是“有”與“無”的重復。需注意的是,通俗小說中的重復,是有嚴格的順序要求的:一定是按照由匱乏到滿足、由更高的匱乏到更高的滿足這樣不可逆的順序。一定是從“無”到“有”的重復,而不是從“有”到“無”的重復。“無”是起點,“有”是終點。小說總是從一無所有的匱乏狀態開始,到功成名就、終成眷屬結束。所謂“始多乖違,終多如意”,因為,從“無”到“有”,這是“生”,而從“有”到“無”,這是“滅”。
“輸—贏”“失—得”“散—聚”,無一例外都是在強調“生”的在場、“滅”的不在場,“生”的必然、“滅”的偶然,以此構造“不死”的幻覺。閱讀通俗小說的時候,我們像被注射了嗎啡,暫時遺忘了時間的流逝,現實的煩惱,以及人一定會死這個恐怖片一般的情節。內心得以鎮定,“死亡焦慮”也被緩解了。而屢試不爽的重復,正是鎮痛機制。
重復就是不死不滅。我們為什么熱愛重復呢?首先,與我們“好生”的文化傳統有關。傳統儒家的教育,講求“好生之德”,要“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遠之”。總之,過度重視“生”的教育,排斥“滅”的教育,導致我們的文化基因中,缺乏對于“滅”的免疫。今天,唯物主義教育和國學的復興,更是將“滅”的恐怖性激發了出來,國民對重復的心理需求非常旺盛。其次,與心理層面的“安全需要”(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 相關。我們的心里判定熟悉物是安全的,陌生物是不安全的。我們的本能要求我們將陌生物轉換為熟悉物,而轉換的方法,就是重復。當我們看到故事情節不斷重復時,我們內心會漸漸放松警惕,產生愉悅感和安全感。重復首先通向的是安全感,然后才是厭倦感。網絡小說結構的重復,徘徊在安全感(吸引力) 和厭倦感之間。優秀的網文作家總在絞盡腦汁,想在重復的同時求新,以免故事過早滑向厭倦。
重復的反面,是冒險。重復的任務,是將遇見的每一個陌生經驗熟悉化,成為可控、可靠、安全的經驗。冒險的任務,是保持每一個陌生經驗的“初體驗”,保持經驗的新奇性、神秘性、危險性。重復帶來的是倫理學的安穩;冒險帶來的是美學的刺激。在倫理學高于美學、“美”“善”高于“真”的時代,西方的文學作品總在實踐重復的藝術。18 世紀,《小癩子》《魯濱遜漂流記》誕生之后,故事的內容變成了一個普通人肉體與精神的“雙重冒險”。從此之后,冒險代替重復,成為了“小說”(Novel) 的使命。小說身上的美學潛能被釋放了,此后逐步精英化、正典化,成為了文學史的主要文體。
在今天,重復和冒險,可作為劃分通俗小說和精英小說的一個粗略標準。通俗小說,基本都是以重復為主旨的故事。精英小說,基本都是以冒險為主旨的故事。長篇故事,通常離不開重復;短篇故事,往往更適合冒險。然而,“危險的事固然美麗/不如看她騎馬歸來”。當文學一心潛入美學冒險當中,就會不可避免地失去讀者。所以在具體的文學實踐中,通俗小說和精英小說總會互相學習對方的長處。《西游記》《水滸傳》這樣的古典名著,《傲慢與偏見》《紅與黑》這些西方名著,《冰與火之歌》《哈利·波特》這些當代故事,都是重復的藝術和冒險的藝術聯姻后誕下的子嗣。
三、上升與下降
男頻小說中,局部從“無”到“有”的重復,如攀爬階梯,最終形成了整體結構的“上升”趨勢。比如,財富或寶物的從“少”到“多”,武力的從“弱”到“強”,技能的從“低”到“高”。即便有財富的虧損、寶物的丟失、武力的削弱、技能的喪失,也一定是暫時性的,為之后的重振雄風做鋪墊。總之,全部情節被一個設計精密的“升級機制”所統攝。
“升級機制”是男頻小說的靈魂,包含三個基本原則:第一,不死(重生) 原則,表現為主角絕處逢生甚至死而復生,主角一定要活到大結局,這是鐵律;第二,進化原則,主角一定要從弱到強,從量變到質變,不斷進化,最后成為某個領域的世界第一;第三,等級壓制原則,主角遇到的對手,一定比自己等級更高,在寶物、武力、技能上壓自己一頭,以便激起主角超越的野心與進化的主觀能動性。最受歡迎的男頻小說,像《斗羅大陸》 與《全球高武》這樣的“修仙文”,一定具備最完善的“升級機制”。男頻小說的“爽”,正是依賴這個“升級機制”。
不止今人,古人也喜歡升級的人生。《枕中記》中盧生的“黃粱一夢”,《金瓶梅》中西門慶的前半生,就屬于古代的男頻故事。不同處在于,古人有“色空”的思想,有哲學和倫理學的顧慮。因此,寫“夢中”之色相,也寫“夢醒”之空相。讓盧生睡著的時候享受,也讓他醒來的時候難受;讓西門慶登上歡愉的頂峰,又在歡愉的頂峰跌個粉身碎骨。從而,對人不斷膨脹的欲望,起到中止、勸誡、消解的效果。網絡小說可不會自找沒趣,何況也沒有哲學和倫理學的顧慮。所以,男頻小說一定只寫“夢中”,不寫“夢醒”。古典文學一定要設置一個“夢醒時分”,意味著欲望無限膨脹,在古代文化中是不合法的。相反,今天的網絡小說取消“夢醒時分”,說明欲望的滿足在今天的文化語境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肯定。在消費社會中,欲望是第一生產力。
局部重復與總體上升,制造了“積累的神話”。改革開放之后,我們不再制造“平等的神話”,而是要讓“少數人先富起來”,開始制造“積累的神話”。“積累的神話”,是國力上升期家國敘事的要求,也是上升期國民的潛意識需求。網絡小說積極地參與了這一敘事。
正如重復對應著冒險,上升則對應著下降。局部冒險、總體下降,往往是精英文學的結構。精英文學顛倒了通俗文學從“無”到“有”的基本情節單位,轉而寫從“有”到“無”,也即從“生”到“滅”,自“色”入“空”。《紅樓夢》將這個道理,表述為從“好”到“了”的辯證法。財富一點點減少(家道中落),親人一個個離散(妻離子散),容顏一天天衰老(美人遲暮),地位日漸下降(英雄氣短),生命逐步熄滅(人生向晚) ……這個不斷下降的過程,是積累的反面,是一個“耗散的悲劇”。
通俗文學,否定“無”,否定“散”,否定“衰朽”。因為在成功學和倫理學看來,耗散是一種失敗,是否定性的。這是一種“生”本能驅使的文學觀。精英文學不然。精英文學的世界觀,是一種熱力學的世界觀:能量總在從高溫向低溫轉移,分子總在從有序態向混亂態變化,世界的“熵”(耗散) 總在增加。精英文學承認世界的“熵增定律”。
在承認“無”“散”“衰朽”是一種真理的同時,精英文學又通過美學的眼睛,發現了“無”“散”“衰朽”的意義,從而將耗散的否定性價值,逆轉為肯定性價值。經典如《情人》的開頭:“我已經老了,有一天在一處公共場所的大廳里,有一個男人向我走來,他主動介紹自己,他對我說:‘我認識你,我永遠記得你,那時候你還很年輕,人人都說你美,現在我是特來告訴你,對我來說,我覺得現在你比年輕的時候更美,那時你是年輕女人,與你那時的面貌相比,我更愛你現在備受摧殘的面容’。”通過一個男人美學的眼睛,“衰朽”被拯救了。再如余華的《活著》,家道中落、妻離子散、人生向晚,人生所有重大的耗散,都被福貴經歷了。從成功學和倫理學看來,福貴如此不幸。但余華給予了福貴一種涉及愛、忍受、懺悔的姿態,這個姿態,讓福貴超越了世俗的不幸,步入了一種高尚得類似宗教的幸福。
蘭陵笑笑生和曹雪芹更是深諳此種真義。他們只是寫到了“色即是空”就停下,不去寫“空即是色”;只寫到“食盡鳥投林”的停止與耗散,不去寫“飛入尋常百姓家”的轉換與積累。也許,這就是精英文學的邊緣,不能跨過去——像通俗文學那樣——超越熵增定律,享有新的輪回、新的累積、新的循環,那會立即迎來美的死期。
但是,從出現的那一刻起,小說承擔世俗欲望的任務,就先于承擔美的任務。在美的灰燼中,盛開的將是一個比現實更完美的白日夢世界。那里,有“千金散盡還復來”,有“春風得意馬蹄疾”。那里,英雄不會失敗,美人不會老去,親人不會失散,戀人不會分離。在上升的空中階梯上,滿是攀登的人。過去如此,此時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