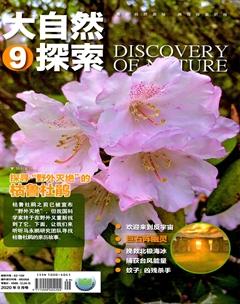蚊子:兇殘殺手
吳青

我們正在與蚊子交戰。除了南極洲、冰島和為數不多的法屬波利尼西亞小島是例外,由110萬億只蚊子組成的大軍在地球表面其他每一寸土地上巡邏。咬人的雌蚊裝備著至少15種讓人痛不欲生的致命生物“武器”。雖然全球每年的防蚊花費高達110億美元,且還在猛漲,但收效看來并不大——盡管蚊子致死人數(尤其是瘧疾致死人數)逐年減少,蚊子對人類來說卻依然是致命的殺手。
年均殺人200萬
根據多種估計,自2000年以來蚊子平均每年造成200萬人死亡。按照年均數來說,這方面的第二名是人類,其自相殘殺致死人數為47.5萬。第三名是蛇,致死人數5萬。狗和白蛉并列第四,致死人數均為2.5萬。采采蠅和獵蝽并列第五,致死人數均為1萬。鱷魚位列第十,致死人數為1000。其后是河馬、大象和獅子,致死人數分別為500、100和100。鯊魚和狼并列第十五,致死人數均為10。
但蚊子并非直接傷人,而是它傳播的致命疾病在害人。如果沒有蚊子,這些惡疾可能就不會被傳染給人類,甚至這些惡疾都不會存在。我們的免疫系統很能適應我們所長期生活的環境,卻不能立即適應異域。行進的軍隊、探險者和殖民者把疾病帶到遙遠的土地,但他們也被由自己企圖征服之地的蚊子所攜帶的微生物奪命。從某種意義上說,蚊子是推動人類歷史的最大非人類力量。

采采蠅

獵蝽
蚊子愛叮哪些人
蚊子的嗡嗡聲是我們最熟悉的聲音之一。野營一天后,你和親朋洗完澡,躺在草坪椅子上,打開冰鎮啤酒。正當你們準備開懷暢飲時,卻傳來蚊子的嗡嗡聲。此時近黃昏,也是蚊子最喜歡的吸血時間。
雖然你聽見了嗡嗡聲,知道蚊子駕到,但察覺不到它在你腳踝上輕輕降落。為什么是腳踝?蚊子叮咬部位通常接近地面,而且只有雌蚊才咬人。蚊子用10秒鐘尋找一根主要血管,然后帶著頭部的6根“針”聚焦和接近目標。它把其中兩根“針”(兩塊鋸齒狀下頜骨切削刀片,它們很像是兩張刀片來回移動的電動刻刀)插入(或者說鋸進)你的皮膚,并且用另外兩根“針”(兩根牽引器)為第5根“針”——吸管(從蚊子的保護性翅鞘中伸出的“皮下注射器”)開辟通道。它用吸管吸血3~5毫克,立即排泄血液中的水分,濃縮占血液20%的蛋白質。在此過程中,它用第6根“針”把包含抗凝血劑的唾液注入吸血部位,阻止血液凝固。這會縮短它的吸血時間,從而降低你感覺到它正在吸你血的風險。這種抗凝血劑引起過敏反應,產生發癢的瘡包。
蚊子叮咬是蚊子生殖所需的一種復雜而創新的進食方式——雌蚊需要人血來讓它的卵子生長和成熟。不要以為蚊子專咬某些人,事實上它什么人都咬。民間一直有這樣的說法:女性愛“招”蚊子;小孩容易被蚊咬;皮膚黑的人不容易遭蚊咬……其實,這些說法都不對。不過,蚊子咬某些人確實要多一些。例如,據一些統計,O型血者被蚊子咬的次數是A型血者的兩倍,B型血者居于前兩者之間。皮膚中某些化合物(尤其是乳酸)天然含量更高者看來更受蚊子青睞。蚊子能根據這些化合物含量分析你的血型,而這些化合物也決定著一個人的皮膚細菌和獨特的身體氣味。如果你體味酸臭,會讓人不悅,卻會增加你皮膚表面的細菌數量,這會讓蚊子不喜歡你。但腳臭是個例外——臭腳所釋放的細菌對蚊子來說是催情劑。此外,蚊子也被除臭劑、香水、肥皂和其他香料的氣味吸引。

雌蚊用6根針狀口器叮咬人。其中,藍色針和黃色針用于鋸進人皮膚,綠色針用于把蚊子的唾液注射進人皮膚,紅色針用于吸血。

滿天的蚊子。
蚊子特別喜歡愛喝啤酒的人。著裝太靚麗也不好,因為蚊子靠視覺和嗅覺獵食。蚊子的嗅覺主要依賴潛在襲擊目標呼出的二氧化碳數量,因此激動、發怒只會招來更多蚊子。蚊子在60米外就能聞到人呼出的二氧化碳。你鍛煉時會呼出更多二氧化碳,而出汗會釋放乳酸等化合物,因此你被蚊子關注。此外,你的體溫升高也使蚊子更能選中你。由于孕婦呼出的二氧化碳數量比一般人高20%,孕婦體溫也更高,因此孕婦遭蚊咬的次數是一般人的兩倍,孕婦感染寨卡病毒病和瘧疾等蚊媒疾病的風險也比一般人高。
雄蚊不叮人。它們的世界只有兩件大事:采花蜜和繁殖。與其他飛行昆蟲一樣,當準備繁殖時,雄蚊在煙囪、天線、樹木或人群周圍聚集成群。當我們走動時,蚊群尾隨不散,讓人甚為煩惱。蚊群甚至能延伸超過300米高度,就像龍卷風的漏斗云。當雄蚊聚集在你頭頂上方時,雌蚊飛進雄蚊群中尋找配偶。雖然雄蚊在一生中頻繁交配,但交配一次的精子數量就足夠雌蚊產生一大批后代。雌蚊存儲精子,把它們逐個分配給每一個卵子授精。雌蚊的短暫激情為生殖提供了兩個基本要素之一,而另一個要素就是你的血液。
反復叮人和產卵
回到營地,你剛剛完成了耗費體力的徒步旅行,在身上抹香皂洗澡,擦干身子后噴上香體液,然后穿上紅藍色沙灘裝。此時近黃昏,瘧蚊的晚餐時間。雌蚊在與雄蚊交配后,吸了你的血帶走。這些血的重量是雌蚊體重的3倍。它在最近處找到一個垂直表面,在重力幫助下繼續排掉你血液中的水。采用濃縮血液,它將在未來幾天里讓卵子發育。然后,它把大約200只卵產到小水坑表面。說是小水坑,可能只不過是在一只被踩扁的啤酒罐表面的積水。雌蚊總是把卵產在水中,但它無需多少水。
在1~3周的生命期里,雌蚊反復叮人和產卵。雖然它最遠能飛到3000米以外,但它實際上很少飛到自己出生地周圍400米以外。如果溫度夠高,兩到三天內蚊卵就會孵化為在水中扭動、覓食的幼蟲(孑孓)。如果溫度不夠,這個時間就會長一些。幼蟲很快變成上下顛倒、逗號形狀、身體歪斜的毛蟲。毛蟲通過從露出水面的臀部伸出的兩個呼吸角呼吸。幾天后,幼蟲的保護性體殼裂開,成年蚊子飛出,新一代“魔鬼”雌蚊已準備好叮人。蚊子的成熟過程只需大約1周。

白紋伊蚊(亞洲虎蚊)的幼蟲。
病原體為什么殺人
蚊子所攜帶的細菌、病毒和寄生蟲等病原體引發了無數災難,主導著人類歷史進程。為什么這些病原體會進化到消滅宿主——人的地步?如果我們暫時拋開偏見,就會發現這些病原體與人類一樣經歷了自然選擇過程。這就是它們至今會讓我們生病、死亡和它們難以被清除的原因。你可能會困惑:既然人類是這些病原體的宿主,也就是說人類為病原體提供了“寄宿”,那么為什么病原體要殺死自己的宿主?沒錯,病原體致病會致人死亡,但病原體利用疾病癥狀來幫助自己傳播和繁殖。如此看來,病原體真的很狡猾。一般而言,病原體在殺死宿主前會確保自己的傳播與復制。包括導致我們食物中毒的沙門氏菌在內的一些微生物和多種寄生蟲都在等待自己被吞噬——也就是一種生物吃另一種生物。

瘧原蟲(黃色)破壞紅血球(示意圖)。
有很多水生傳播疾病,其中包括賈第蟲病、霍亂、傷寒、痢疾和肝炎。包括普通感冒、24小時流感和真流感在內的其他多種疾病通過咳嗽和打噴嚏傳染。天花之類的疾病通過傷口、受污染物體或咳嗽直接或間接傳播。還有一些疾病通過性行為傳播,其中許多惡毒病原體在孕婦子宮內傳給胎兒。
導致斑疹傷寒癥、黑死病(淋巴腺鼠疫)、南美錐蟲病和嗜眠病(錐體蟲病)的微生物,搭載的是由帶菌者(傳播疾病的生物體,例如虱子、白蟻、蠅、扁虱和蚊子)提供的“免費便車”。為了讓自己的生存概率最高,許多微生物使用多重手段。疾病的多種癥狀其實是微生物傳播疾病的多種模式,這些模式有效地幫助微生物繁殖和其物種存在。微生物為自己的生存而戰,和我們為自己的生存而戰沒有兩樣。微生物在進化節奏上領先我們一步,因為它們持續變形以繞開我們企圖借以清除它們的最好手段。
適應環境的高手
為了了解蚊子對人類歷史的深遠影響,首先有必要認識蚊子自身和蚊子傳播的疾病(蚊媒疾病)。有一個被錯誤歸于達爾文的說法:“存活下來的并不是最強壯者,也不是最聰明者,而是最能適應變化者。”不管這句話到底是誰說的,蚊子和蚊媒疾病(尤其是瘧疾寄生蟲病)都是這句話的最好例子。蚊子是進化性適應高手,它們在幾代之內就能適應變化的環境。在1940~1941年德國閃電戰期間,隨著德軍轟炸倫敦,一些孤立的庫蚊種群與倫敦市民一起被隔離在倫敦地下防空洞中。這些蚊子很快就從原來吸鳥血變成了吸食老鼠血和人血。現在,它們已經是明顯有別于其地面祖先的另一個蚊種。就這樣,原本需要花成千上萬年才能完成的進化,竟然在不到100年內就完成了。
蚊子不僅有奇跡般的適應能力,而且非常“自戀”。與其他昆蟲不同,蚊子不會在任何有用的意義上為植物授粉,不會讓空氣進入土壤,也不會消化廢物。與大眾認識相反,蚊子根本不構成其他任何動物不可或缺的食物來源。除了延續自己的種類,還或許除了殺人之外,蚊子沒有其他生存目的。作為頂級掠食者,蚊子與人類的關系看來只在于蚊子要“控制人口失控性增長”。

倫敦地下庫蚊。
兩種惡毒的蚊媒疾病
在整個人類歷史中,蚊子傳播的兩種惡疾——瘧疾和黃熱病一直是死亡和歷史變化的主要推手。人在被攜帶瘧原蟲的蚊子叮咬后,罪大惡極的瘧原蟲會在被感染者肝臟內變異、繁殖長達一兩周,在此期間不會導致任何癥狀。然后,變異過的瘧原蟲大軍從肝臟暴發而出,侵犯血液。它們附著在紅血球上,穿透紅血球的外層防御,大啖紅血球內部的血紅蛋白。瘧原蟲在紅血球內會經過另一次變形和繁殖周期。脹滿的紅血球最終爆裂,噴射出兩種形式的瘧原蟲。其中原來形式的瘧原蟲前去進犯新鮮紅血球,新的“無性”形式的瘧原蟲漂浮在血流中,等待蚊子傳播。
瘧原蟲是變形專家,正是它的這種基因靈活性導致我們難以用藥物或疫苗清除或抑制它。被感染者至此已嚴重發病,先是發冷,然后是41℃的高燒。患者不得不臥病在床,汗濕床單,扭曲痙攣,賭咒發誓,痛苦呻吟,肝脾腫大,皮膚發黃,嘔吐不止。隨著紅血球每一次爆裂,瘧原蟲從紅血球中暴發而出,患者都會以精確時間間隔發燒。隨著瘧原蟲在新的紅血球內進食和繁殖,退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