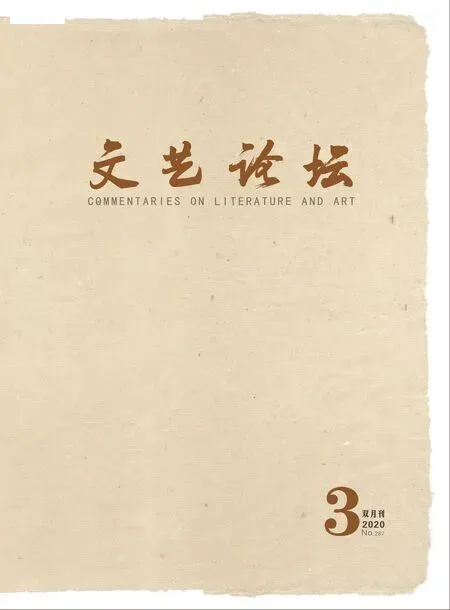在認同與規避之間
——論茅盾《子夜》對左拉《盧貢·馬加爾家族》的借鑒與改寫
◎ 龍其林
1933 年1 月,開明書店出版了茅盾的長篇家族小說《子夜》。作品剛一出版,即引起了各方關注,小說3 個月內就印刷4 版,成為當時具有轟動效應的作品。瞿秋白曾充滿激情地贊揚這部小說,認為“這是中國第一部寫實主義的成功的長篇小說”,“一九三三年在將來的文學史上,沒有疑問地要記錄《子夜》的出版”。吳宓撰文也對這部小說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認為“吾人所為最激賞此書者,第一,以此書乃作者著作中結構最佳之書。蓋作者善于表現現代中國之動搖,久為吾人所知。其最初得名之‘三部曲’即此類也。其靈思佳語,誠復動人,顧猶有結構零碎之憾”,“此書則較之大見進步,而表現時代動搖之力,尤為深刻。”而在之后的各種文學史著作中,茅盾及其《子夜》也獲得了高度的評價:“他是徹底改變‘五四’中長篇小說的幼稚狀態,使之走向完善的最突出的小說家”,“《子夜》對洋場都會的色彩和聲浪的捕捉,以及它對實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在交易所角逐的出色描繪,是同代作家未能企及,后代作家難以重復的”。
《子夜》在中國獲得的巨大成功和轟動效應,也使得這部作品被翻譯成多國文字介紹到德、日等國。1938 年,德國的弗朗茨·庫恩在其翻譯的《子夜》前言中寫下了這么一段耐人尋味的話:“《子夜》在中國引起了人們極大的注意,并很快一再重版。它非同尋常地向我們顯示,在今天的中國,東西方文化之間的融合過程是進展到了何種程度。就是由于這一理由,促使我把它譯為德文。”庫恩所言東西方文化之間的融合語焉不詳,并未說明這部小說受到了西方哪位作家的作品影響,但人們通常都傾向于將此“西方”理解為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在一些研究者看來,《子夜》更多地表現出對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的借鑒,而左拉的《盧貢·馬加爾家族》似乎并無多少影響。
一、從認同到規避:茅盾之于左拉
1921 年下半年,茅盾在《評四五六月的創作》一文中旗幟鮮明地倡導自然主義:“對于現今創作壇的條陳是‘到民間去’;到民間去經驗了,先造出中國的自然主義文學來。”之后茅盾接連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在中國作家和文化界中大力提倡自然主義文學。1921 年7 月在為自然主義論爭作的總結性文章《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中,茅盾仔細地反思了當時中國文學創作的困境,認為中國作家們中了兩個觀念的毒:“一是‘文以載道’的觀念,一是‘游戲’的觀念。”作為矯正,茅盾主張通過學習以左拉為代表的自然主義文學作品的方法進行改造:“我們都知道自然主義者最大的目標是‘真’;在他們看來,不真的就不會美,不算善”,“左拉這種描寫法,最大的好處是真實與細致。”在這篇文章中,茅盾還專門分析了《盧貢·馬加爾家族》與近代科學的關系:“自然主義都是經過近代科學的洗禮的;他的描寫法,題材,以及思想,都和近代科學有關系。左拉的巨著《盧貢·瑪卡爾》,就是描寫盧貢·瑪卡爾一家的遺傳,是以進化論為目的”,“我們應該學自然派作家,把科學上發見的原理應用到小說里,并該研究社會問題,男女問題,進化論種種學說。否則,恐怕沒法免去內容單薄與用意淺顯兩個毛病。”
1930 年,茅盾以方璧的署名在上海世界書局出版了《西洋文學通論》,專門介紹了自然主義的代表作家及作品,其中就包括左拉的《盧貢·馬加爾家族》。在書中茅盾這樣評價這部家族巨著:“在十九世紀后半的歐洲文壇上,沒有第二部書更惹起廣大的注意和嘈雜的批評如《羅貢馬惹爾》了。即使是反對自然主義的批評家也不能不承認《羅貢馬惹爾》這二十卷巨著是文學史上空前的‘杰作’,直到現在還沒有可與并論的作品出世。在這部大著作內,左拉不但應用了近代科學的遺傳論的理論,作為全書的骨干,并且又恰當地挑選了‘第二帝政’時代的社會各方面都在轉換(資本主義發達到全盛) 的法國作為全書的背景,企圖對人生的各面作一極精密的分析和極露骨的表白。”⑩茅盾概述了《盧貢·馬加爾家族》中的系列小說的內容,分別對20 部小說的主要人物及內容進行了概括。總括了左拉這部巨著的內容之后,茅盾充滿激情地寫道:“這就是《羅貢馬惹爾》。左拉這巨人所堆的金字塔!”對于自然主義的代表作家左拉及其巨著《盧貢·馬加爾家族》,茅盾是有著自己獨特的閱讀體會和思考的。他曾這樣分析這部作品的特點:“由歸納‘人間記錄’而得科學的結論,因以立小說中所要表現的‘真理’而支配題材。《羅貢馬惹爾》不是隨便寫的,是依據了遺傳理論,歸納了‘人間紀錄’,然后客觀地描寫。這把人類的賢不肖的種種行為,立腳在科學的理論上,是左拉所獨創的。”
茅盾早在1920 年便參加了共產主義小組,同年7 月更是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政治身份的歸屬與對中國命運前途的憂慮,使茅盾的思想觀念逐漸地發生變化。茅盾在后來談到自己所受西方文學的影響時,已經與五四時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他說:“雖然人家認定我是自然主義的信徒,——現在我許久不談自由主義了,也還有那樣的話,——然而實在我未嘗依了自然主義的規律開始我的創作生涯;相反的,我是真實地去生活,經驗了動亂中國的最復雜的人生的一幕,終于感到了幻滅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執著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燼從別方面在這迷亂灰色的人生內發一星微光,于是我就開始創作了。”在20 世紀二三十年代,茅盾的文學觀念經歷了一系列的轉變,他對自然主義也經歷了由陌生到熟悉、由大力倡導到漸漸疏離的過程。隨著茅盾文學主張和思想觀念的發展,他對于左拉也有著迥異的評價。茅盾曾這樣分析左拉的創作方法:“這樣的方法似乎是有條有理,周密而謹慎。這是左拉慣用的方法。”“但是從這樣的方法搜集得來的材料只能說明那生活圈子的表面狀況,——是它的軀殼而非靈魂。”同時,面對瞿秋白所指出的《子夜》受《盧貢·馬加爾家族》中《金錢》 影響一事,1962年時茅盾還竭力為自己辯解:“瞿秋白當年稱《子夜》為受了左拉《金錢》的影響云云,我亦茫然不解其所指。”這一切,似乎都表明了一個令人尷尬的現象:茅盾雖然早年倡導自然主義,極為推崇左拉及其巨著《盧貢·馬加爾家族》,但其在創作長篇家族小說《子夜》時已經淡化了左拉這部自然主義經典家族巨著的潛在制約。
作家的思想資源構成、作品的創作過程受到特定社會環境、文化氛圍的影響是不爭的事實,無論作家出于各種原因加以否認,也不影響研究者勾稽史料、客觀分析作家作品之間的相互關聯。茅盾不僅對于左拉的這部巨著有著總體的、到位的分析,而且了解每一部作品的內容。他之借重左拉及其作品,根本目的乃在于向中國文學執著地輸入進客觀描寫、追求真實的精神與技巧,而對于某些有違中國文化精神的思想卻保持了足夠的謹慎。他在20 世紀三四十年代之后對于自然主義文學及左拉的回避,有著多重的原因,但并不影響作家受到自然主義文學影響的歷史事實。
二、家族生活的構思:結構、內容和破綻
左拉接受了實驗醫學和遺傳學的影響,他所設置的家族血緣關系中隱含著一種生理遺傳的因素,而這是茅盾在構思《子夜》時所沒有涉及的。在為一個充滿瘋狂與恥辱的時代做記錄的過程中,左拉所做的設想是:“把一個家族放在中心地位,另外至少有兩個家族派生于其上。這個家族在現代社會各個階級里繁衍。”“我要說明一個家族、一個小小的人群,在一個社會里是如何安身立命的,它繁殖出一、二十個成員,初看之下,他們千差萬別,各不相似,但加以分析,則可看出他們彼此之間隱深的關聯”,“一旦我掌握了這些線索,一旦我手里擁有了整個一個社會群體,我將表現出這個群體如何像一個歷史時代里的角色一樣行事,我將讓它在自己錯綜復雜的奮斗中活動,我將同時分析它每一個成員的意志力的總和與這整個家族總的發展”,“并且通過他們各自不同的經歷敘說出第二帝國從政變陰謀到色當投降的全部歷史。”從實踐來看,左拉對《盧貢·馬加爾家族》的設想達到了其目的。這部巨著中的人物活動的時間雖然被限定在第二帝國時期的20 年時間里,卻因寫于第三共和國期間,“整個家族史小說實際上也就反映了從五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的法國現實。”
作為對左拉的《盧貢·馬加爾家族》20 部小說內容均有了解且熟知小說結構、家族關系的茅盾來說,他在創作時自然會使之成為自己小說的某種潛在觀照,由此而形成內容上的某種共通性。從整體上看,左拉通過《盧貢·馬加爾家族》20 部小說表現了第二帝國時代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金融、農業、商業、政界、宗教界、資產階級暴發戶、藝術家、產業工人、流氓無產者、軍官、妓女等各個領域的形象;其中每一部小說反映社會生活的一個側面,由此而構成對時代生活的立體表達。而貫穿其中的,則是左拉所設計的盧貢家族的“自然史”和“社會史”。《子夜》創作于1931 年10月至1932 年12 月5 日,當時剛剛發生了一場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這促使茅盾萌發通過家族小說來表現中國社會性質及階級特征的希望。茅盾試圖借助一個遍布社會各個角落的吳氏家族,再現二三十年代上海社會形形色色的階層、人物和生活。“我那時打算用小說的形式寫出以下的三個方面:(一) 民族工業在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壓迫下,在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下,在農村破產的環境下,為要自保,使用更加殘酷的手段加緊對工人階級的剝削;(二) 因此引起了工人階級的經濟的政治的斗爭;(三) 當時的南北大戰,農村經濟破產以及農民暴動又加深了民族工業的恐慌。”茅盾的《子夜》在規模上明顯要小于《盧貢·馬加爾家族》,但我們同樣可以發現茅盾所展示的20 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社會的各個階級、領域內的種種生活,各階級各階層人物的形象在茅盾的筆下得到了栩栩如生的表現。就涉及到的領域而言,《子夜》仍然在都市與農村、政治與經濟、農民與工人、革命者與資本家、民族資產階級與買辦資產階級、上流社會奢華淫逸生活與底層貧民艱難度日、學生運動與教授生活等眾多場景的描寫中實現了對于社會史的生動刻畫。在某種意義上看,《子夜》可以說是對《盧貢·馬加爾家族》諸多生活和線索的濃縮,并以家族生活作為內在線索。
《子夜》與《盧貢·馬加爾家族》存在著某種對照關系。在《子夜》出版之后,瞿秋白即敏銳地發現了小說與左拉《盧貢·馬加爾家族》系列小說中的《金錢》之間的密切關系。在《<子夜>與國貨年》中,瞿秋白分析說:“這是中國第一部寫實主義的成功的長篇小說。帶著很明顯的左拉的影響(左拉的‘L’argent’——《金錢》)。自然,它還有很多缺點,甚至于錯誤。然而應用真正的社會科學,在文藝上表現中國的社會關系和階級關系,在《子夜》不能不說是很大的成績。茅盾不是左拉,他至少已經沒有左拉那種蒲魯東主義的蠢話。”除此之外,《子夜》中描寫到的雙橋鎮農村生活的動蕩也與《土地》中的鄉村世界有著相似的地方,尤其是《子夜》中的曾家駒這個流氓闊少簡直融合了《土地》中諢號耶穌基督的亞山特和畢托這兩個流氓的特色;《子夜》中所描繪上流社會奢華淫蕩的私生活,與《娜娜》所揭露的貴族階層荒淫無恥的生活十分相似,而交際花徐曼麗、以身體為代價接近趙伯韜的馮眉卿等形象也與娜娜的形象有著某種一致性。此外,《子夜》存在的缺陷也殘留了左拉的影響。左拉在創作時主張以科學的態度加以觀察,為了使自己的作品具備科學實驗的精準與攝影師般的細膩,他在進行創作之前總要大量地搜集、閱讀資料、了解生活,甚至為了寫作具體的場景還要進行實地考察,以期達到自己所追求的小說目標。在創作《人獸》時,左拉仔細地觀察車站、隧道、機車庫,與鐵路工人、工程師談話;為了創作《小酒店》,左拉經常到小酒店去廝混,并對個體勞動者和下層百姓進行調查;茅盾在《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中認為:“自然主義者事事必先實地觀察的精神也是我們所當引為‘南針’的”,“這種實地觀察的精神,到自然派便達到極點。他們不但對于全書的大背景,一個社會,要實地觀察一下,即便是講到一片巴黎城里的小咖啡館,他們也要親身觀察全巴黎城的咖啡館,比較其房屋的建筑,內部的陳設,及其空氣(就是館內一般的情狀),取其最普通的可為代表的,描寫入書里。”茅盾在寫作精神上接受了科學的方法,因而他也采取了相同的創作模式。
三、家族生活的再現:科學的描寫和實驗的小說
在《實驗小說論》中,左拉這樣闡釋自然主義的理論主張:“觀察者純粹是僅僅看到眼前的現象……他應該成為現象的攝影師;他的觀察應該準確地反映自然……他傾聽自然的話音,一字不差地記下來。然而,一旦看到了事實,仔細觀察了現象,思想便接踵而至,于是開始進行推理。這時實驗者便出面說明這個現象。”在這個過程中,作家如同科學家一樣,對事物保持客觀冷靜的態度,通過文字精確的剖析與分析來實現作品對于科學性的追求。為此,左拉對自然科學的方法進行了強調,認為應該將科學研究的方法應用到社會史和自然史的描寫中,以此來建立對一個時代的全面、立體和真實的表現。
左拉的這種主張正契合了茅盾關于發展中國文學的態度。在《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中,茅盾曾猛烈地抨擊舊派小說所存在的問題:“(一)他們連小說重在描寫都不知道,卻以‘記賬式’的敘述法來做小說,以至連篇累牘所載無非是‘動作’的‘清賬’,給現代感覺敏銳的人看了,只覺味同嚼蠟。(二) 他們不知道客觀的觀察,只知主觀的向壁虛造,以至名為‘此實事也’的作品,亦滿紙是虛偽做作的氣味,而‘實事’不能再現于讀者的‘心眼’之前;”對于新派文學,茅盾也意識到了其中存在的致命問題:“除了幾位成功的作者而外,大多數正在創作道上努力的人,技術方面頗有犯了和舊派相同的毛病的。一言以蔽之,不能客觀地描寫。”這里茅盾指出了舊派和新派小說的兩點缺陷,一是缺乏描寫意識和技巧;二是缺乏客觀的精神。正是因為這兩點,導致了當時新文學發展的緩慢和藝術成就的不高,茅盾試圖以左拉的自然主義為利器來糾正現代小說中真實感匱乏的癥候。
在《子夜》的創作過程中,茅盾運用左拉小說中充分展開細節的方式,對人物、環境和人的表情、動作進行詳盡的描寫,他雖然并未完全放棄作家的選擇權力,卻盡可能地按照生活的原生態加以勾勒,從而增加了小說的信息內涵,借此確立了中國現代小說的真實性地位。茅盾力求真實反映現實生活的原本狀態,努力摒除主觀意志對于小說敘事進程的干擾,使創作者的主體意志被消弭到最低的限度,從而讓作品呈現世界的客觀面貌。在茅盾的敘事中,他常常把全知全能的敘事者遮蔽起來,而代之以第三者的理性觀察。正如普實克指出的:“茅盾寫作方法與中國古代小說中盛行的那種古老的敘事方法完全相反。”中國傳統小說由于承載了過多的說教色彩,因此無論是說書還是小說,都喜歡采用主體存在明顯的敘事方式。這種傳統的敘述方式,在茅盾看來存在一個致命的缺陷,即“過于認定小說是宣傳某種思想的工具,憑空想象出一些人事來遷就他的本意,目的只是把胸中的話暢暢快快吐出來便了;結果思想雖或可說是成功,藝術上實無可取。”茅盾正是意識到了傳統文學敘事方式的弱點,他才堅決主張將左拉實踐的客觀真實性運用到文學創作中來,希望通過語言的客觀、邏輯的嚴密以及在場感的還原,為中國文學開辟一條新的大道。這種方法的優勢,一方面在于讓自然和社會描寫自動地進入讀者的視線,在一種客觀、理性乃至淡漠的態度中呈現出生活的本真面貌;另一方面,敘述視角的客觀化,也對傳統的文以載道的文學形成了致命的打擊。
在《盧貢·馬加爾家族》中,左拉對于日常生活化細節和環境有濃厚興趣,他試圖在人們習以為常的場景中建構起自己對于第二帝國時代自然史和社會史的表現目標。這些看似平淡的細節,填充了文學作品中人物活動的時代背景和現實處境,使人物的性格、思想和動作不再顯得突兀,而是與客觀環境融為一體。這種細瑣繁復的靜態描寫,在茅盾的《子夜》中也比比皆是,它們以實錄的精神盡可能地還原了一個時代的特定社會環境與社會習俗。左拉和茅盾都追求對于一個帝國或一個時代的社會生活的再現,在作品中表現社會不同階層的生活狀態。左拉在《實驗小說論》主張,“在我們的小說中若要對毒害社會的一種嚴重的創傷進行試驗,采取的作法同試驗醫生一樣,就是悉心找出最初的簡單的決定因素,然后即可獲得產生作用的復雜的決定因素。”運用科學方法進行文學創作,就必然要求全面地考察社會,這在某種意義上即是對于毒害社會肌體因素的尋找和發現,這必然導致作家在描寫和分析過程中對于一種完備而具體的描寫的要求。
在左拉的《盧貢·馬加爾家族》中,作家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著手,對第二帝國時期的社會生活進行了全面再現。其中在宏觀層面,左拉借助《盧貢·馬加爾家族》系列家族史小說,在每一部作品中揭示出一個對應的社會生活斷面,然后再將這20 部小說聯綴起來,就構成了文學作品對于社會歷史的全面而生動的再現。正是追求對于社會各階層生活的把握,這部巨著的人物總數達到了1200個,其人員分布覆蓋了第二帝國時期的各行各業,并由他們進而展開對于社會生活的全景式描繪。茅盾的《子夜》亦選擇政治、經濟、文化、感情、農村、都市等眾多方面進行具體細致的描寫,雖然規模上無法與《盧貢·馬加爾家族》媲美,卻也稱得上體例完備、人物周全,作品“寫大都市中形形色色的日常現象和世態人情,從舞女、少爺、水手、姨太太、資本家、投機商、公司職員到各類市民以及勞動者、流氓無產者等等,幾乎無所不包。”輦輷訛就微觀而言,《盧貢·馬加爾家族》將自然主義對真實生活的細節表現推向了一個空前的細致程度。在作品中,左拉對具體生活場景中出現過的景和物、狀態、方位、色澤、大小等都努力做到與現實一致。例如,《金錢》中對交易所的描寫,《娜娜》中對劇場的描寫,《土地》中對農村生活方式的描寫,都達到了令人震驚的地步。在茅盾的《子夜》中,作家對于吳老太爺風化細節的描寫、對于上海交際場所的刻畫等等,也達到了讓人過目不忘的程度。
當然,《盧貢·馬加爾家族》和《子夜》的創作并非盡善盡美。左拉與茅盾過于強調作家的科學精神,而對于人的心靈世界關注不夠,從而導致了小說敘事“物化”的傾向;他所主張的絕對冷靜、客觀的描寫方式也過于理想化,作家的視角可以隱退,但并不意味著完全放棄了篩選和摘擇的能動性。同時,自然主義所推崇的嚴格寫實,一方面可以促使作家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勇于再現生活的嚴酷性,從而達到暴露和批判的效果;但另一方面,由于失去了判斷的標準,一些觸目驚心、駭世驚俗的庸俗內容和瑣碎細節進入了文學。
四、家族的還原:生理學的觀察與社會環境的影響
左拉在對《盧貢·馬加爾家族》進行總體構思的時候,曾這樣表達自己所要追求的目標:“我的小說不可能發生在1789 年之前,我把它置于現代的真實性,寫種種野心與貪欲的擁擠沖突,我考察一個投身于現代社會的家族的野心與貪欲,它以超人的努力進行奮斗,卻由于自己的遺傳性與環境的影響,剛接近成功就又掉落下來,結果產生出一些真正的道德上的怪物(教士,殺人犯、藝術家)。”左拉在其中強調了他觀察的重點在于生理學和環境的影響兩個方面,其中生理學又包括遺傳學、身體欲望等內容。正如左拉所言:“如果我的小說應該有一種結果,那結果就是:道出人類的真實,剖析我們的機體,指出其中由遺傳所構成的隱秘的彈簧,使人看到環境的作用,”這也是對《盧貢·馬加爾家族》創作主旨和人物關系的一種獨特理解。
左拉的《盧貢·馬加爾家族》 真正從生理學、遺傳學的角度來觀察人、表現人,它對人類所具有的生物性進行了聚焦,從而一改過去形而上地描寫人物的模式,將人類的思想、情感、言談、情感甚至是疾病、變態行為等都納入到了文學的范疇加以考察。左拉通過家族小說中對人的自然屬性的描寫,試圖驗證他關于生理遺傳與家族成員命運的研究設想。“我所要研究的盧貢·馬加爾家族有一個特征。那就是貪欲的放縱,就是我們這個時代里向享樂奔騰而去的狂潮。在生理上,這個家族的成員都是神經變態與血型變態的繼承者,這種變態來自最初一次器官的損壞,它在整個家族中都有表現,它隨環境的不同,在每一個家族成員身上造成種種不同的感情、愿望、情欲,種種不同的人態,或為自然的,或為本能的,而其后果,人們則以善德或罪惡相稱。”左拉曾經為自己的這部巨著制定了一個人物世系表,以后的創作基本上按照這個世系表進行。
與左拉在《盧貢·馬加爾家族》中對于遺傳機制的系統考察不同,茅盾在《子夜》中并未明顯表露出有關遺傳學的思考;但后者對于作品中的性愛意識的描寫則是受到了左拉的影響。傳統的東方文化“像一個嚴酷的審美主義者,對人的肉體耿耿于懷,常常采用一些極端的措施,從物質到精神進行雙重改造和閹割。閹割就是去掉突出部位,使肉體變得完美起來,由功用主義物質形態變成抽象的美學形式。”對于具有濃郁封建色彩的中國文化來說,性愛意識往往受到封建倫理、禮教的重重壓制,人的生理屬性長期以來是被忽視的。在20 世紀二三十年代,當傳統文化趨向衰微、自然主義文化被大加介紹之際,性愛意識往往最先從文學中尋找到突破口。《盧貢·馬加爾家族》對于中國文學的意義,或許正在于此——“在左拉影響下,中國作家開始將性欲視為生命內驅力合乎自然目的的追求,不以為淫穢,亦不輕薄,以期真實傳達完整人生,從而大大豐富了小說中人性意蘊,深化拓展了現實主義。”
茅盾正要借助自然主義對于性愛的描寫來表現真實的人生:“他們也描寫性欲,但是他們對于性欲的看法,簡直和孝悌義行一樣看待,不以為穢褻,亦不涉輕薄,使讀者只見一件悲哀的人生,忘了他描寫的是性欲。”不過,雖然在《子夜》中也鮮明地體現了性愛意識,但這并不意味著茅盾對于自然主義關于生理學的描寫是全盤接受的。1922年周作人在給茅盾的信中就告誡說,自然主義專在人間看出獸性,中國人看了容易生病。對此,茅盾以郎損的筆名專門寫了一篇《“曹拉主義”的危險性》一文進行辯駁:“自然主義的真精神是科學的描寫法,見什么寫什么,不想在丑惡的東西上面加套子:這是他們共通的精神。我覺得這一點不但毫無可厭,并且有恒久的價值”。在這里,茅盾一方面堅持著自己對于“曹拉主義”的堅持,認為它具有“恒久的價值”;但另一方面,茅盾自己也對左拉作品中常見的所謂“獸性”抱有某種疑慮,而“根本觀念不同”則進一步明確地表明了作家對于左拉思想觀念的疑慮。
左拉在很多文章中都提到過他對于環境影響的關注。他認為“純粹意義上的環境,即社會環境與地域環境,則決定了人物所屬的階級”,“人們在成為掌握人體現象的主人并對之產生影響時,便可以對社會環境發生作用。下面就是構成為實驗小說的幾個方面:掌握人體現象的機理;依照生物學將給我們說明的那樣,展示在遺傳和周圍環境影響下,人的精神行為和肉體行為的關系;然后表現生活在他創造的社會環境中的人,他每天都在改變這種環境,他自身在其中也不斷發生變化。”左拉不僅在《盧貢·馬加爾家族》中表現出一個家族的自然史,而且還要表現出這個家族與社會環境、物質條件產生的關系及其影響。為了表現環境對于盧貢·馬加爾家族的重要影響,他將一個家族的不同后代設置在不同的社會、物質環境中,結果他們的命運或者遺傳疾病的走向都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同時,在表現環境對于人物的影響時,左拉還特別注意勾勒出不同階級、職業、身份的人物之間的社會和個性的差異。與左拉在《盧貢·馬加爾家族》中表現出來的某種遺傳學的宿命色彩一樣,茅盾在《子夜》中也著力刻畫了社會環境對于個人的無法抗拒的壓力。《子夜》中的吳蓀甫是一位有著雄才大略的民族資本家,他既有著現代科學管理的經驗,又有著罕見的魄力、頑強的斗志,如果欣逢盛世或許早已成為中國的大企業家。但是吳蓀甫恰恰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一方面受著買辦資本的排擠,一方面又受到戰爭、工潮的掣肘;他一方面有著發展民族工業的藍圖,另一方面又缺乏政治支持和經濟援助,最終在多重環境的壓迫下精神崩潰,這與《盧貢·馬加爾家族》中環境對人物的影響有著極大的相似性。
茅盾通過對左拉自然主義文學作品的吸收、借鑒促進了自身的創作,他運用自然主義手法表現中國家族小說及社會各階層的生活,并將科學實驗的方法和生理學的內容納入了文學領域,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家族小說的表現范圍和敘事方法。這種融匯了科學實驗精神、生理現象學和社會文化學的家族小說,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獨樹一幟。這一方面驗證了弗朗茨·庫恩關于《子夜》中東西文化融合的體察,另一方面也向我們昭示了中西家族小說在借鑒、融合過程中存在的文化差異。創作方法、生活閱歷不斷豐富的茅盾,本應有機會創作出中國式的《盧貢·馬加爾家族》,然而波瀾詭譎的現代中國卻并未提供良好的寫作環境。在救亡與圖存的歷史轉折關頭,茅盾對于中國現代家族的敘事沖動一步步讓位于戰爭風云和政治斗爭,最終只留下了《子夜》這一部留下了許多缺憾的自然主義家族小說。茅盾的經歷與選擇,給文學史留下了許多耐人咀嚼的作品與史料,值得后世學者認真研究。
注釋:
①?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 年版,第71 頁、第71 頁。
②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中)》,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版,第121 頁。
③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版,第172 頁。
④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年版,第108 頁。
⑤[德]弗朗茨·庫恩著,郭志剛譯,李岫編:《德文版<子夜>前記》,《茅盾研究在國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5 頁。
⑥沈雁冰:《評四五六月的創作》,《小說月報》1921 年第8 期。
⑦⑧⑨?????沈雁冰:《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小說月報》1922 年第7 期。
⑩??茅盾:《西洋文學通論》,書目文獻出版社1985 年版,第109-110 頁、第117 頁、第117-118 頁。
?茅盾:《從牯嶺到東京》,《小說月報》1928 年第10 期。
?茅盾:《茅盾論創作》,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 年版,第462 頁。
?茅盾著,賈亭、紀恩選編:《茅盾散文》,中國廣播出版社1995 年版,第562 頁。
??????????[法]左拉著,柳鳴九譯,柳鳴九編:《關于家族史小說總體構思的札記》,《法國自然主義作品選》,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733 頁、第736頁、第737 頁、第741-742 頁、第756 頁、第733頁、第735 頁、第736-737 頁、第733 頁、第751頁。
?[法]左拉著,柳鳴九譯,柳鳴九編:《<盧貢·馬加爾家族>總序》,《法國自然主義作品選》,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247 頁。
?茅盾:《<子夜>是怎樣寫成的》,《新疆日報》(副刊《綠洲》) 1939 年6 月1 日。
?[捷]雅羅斯拉夫·普實克著,李燕齊等譯:《普實克中國現代文學論文集》,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 年版,第135 頁。
?柳鳴九:《重新評價左拉的幾個問題——在中國法國文學研究會主辦的左拉學術研討會上的主旨學術報告》,《法蘭西文學大師十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 頁。
?張檸:《中國當代文學與文化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 年版,第322 頁。
?錢林森:《法國作家與中國》,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 年版,第333 頁。
?郎損:《“曹拉主義”的危險性》,《文學旬刊》1922 年第50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