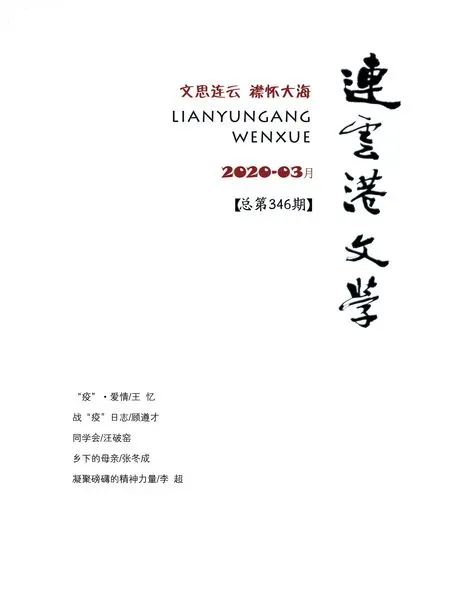瓜事
王文巖
對于生吃瓜,我有著近乎病態的迷戀。若追根求源,這種病態可以追溯到20 世紀我很小很小的時候。
我出生在20 世紀60 年代末,那個時候溫飽問題還未解決,一切都以糧為綱,而我家鄉的黑土地又是長莊稼的沃土,于是,家鄉的大小片田,種的都是小麥、玉米、黃豆、水稻之類的糧食,家門口那塊小得可憐的菜園里也幾乎統一地栽種大蔥、白菜、蘿卜等能放進鍋里的菜類,就連籬笆墻上纏繞著的也是能炒菜的豆角、冬瓜、絲瓜、葫蘆之流。至于那些能生吃的瓜類,統統被看成是不抵饑不抵餓的消費品。村上偶有敗家老娘們在菜園隱蔽處栽上幾棵黃瓜,往往是剛剛結出指頭大的瓜牙轉眼工夫就不知進了自己孩子還是別人家孩子的肚里,因此種種,村上人家的菜園子就好像復制一般,一家一家的都一個樣。要想見到黃瓜、酥瓜、甜瓜,那就得豎起耳朵,一聽見“賣瓜嘍,賣瓜嘍”的吆喝聲就尥蹶子朝外跑,一準看到推著交通車高聲叫賣緩緩走來的侉子賣瓜人。交通車的長框里多的是黃瓜、酥瓜,很少見甜瓜的。瓜可以用錢買,也可以用糧食換。于是有的孩子便氣吁吁地跑回家,哭鬧著讓大人買瓜,可大多數的大人都無視孩子的哭鬧,硬著心腸不買。也有的孩子哭鬧成功了,破涕為笑地跟在媽媽后面仰著小臉端出半米籮小麥、玉米抑或是山芋干,一番討價還價后買了幾根黃瓜,樂滋滋地端著奔回家去。大多數的孩子們知道哭鬧無用,便嘰嘰喳喳地圍攏著賣瓜人的瓜框,似乎看一看瓜兒嗅一嗅瓜味也能解饞,當然,也有的孩子忍不住誘惑會悄悄地將臟乎乎的小手伸進瓜框,企圖去摩挲一下瓜兒那清嫩嫩的皮兒。
買瓜解饞的可能性不大,孩子們的希望在田野里吶。背著背簍三五成群的身影游弋在鄉野的每一個角落:玉米高粱地、黃豆山芋田、大河灘小樹林。名為割草,眼睛似鷹鼻子似犬,最常獵獲的便是野生喇叭瓜,一根藤蔓拉開來,能摘到好多鵪鶉蛋大小的喇叭瓜,其中熟好微黃的喇叭瓜又香又甜。有時候,運氣好也會在人跡罕至的隱秘處發現悄悄生長的野酥瓜,但大多數情況下,最大的野酥瓜也只有雞蛋大小,此時的野酥瓜正在醞釀苦味,淺淺的啃一層皮,脆鮮鮮甜津津的,稍咬深些便苦得人腦仁生疼。因此,孩子們都會強忍著口水,將四周的藤蔓野草聚攏來嚴嚴實實地掩蓋住野酥瓜秧子,并相約多少天后一起來摘瓜。只是往往事與愿違,幾天后再來看時,瓜早已被后來者摘走,懊惱之余恨恨地咒罵幾句怏怏而去。
所謂“狼多肉少”,好不容易發現一棵喇叭瓜,驚喜還在心頭跳動呢,可拉起瓜蔓一個個試過去,滿滿的全是失望,熟好的喇叭瓜早已進了先行者的肚里。黃豆地里喇叭瓜多,可自從豆莢起鼓后生產隊的看青便看得緊了,看青的來回巡視,冷不丁的就會在哪兒冒出來,嚇得人魂飛魄散,因此,孩子們輕易是不敢進黃豆地。
不過,孩子們智慧多多,解饞的方法也多多。譬如我與我的好朋友小榮就偷吃過東河灘霞家的冬瓜。那天太陽亮亮的,我與小榮在河灘上割草,中途提起過好多棵喇叭瓜蔓,可沒找到一個不苦的喇叭瓜,天近晌午,又饑又渴的我們發現了一個個圓嘟嘟的冬瓜靜臥在瓜葉下,我與小榮的想法不磨而合:我們挑一只乳白色絨毛覆蓋的鮮嫩冬瓜,削掉嫩綠的皮,一人一半,坐在樹蔭下大快朵頤。冬瓜肉不太甜但汁水很多,瓜瓤部分則有點別樣的酸,很是可口,只是吃過冬瓜后嘴巴里有點澀澀的異樣感。
小榮說冬瓜有些像西瓜,我沒見過西瓜,可小榮吃過。小榮家與我們家只隔著一條窄窄的巷口,小榮的父親在大隊部干點什么,母親是代課老師,他家總會有稀罕的東西。有一次我在小巷里發現一塊碧綠的瓜皮,翻過瓜皮,瓜皮上還帶著薄薄的一層瓜肉,瓜肉上還隱隱見到淡淡的粉紅。平常我們吃瓜是不留瓜皮的,我跑回家夸張地向父親描繪那塊瓜皮,父親說那是西瓜,吃西瓜只吃里面紅色的瓤子不吃瓜皮的。我使勁地在腦海里琢磨著西瓜的樣子,可想的全是紅紅的瓤子咬進嘴巴的爽快,不由地猛咽口水。
一年級的時候,語文老師教授我們漢語拼音,老師帶讀“X 西瓜的西”,X 拼音下配圖:一塊切開的西瓜,碧綠的瓜皮,紅艷欲滴的瓜瓤,黑亮的瓜籽。我一邊大聲跟讀一邊悄悄地吞咽口水。這時候,我對西瓜總算有了形象感官的認識了,不過我憧憬著的是什么時候能看到真的西瓜,咬一口蜜汁樣的西瓜紅瓤。
做夢一樣,一天放學回家,我真的見到了一個又大又圓的西瓜,并且真得吃到了西瓜瓤子,只不過我吃的西瓜瓤子是淡粉色的。那年我十歲,好像大人們也不在為溫飽問題發愁了,以糧為綱的口號似乎也不再喊了。我們固村臨縣的郭莊悄悄地種了一片瓜田。郭莊與我們村隔著一條大河,郭莊的幾乎所有都在東河岸,可偏偏遺留一塊河灘地在西河岸與我們村的田地相連,郭莊人便在西河灘上種起了香瓜,自然這塊地從瓜秧扯藤起就吸引了我們村大孩子小孩子垂涎的目光。郭莊人當然知道這塊瓜地的誘惑力,他們村派出了粗壯似虎奔跑若飛的大刁二刁兩光棍兄弟看瓜,兄弟倆在瓜地頭搭個瓜棚,吃住都在瓜棚,整日虎視眈眈地守護著瓜地。慢慢地隨著瓜的成熟,瓜的甜香隨著微風飄進了孩子們的睡夢里,大小孩子白天黑夜都在琢磨著香瓜的事。孩子們的鬼點子多的是,何況參與的還有許多大孩子。俗語說“好漢難敵雙錘”,況且幾乎是整個村莊的烏泱泱一片的孩子,他們有的是從電影里學到的戰術:“敵進我退,敵退我擾”“多方向多角度進攻”。結果是大刁二刁顧頭難以顧腚,面對各個方向真真假假的偷瓜者茫然不知所措,自然,孩子們得手的機會就很多了。這一次大刁二刁追趕幾個偷瓜的大孩子去了,姐姐他們便趁機跑進瓜地,瓜地種的都是香瓜,只有瓜棚旁種有幾棵西瓜,姐姐沒見過西瓜,看到這么大的一個便摘下抱著跑回了家。哪知道抱回來的西瓜還是個生瓜蛋子,不過我們捧著這沒熟的西瓜也是十分的欣喜,自然也啃得津津有味。
日子真是不經過啊,幾乎是一轉身的光景,我們已近中年。不知從幾時起,生吃瓜不再是夏日的專利了,一年四季,只要你想吃,超市里可以買到各種各樣的瓜,黃瓜、酥瓜、香瓜、哈密瓜……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的瓜。就是西瓜也有眼花繚亂的品種,八四二四、黑美人、蜜寶、特小鳳……紅壤的、黃瓤的……只有你想不到的沒有你買不到的。我仍然喜歡吃瓜。終于可以酣暢淋漓地吃瓜了,可再稀罕的瓜也激不起自己那份吃瓜的急切了,即使是特甜特香的瓜塞鼓肚皮,仍覺得瓜味里少了點什么,而淤積于心的饞癮卻一直都在。有時候依然懷念野地里喇叭瓜的香甜,舌尖存留的仍是第一次遇見的那半生熟西瓜的甜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