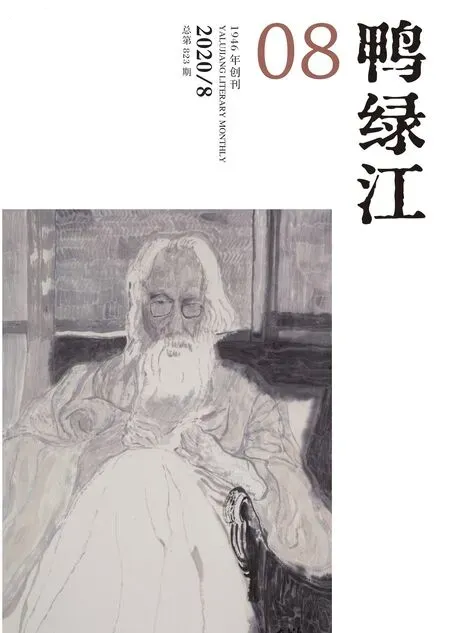胡劍散文二題
胡 劍
老妹曉凡
妹妹來無錫了,并且和我一起過了元宵節,這是妹妹離開無錫八年來唯一的一次團圓元宵。如果不是她到蘇州參加一個培訓,重聚無錫的日子恐怕還要等待下去。
妹妹跟著我一起來無錫的那一年,我23歲,妹妹21 歲,我一手揣著大學畢業報到證,一手拉著妹妹,在父母的淚眼中踏上了北上的列車,頗有大義凜然狀,覺得很是豪邁。自己剛畢業,就能帶妹妹出來打工,而父母也那么信任自己。那時村里的小年輕兒都流行南下廣東打工,帶親戚出去能找到一份工作、掙到一份工錢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村東頭的胡齊堂,那個和我同屆的大學生,帶著他的妹妹居然在省城南昌找到了工作,不知道紅了多少村里人的眼球,哎,我就是其中一個。所以,決定帶妹妹一起出來,我是沒有一絲猶豫的,盡管母親一直嘆氣落淚,最終還是把從沒離開家的妹妹交給了我。
妹妹還算幸運,高中畢業。在農村,“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唯有讀書是出路,要想跳出“農門”,拿到城市“糧油證”,只有考上大學,但在農村都只愿意供男孩讀書,女孩大多讀到初中畢業就回家幫父母打理田地,然后嫁掉。在“供書”上,母親從來都是一視同仁的。但最終沒能“供”出來,擠“橋”的人太多了!
母親的擔心不是多余的。其實可以想象到的,一個毛頭小伙子,在無錫無親無故,自己都沒踏上社會,怎么可能幫妹妹找到工作。到單位報好到,我馬不停蹄滿大街地去找工作。妹妹學了五筆輸入法,速度還可以,我打算給她找一份打印社的文稿輸入工作,但問下來都以失敗告終,理由都是一個,光會輸入文稿不行,還得會平面設計。做小飯店服務員我是舍不得的,在家里我都不愿意讓妹妹洗碗。大飯店里又進不去,再說又沒經過專業培訓。馬路旁電線桿上的小廣告也是我搜尋的目標。有兩次深刻的記憶,一次是看到一個招做月餅的操作工,興沖沖跑過去一看,竟然是個地下黑作坊,蒼蠅滿天飛,我拉著妹妹的手就跑了。另外一次是一個小煙酒店要招看店女工,還包吃包住,工資待遇應該還可以,但那個四十幾歲的鰥夫眼睛一直往我妹妹身上瞟,我很是厭惡,走后就沒有再出現過。
剛認識的一個人在我焦頭爛額無計可施的情況下幫了我,把妹妹介紹進了中橋二村幼兒園做了一名代課教師,美麗的妹妹終于有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盡管工資低得可憐,盡管只是代課。連夜電話給母親,在我們兄妹興奮的語調中我聽到千里之外母親哽咽的祝福。
妹妹只做了半年幼兒園的代課教師,一次意外,妹妹失去了那份工作。那是一件令我至今難以釋懷的“恥辱”之事。一天那個朋友找到我,說幼兒園里丟了兩條幼兒睡覺蓋的被子,問在不在我宿舍,還說報警了。我頭一熱,兩條被子確實在我宿舍,也確實是妹妹從幼兒園里抱過來給我的,說是幼兒園被子很多,不要緊,她跟里面阿姨說好了帶過來的,省得我花錢去買,可以省下一百多塊之類。我是忍著眼淚把被子抱給警察的,并全部承攬了責任,說是我教唆妹妹去拿的。我讓妹妹辭了那份來之不易的工作。當晚,兄妹對坐半夜,妹妹只對我說一句話:“我看你冷,你又舍不得買。”我也只對妹妹說了一句一直想說的話:“苦難會過去的,你哥行!”
后來妹妹做了郊區熱水器廠的操作工,做過小飯店服務員,沒工作時還在她認識的小姐妹家閑住過,我們相互鼓勵,相互打氣。我在工作上也絲毫不敢怠慢,兼職做起了家教,一對一上門教課,備課輔導,兢兢業業。有時晚上補課也帶上妹妹,到學生家吃飯。值得高興的是,我的學生家長都喜歡妹妹,一個叫王一薇的女孩親熱地叫她姐姐,她父母要我每次來家教時都帶上妹妹,并且家庭活動也邀請妹妹參加,還有一個叫朱阿姨的學生家長,每次都做妹妹喜歡吃的紅燒肉。
妹妹終于有了一份讓我也羨慕的工作。朱阿姨給我介紹了一個學生,他爸爸是廣東一家服裝的總代理,在夢之島商場設有專柜,那時的夢之島商場是無錫最豪華的服裝商場,購物環境一流,服務設施一流,遠遠超過當時的中山商場、商業大廈和一百。當妹妹穿上制服站在夢之島商場二樓的飛將軍專柜,優雅地為顧客介紹服裝時,我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哥哥,每每經過夢之島,我必定上去看看,有時還特地帶同事去她的專柜看她,而妹妹也驕傲地為同事介紹她的哥哥我。那一年,我的工資是五百來塊,而妹妹的工資是一千元,加上銷售額,近兩千元!
這樣平穩的日子持續了兩年,隨著公司的運作轉制,妹妹又要失業了。但這次,妹妹選擇了離開,回江西,離開她生活了四年的無錫,離開與她相依為命的哥哥。這一次,我沒怎么傷心,因為她回去是為了愛情!
但我非常不舍得!
相處四年,已經習慣了妹妹在身邊的日子——
習慣了每天兩人買菜做飯;
習慣了兩人圍坐一起說家鄉話;
習慣了帶她去學生家吃飯;
習慣了兩人騎單車去市中心逛;
習慣了兩人守著那臺黑白電視機;
……
其實,我心里最大的結,就是沒能讓妹妹體驗到哥哥的成功,妹妹回江西的時候,我甚至還沒有自己的房子,依然住在單位廁所旁的那間宿舍,也沒能帶妹妹進好的飯店吃飯,走到公園門口被那幾十元的門票擋在外面,從來都沒帶妹妹打過車……
送妹妹上火車時,我說,下次來給你個全新的哥,不一樣的哥!妹說,一定來,喜歡吃你做的老兩樣——青菜和紅燒豆腐!(這兩樣菜最便宜,十天里我們兄妹要吃七天。)
時隔八年,物是人非。我對妹妹說,你看你哥行吧,無錫人有的我都有了,無錫人沒有的我也有了。我這個大忙人做起了專職司機,帶妹妹游歷了曾經工作的熱水器廠、幼兒園,還有我原來單位的宿舍,到原來小姐妹家吃飯做客,之后“錢柜”唱歌,“金水桶”泡腳,中山路購物。
第二天,我帶妹妹去了我的新單位,如十二年前般,又體驗了一回帶著妹妹去上班的感覺。
正月十七,妹妹又回江西了,妹妹說:這次真的不一樣!可惜沒吃到你做的老兩樣!妹妹今年33 歲了,應該叫老妹了,她有個非常好聽的名字——曉凡。
那些一去不再的歲月
昨晚,兒時的玩伴終于聚集一起了。
組織這次聚會不容易。大家天南海北,各奔東西,村里二十幾個同齡人也就來了十個。電話打過去,萬里之外的拉薩,胡勁松說忙著討債明年一定回來;千里之外聊城的胡美華說票難買到年后看看能否回;而八百里的常州,胡華林干脆就說不回來,過自己的小家家了……
酒桌上的話語一刻沒有停過,東耙西耙,海闊天空,侃到哪兒是哪兒,一會兒這兩個人一堆,一會兒那三人個一撮,一會兒全體側耳傾聽,土話連篇,還時不時冒出很地道的臟話,說得最多的當然是兒時那些爛谷子的事。每個人都在搜索自己最深刻的那些印跡。三十多年過去了,居然一拉就是許多個片段,可想而知那時的記憶鐫刻得多么深厚。
兒時嬉戲的三個池塘兩個不見蹤跡,剩下的一個也已一潭死水臭味熏天,好在政府已經認識到發展經濟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關閉了百分之八十的養豬坊。這三個池塘是村里的命脈,池塘把我們從兒童泡成了少年,洗衣的少女從這個村的池塘邊嫁到了那個村的池塘邊。如今的村子池塘不再,倒是幾個當年的小伙伴的三層小樓造在其上。池塘的水已不能洗衣游泳釣魚,現在的少女已經不能重現我們當年的畫面。悲夫。
除了池塘,話題最多的就是電影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基本沒有什么娛樂節目,跳房子、跳皮筋、打紙板,再就是每個小伙伴端著個小玻璃瓶去抓墻洞里的蜜蜂,比誰抓得多。要是村里來了場露天電影,那基本上就是過節了。村里放電影無外乎以下兩個原因,一是鄉鎮里輪流放,輪到哪個村就哪個村;二是村里有了大喜事,有錢人家花錢請場電影在村里提升人氣。提到電影,自然少不了要提一個叫胡和平的小伙伴,只要本村或鄰村放電影,他是第一個知道的,甚至連什么電影都能搞清楚。他是個結巴,可他是傳播速度最快的人,“可惜啊,死得太早。”胡張華感慨地說。我們都停下了酒杯,沉默了一會兒。他是得出血熱死的,年僅十二歲,那個時候這個病是絕癥。
胡椒是村里第一個跳出農門的女生,她今天的到場讓小伙伴們有了不少談資。“要是當年沒考上衛校,現在哪有這么水靈?應該就是農村老大媽一個吧。”胡新春逮著就是這句話。依稀記得三十年前她的樣子,小個子、短頭發、瓜子臉,不愛說話還愛哭的一個小女生,那年她參加中考考上了多少人夢寐以求的宜春衛校,真正實現了知識改變命運。如今的胡椒是高安市區一個醫院的護士長,還是那么嬌美。
打群架也是飯桌上的話題之一,我們這一圈男人在那個時候至少分了三幫,小伙伴有摩擦是正常的事情,自然而然就有人拉幫結派。不過,打群架可不是現在小青頭那種打法,充其量是斗“人氣”,誰的小伙伴多,誰就占上風,經常是這樣一個場景:胡張華帶著一幫人,胡新春帶著一幫人,分站兩邊。對罵開始,兩個小頭目要開始比畫了,胡正帶了一幫人出現,兩伙小伙伴就扯呼作鳥獸散狀,每次都打不起來。說到此,我們不由得哈哈大笑起來。
不只是祠堂不在了,還有逝去的人,回到村里,往年親切叫“建軍回來了”的老人也大多不在了,見到的是一個個陌生的后輩,以及正在經歷我們當年故事的少年和少女,但是,少了池塘,少了綠水,少了祠堂,少了露天電影,少了洗衣的青石板,少了打群架的他們,多年以后,記憶里的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