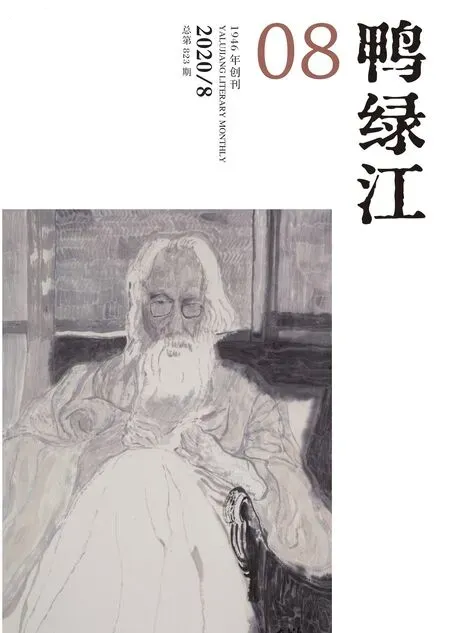魯迅小說的藝術創新
——以《故事新編》為例
蘇文潔
一、話語結構
在《故事新編》中有兩個話語系統,一是包含作者自己主體意識的主體話語;二是被描述了的客體話語,也就是“他者言語”。
第一類話語不言自明,它表達了作者對于周圍世界的主體性體驗以及評介,它只屬于作者自己。作者對世界的觀點都包含在了這一話語之中。主體話語反映的其實是作者與世界的關系,它表達了在作者眼中,世界的圖景到底為何。作家通過自己獨特的想法和感受,將自己特殊的情感體現在語言和語句中,更重要的是要將自己觀察世界、觀察生活的感受和方式也表達出來,所以語言一定會帶有他自身的獨創性和自由性。寫作的意義也在于此,即用自己的語言表達對于世界的看法,如《奔月》《理水》《鑄劍》中的話語。
《故事新編》的第二類話語是“他者話語”。既然是“故事”的新編,必然是對那些已經存在的神話、傳說以及史實中存在的舊事進行重新描述。而描述的范圍不僅包括故事本身,同時也包括對故事人物的言語與行為更加細致的虛構。我們關注的“他者話語”,其實就是故事中人物的言語。通觀《故事新編》,讀者可以發現,作者對其中人物的語言表現出了極大的描摹興趣,甚至可以這樣說,《故事新編》中對話語的關注已經超越了故事本身。這些眾多不同的“他者話語”成了《故事新編》中真正的主角。文本中出現了多少個人、發生了什么事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是否在文本中發言,話語成了魯迅關注的重心。每一個仔細閱讀《故事新編》的讀者,都能感到這些“他者話語”被作者推到了前臺,如《補天》《采薇》《起死》《出關》等。
二、敘事特點
世俗化敘事是魯迅對歷史題材小說創作方法的創新,已有研究多從兩個維度出發:一是“古與今的對照互動”,即通過現代反觀古代,揭示古代人與事中某些被掩蓋的真相;第二個常見的研究維度是“虛與實的糅合”,即將現實性細節有意識地融入歷史小說之中,直接影射現實社會中的一些具體現象。
對《故事新編》來說,世俗化敘事具有形式和思想上的雙重意義。在“古今雜陳”和“虛實結合”之外的第三個維度是“神圣與世俗”的關系角度——既表現在原始文本與新編文本之間,又體現在新編文本內部。《故事新編》的“試驗性”和“先鋒性”特質表現為作者向早期建立的中國現代小說規范(以《吶喊》《彷徨》等現實題材小說創作為代表)尋求突破的藝術訴求。現實與歷史本身就有一種回望性,但是歷史與現實是怎么聯系起來的,這就需要一種超脫俗常的、具有獨特表達效果的敘述方式。文本中主要人物身份經過語境的變化顯示出截然不同的意義,即主要人物本身所代表的文化、歷史意義與新編語境之間形成沖突磨合導致意義的指向性模糊化,多種類型的文本形態的化用使文本意義呈現出多層次性。因此,世俗化敘事形態下的《故事新編》在不同的歷史語境中會呈現出不一樣的闡釋角度和結論。《故事新編》中的世俗化敘事主要表現為“英雄形象”的日常生活呈現,也就是將“英雄”與“日常生活”兩個元素形成一個“錯位”的組合,表現英雄的日常性一面,或者說描寫日常生活形態下的英雄形象。這樣一種“陌生化”的表現策略,不僅具有題材上的創新性,更有創作指向上的獨特思考。體現虛構文本對神話傳說文本的世俗化作用的篇目有《補天》《理水》《起死》等,體現歷史文獻文本敘述重點的轉移的篇目有《采薇》《出關》《非攻》《起死》等,體現民間故事對神話文本的世俗化作用的篇目有《奔月》和《鑄劍》。
《故事新編》的多種文本類型之間并不是簡單地拼湊相加,作者在各個層面上使不同文本類型之間相互作用,形成新編故事文本的戲劇沖突,使得以神圣敘事為主的歷史文本的性質發生了變化,既有歷史文獻本身的“言必有據”,又有民間故事的戲謔和滑稽色彩。
三、審美趣味
《故事新編》展現出來的是一種“民間”表達,即走向現實與反思的歷史。出現了圣賢回歸大地后的各種姿態,就是《補天》中的仙女嫦娥每天也得吃炸醬面,而后羿更是將吃表現到了極致,正像是人們常說的“吃飽才有力氣干活兒”。就算是要赴天追回嫦娥,也要好好吃頓飽飯。而《非攻》中的墨子,也一改理性刻板的智者形象,他的出行方式有一種“兵馬未到,糧草先行”的感覺,必須提前準備好自己的行路干糧。同樣,在《起死》《理水》中也有相似的表達。這種描寫的背后不僅是“圣賢”與世俗文化的抗爭,也是“物質”與“世界”的對抗。所以羿吃完晚餐、休息好之后依然還是要上天追月。
《故事新編》還表現出了對自由的探索。魯迅在《序言》中解釋歷史小說的創作規范時,提到了文體語言的自由和“隨意點染”。從這個角度來說,魯迅的確是新文體的創造者,也是在這個意義上,充滿著古今交融、想象虛構的《故事新編》以一種獨立的小說體例類型而存在。魯迅對他的“自由”的使用效果是沒有將“古人寫得更死”。他無意于對著古書照著講,而是在中心情節發生之前或之后接著講,在自己的生活經驗、生命體驗的基礎上進行自由的新編。因此《故事新編》我們看到作者想探尋的不是“是什么”,而是“為什么”和“怎么樣”的問題。同時,又讓現代元素自由出入古代文本,為古今共有的一些普遍性現象提出一些新的問題。這樣一來,編年史的求“事實”被思想史的求“解釋”所代替。文本中的女媧的“造人”和“補天”、嫦娥的“奔月”、三個頭顱的“鼎中互噬”、莊生“起死之術”這些玄幻荒誕的情節的真實性被懸置起來。魯迅并不為這些玄幻荒誕的情節做某些合理化、科學化的解釋,似乎它們成為一種已然成立的假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