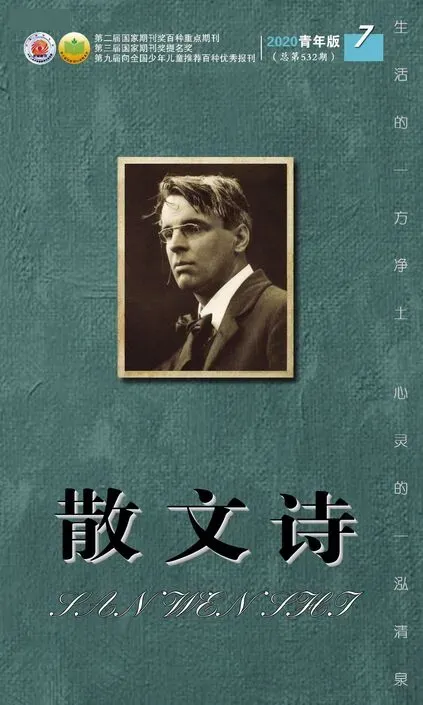母親在黑夜唱起歌謠
甘 健

圖/蔡建勛
我一直不喜歡黃昏。
是的, 確實, 不喜歡。
你眼睜睜地看著夕陽無可挽回地墜落, 田野里、 水塘中飄起暮靄, 漫長的黑暗從此刻出發。 黃昏, 像一個坑, 一天的瑣碎,一家的悲歡, 都選擇流向這里。
這樣的時候, 似乎只配發生不愉快的事情。
我看見生產隊長背著手, 臉色沉重地, 從東頭到西頭, 挨家挨戶地踱過去。
他跟每一家的大人低語幾句, 然后又似乎不情不愿地轉往下一戶人家。 我感覺他對每一戶說的都是相同的話, 他一直在做復制的工作, 而這些話顯然是不方便粗著脖子、 鼓著腮幫在大喇叭里喊叫的。
本來安靜的村莊在隊長走訪過后一下子長出許多喧鬧的聲音。有女人哭著罵自己的男人沒有用的, 有男人怨自己家里要供養那么多吃閑飯的嘴的, 鄰居家的二狗, 從屋里沖出來, 邊哭邊跑,后面跟著努力追趕著他的二姐。
我那時大約十歲, 是個懂事的孩子, 早就已經懂得察言觀色了。 我敢肯定, 是隊長剛才說的話直接點燃了鄉村的沸騰。
我的父母, 總習慣在黃昏的時候發生爭吵。 這一天, 他們放棄了爭論, 他們在討論一個嚴肅得多的問題。
耳尖的我從他們嘴里依稀聽懂了一個詞——
返銷糧。
在我當時的理解范圍內, 返銷糧大概是在每個人走投無路的時候才會擁有的, 但也不會輕易擁有, 那是對抗災難的最后一張牌。 隊長剛才就是告訴各家, 返銷糧下不來了, 要大家做好挨餓的思想準備和物質準備。 整個世界如天塌一角, 一種抽象的恐怖鋪天蓋地地包圍過來。
構筑我最初記憶的是故鄉的花鳥蟲魚、 細長的竹子和大小高低不一的樹。 我的故鄉, 田野手牽手, 連成片, 默默向遠方延展, 一直抵達天的盡頭。 橫豎交錯的河渠穿行其間, 水與土的相處和諧而自然。 樸素的土和低調的水一直以它們無私的胸懷, 善待居于其上的每一個生靈。 它們是值得信賴的。 我從小就和它們打成一片了, 翻溝鉆渠捉泥鰍, 爬樹上房搗鳥蛋, 我每天都向這片天地源源不竭地釋放熱情。
但是, 那個有生產隊長挨家走過的黃昏, 那個父母停止爭吵的黃昏, 刻在記憶里。 我瞬間長大了。 十歲的我仿佛被拖入一個陌生的世界, 我對這個世界的所有理解原來只是一種自以為是和自作多情。 我好像被整個世界拋棄, 覺得當時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迅速保持身體和語言的絕對安靜。 四周是土磚墻壁的堂屋, 我慢慢收攏自己, 慢慢后退, 退到大人忙碌疾行時不會擋他們道的地方, 退到其他人不會因為陡然看到你而心生煩躁的地方, 退到煤油燈昏黃的光亮搖晃不定的角落, 退到如同消失了一般。
那時, 正是植物離開土地的冬天, 坦蕩無私的大平原, 黑暗、荒涼和亙古如斯的寂靜, 給了不知什么時候突然來湊熱鬧的北風長驅直入的理由。 風, 由小到大, 刮得越來越起勁, 那種平原地帶特有的北風, 拼命搖撼著我家屋后那片楠竹林, 修長的竹枝, 細密的竹葉, 發出瘋狂而迷亂的摩擦聲, 將北風的威力進一步助推。 我一度感覺北風是災難的前奏, 它是來打頭陣的, 它會把災難一步一步地導引過來, 說不定, 馬上會把我家屋頂的茅草掀個底朝天。
那些在大人嘴里說出的和還沒有說出的災難, 會不會趕在北風之后降臨?
又會以怎樣的方式降臨呢?
我在那個時候已經知曉, 春天生長萬物, 夏天萬物生長, 秋天是果實入倉的季節, 只是該收獲的東西早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冬天是我們暫時離開土地的季節。 沒有了土地的哺育和庇佑, 災難就鉆了空子。
昏暗的角落里, 小小的我, 翻江倒海, 絕望而自虐, 然后,我看到了接下來的一幕。
我的媽媽, 她從房間里搬出一個碩大的洗腳盆, 端正地放在堂屋的正中, 她從土灶的大甕缸里舀出比平時多得多的水, 慢慢地澆下來, 坐穩, 卷起褲腳, 將雙腳優雅地探進去, 直至兩只腳全部伸進熱氣騰騰的水里。 媽媽的臉上浮起難得一見的滿足感。水是讓人感覺如此親近和溫馨的東西, 何況是冬天夜晚的熱水,媽媽開始用兩只腳認認真真地互擦起來, 腳與腳、 腳與水相擊而發出響亮的、 咕嘟嘟的聲音。
我詫異地看著媽媽, 像看著一個陌生人, 媽媽盯著那雙被燙得通紅的雙腳, 像在鑒賞一件藝術品。
令我更加意想不到的是, 繚繞的水汽中, 突然飄出幾句歌聲。要將快樂進行到底的媽媽, 她用特有的腔調, 哼出一些短促的、不成曲調的旋律。 我看見晦暗的煤油燈, 仿佛亮了起來。
無論是之前的懵懂記憶, 還是之后的漫長歲月, 母親基本上是不唱歌的, 相較于父親磁性的嗓音、 準確流暢的曲調, 她明顯遜色很多。 客觀地講, 母親是五音不全的。
這五音不全的歌聲傳達給我一個巨大的疑惑, 母親怎么會在這種萬家憂慮的時候反而唱起歌呢?
她不合時宜的高興多么令人費解啊!
母親因何而高興?
她究竟想要表達什么?
然而, 歌聲卻又適時地點醒了那個倚在墻角的木訥的我, 我要趁著歌聲飄揚趕快去做點什么事情。 我怕歌聲轉瞬即逝。 事實上, 歌聲卻還在斷斷續續地綿延。 我趕快打水洗好腳, 一聲不響地爬上了床, 就在我鉆進被窩把身體安排妥帖的那一刻, 歌聲戛然斷在了隔壁的堂屋中。 可是又有什么關系呢? 被歌聲灌溉了的小屋, 如同被炭火焐熱了的冬天, 一切災難和不幸都將被擋在門外; 無論北風如何肆虐, 我們的家, 都是生長希望的地方, 也終將在平穩安然中迎接春天的到來。
我一夜長大, 腦海里突然滋生出許多繽紛的念頭。 我想起我家屋后面那口一年未干的塘坳, 應該麇集了很多魚吧, 我明天就邀上二哥去筑圍堰, 我會一臉盆一臉盆地把水舀干, 只要一個上午的工夫, 就可以把滿滿一桶魚送到媽媽的跟前。 我家屋前面這口幾十畝的大水塘, 在收羅和沉淀了一年的落葉之后, 塘底該生出了一層厚厚的蝦米, 我要將一只爛籮筐用麻繩系上, 把蚌殼敲開, 再將蚌肉放進籮筐里, 沉入水底, 等拉上來時, 必會看見一筐傻傻的蝦米鋪在籮筐底下。 春天來時, 我還可以帶上我的釣鉤, 去水邊尋找那些口吐泡沫準備產仔的鱔魚, 等我釣滿一水缸的鱔魚, 天麻麻亮時, 我就跟二哥一起把它們提到鎮上去賣。 聽說女貞樹的籽也可以賣錢, 我要趁天晴, 把屋角那兩棵女貞樹的籽一顆不留地摘下來, 曬干后, 用麻布袋裝好。 我甚至想即刻就翻身起床, 把這些話告訴媽媽, 我們有沉默無私的土地和河流,它們永遠慷慨, 值得信賴, 饑餓又怎么可能有機會找上門來。 當我激動地一遍遍構思我的計劃時, 我對黎明的到來忽地充滿迫不及待的憧憬。 同時我還發現, 眼角癢癢的, 有眼淚在爬行, 它們穿越臉龐, 流經耳廓, 最終無聲無息地鉆進我頭下的枕頭里。
在本應成為童年最黑暗的一個晚上, 在我稚嫩而脆弱的一顆心急劇沉淪的時候, 我的媽媽, 她用歌聲, 將我拯救。
事實上, 在未來的日子里, 更大的艱難和挫折接踵而至的時候, 我可以肯定地說, 我的母親并不是一個樂觀主義者, 甚至完全相反。
等我后來長到足夠大并開始走向成熟的時候, 我才意識到,一個人抵抗災難的力量其實來自童年。 而更多的時候, 我的整個童年都處在一種逃離的狀態。 我想逃離有時沉悶但更多時候又充滿爭吵聲的家庭氣氛, 我想逃離親戚之間那種被利益牽制的虛偽的關系, 我想逃離被所有人期待必須考出最好成績因而再也沒有時間親近大地的學校, 我想逃離班主任不明所以冷冷看我的眼光。 這種逃離的心態使我沒法安穩地呆在童年, 因而, 光陰也隨之顯得過于冗長而拖沓。 當我終于意識到我最終沒有辦法逃離古老偏僻的故鄉時, 一張突兀的門旋即把童年關在了身后。
現在, 我住所的后面, 有一大片人造的竹林, 規規矩矩地種著粗細不一、 高低不等、 疏密相間的竹子, 自然, 風被逗引來了。 可是, 城市里養育不出童年時代那么霸道的風, 它們游戲一般在竹葉間穿梭。 鳥也來了, 但比起童年時代逆風中奮力飛翔的小鳥, 這些城市的稀客顯然有著一種養尊處優的貴族氣。 這片人造的風景, 永遠上演詩情畫意的平和。 平和的風景是我喜歡的,它們永遠那么熨帖和標準。 可是, 在風景的深處, 我總是能聽到一個年紀尚輕的女子在昏暗的煤油燈下唱起歌來。 她優雅地擦著腳, 慢鏡頭一樣, 不動聲色地與黑暗對峙, 與我心底無邊無際的絕望對峙, 與即將到來的災難對峙。 時間凝固, 停止流動, 世間的人和事退到毫無意義的夜之深處, 給這歌聲作背景的, 是窗外嘯叫的北風, 它們拼命地搖撼著一林密密的楠竹, 用一種千年如斯的、 洪荒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