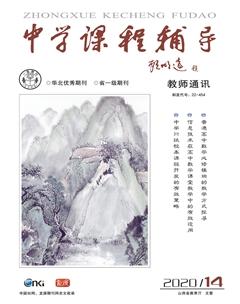從《歸園田居(其一)》感受陶淵明的精神次序
原俊義
【內容摘要】《歸園田居(其一)》昭示了陶淵明矛盾的心路歷程:有著決絕的態度,卻邁著踟躕的腳步;筆下是詩意的生活,面對的卻是殘酷的現實;看似淡淡的喜悅,卻有穩穩的幸福。《歸園田居(其一)》昭示了一個不得安寧的靈魂。
【關鍵詞】陶淵明 心路歷程 矛盾道家文化
陶淵明是偉大的詩人和辭賦家,為人所贊嘆的山水田園詩的創始人就是陶淵明。在山水田園詩中,詩句清新淡雅,給人意韻悠然之感。然世人多從其詩歌中發掘深遠的詩意,卻很少了從詩歌的意象里燭照陶淵明的精神世界。殊不知詩歌不僅是文學的,更是精神的。文字是一個人的精神表達,現在就讓我們一起,從《歸園田居(其一)》中領悟深藏于其中的詩人陶淵明的思想情感。在《歸園田居(其一)》中,昭示了一個不得安寧的靈魂,陶淵明在現實和理想的沖突中詠嘆、煎熬;又掙扎著試圖超脫痛苦,突破心靈的困境。
一、決絕的態度,踟躕的腳步
陶淵明為什么回歸田園?可以從內因、外因兩方面總結。在《歸園田居(其一)》中的一句詩娓娓道出了緣由。“少無適俗韻”是陶淵明說自己在小時候就仿佛與世俗人間格格不入,不愛這熱鬧的世俗。“性本愛丘山”是說自己天性就說這般,喜愛自然是天性難掩。“守拙歸園田”是說帶著自己的拙見歸往田園自然之中,不勉強地混于俗世。這些是回歸田園的內因。
陶淵明所在的官場則是他歸隱田園的外因。他有兩個比喻形容官場:“塵網”、“樊籠”。“塵”字乍然便想到了“灰塵”、“塵土”,有污濁之感,而“網”字仿佛牢籠,使人難以掙脫。“樊”與“籠”兩字意義相同,指被禁錮在一方天地之中,失去自由。陶淵明對于自己曾身處的官場,則用了“羈鳥”、“池魚”來進行指代。羈鳥受縛,難以徜徉天際;池魚被阻,難以暢游海洋。
陶淵明在字里行間流露出辭官的堅決。可事實卻并非如此。在他六十一年的人生歷程中,有十三年是在官場度過,仕、隱徘徊多達五次。公元393年,陶淵明初入官場,擔任了江州祭酒一職,但未久便“不堪吏職,少日即解歸”。在公元400年他再次出仕,在荊州府做屬吏。不久以丁憂為由辭官。而后在公元404年再入官場,于劉裕幕下擔任參軍一職,后又加入了劉敬宣幕府擔任參軍。公元405年,任彭澤令,最后“不為五斗米折腰”離開了仕途。
現在態度如此決絕,可當初為什么一錯再錯,“一去三十年”呢?中國士大夫大多受儒家思想影響。陶淵明少時就“猛志逸四海”,陶氏一族又有尊崇儒學的家風。入世思想早已融入陶淵明的血肉,積淀成他深層的心理機制。因此他走上仕途是必然的。
陶淵明熱愛自然的本性看似是與生俱來,但事實上是他宦海沉浮后的突然醒悟。在初時有“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如今“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這是一種的挫敗后的醒悟,是在宦海煎熬中形成的智慧結晶。可以說,陶淵明告別官場的過程就是他不再迷茫,發現自我的過程。
二、詩意的生活,殘酷的現實
置身官場的陶淵明,如同籠中鳥、池中魚,困頓不已,世人言“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之于陶淵明來說,“海闊”、“天高”之處就是園田居。園田居是一個怎樣的地方?
“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是對住處的簡單勾勒和描繪,表達了盡管住處不甚華麗,只有“草屋八九間”,但是房舍有榆柳樹的綠蔭遮蔽、桃李點綴,也是素雅淡然。“蔭”意為庇護,樹木枝繁葉茂,似乎善解人意,為主人家提供清涼。“羅”有排列、主動呈現之意,樹木似乎主動排列在堂前。可見,陶淵明由衷地喜愛園田居,愛之不足,將樹擬人化,寄托情感。“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曖曖”意為模糊,畫面呈現一種朦朧美。“依依”是指輕柔而緩慢飄升,畫面呈現一種輕柔美。“墟里煙”描寫的則是農家的煙火氣,給人以溫馨自然的感覺。“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犬吠雞鳴之聲在無意中為畫面增加了勃勃生氣,動靜相宜,以動襯靜,顯得幽靜祥和而不冷清,宛若《桃花源記》中的世外桃源。
但是這真是桃花源一樣美好的地方嗎?詩中言“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其中的“十余畝”、“八九間”是多少呢?東晉大族田產以“頃”計算,按“畝”計算田產只能算普通農戶水平。東晉“十余畝”相當于今天的七畝左右,七畝田對于陶淵明這七口人的家庭來講,委實不算太多。其中的“八九間”的房屋,換算過來,也大略約當下的八九十平的房子左右,實在是不算太大,甚至有些許狹小。因此從這些內容的實際分析上來看,所謂的園田居即是陶淵明的現實生活的一部分寫照,這些在當下看來并不好的生活條件,在陶淵明看來,卻已經是“不小”、“不錯”了。
詩歌描繪的并非真實的田園生活場景,而是經過陶淵明心靈選擇、創造的田園圖景。正如榮維東教授所說,“文學藝術對生活的表現是一種審美觀的映照,是對原生態的生活的藝術加工。作者從現實中提攝現象,進行選擇、組合、變異,融入主觀情思,從而生成與真實的現實有一定距離的新形象。”
魏晉是一個個體意識普遍覺醒的時代。覺醒的士大夫紛紛高蹈人格獨立,勇敢追尋內心自適,抗拒異化自我的力量。陶淵明正是其中之一。描寫詩意的田園,不僅象征陶淵明審美靈魂的激活和感官的復蘇,更是對自己誤入官場自我迷失的撥亂反正。一言以蔽之,回歸田園的過程是陶淵明詩意棲居,重新塑造自我的過程。
三、淡淡的喜悅,穩穩的幸福
而回歸田園后的陶淵明生活狀態如何呢?在《歸園田居(其一)》中的四句詩將他的生活狀態淋漓盡致的刻畫出來,“戶庭無塵雜,虛室有余閑。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在這四句詩中,一經閱讀就能夠感受到陶淵明的輕松和愉悅,在字里行間,都透露出了陶淵明的輕快和自然。但是細細探究,正如高爾泰所認為的那樣,藝術家們即使是在最快樂的時候,在他們的內心深處,還存在著隱秘的不安和躊躇。仔細閱讀品味,你會發現陶淵明在圓滿的生活里追求著更高的人生價值,淡淡的喜悅的背后蘊藏著他那穩穩的幸福。
“戶庭無塵雜”,“戶庭”表面是指室內庭院,實則指向陶淵明的精神世界。“塵雜”不僅指灰塵,更指塵俗雜事。擺脫了俗世的雜物的陶淵明,潔凈的庭院與寧靜的心靈相映成趣。
“虛室有余閑”,“虛室”不能只從字面理解為空蕩蕩的房子,它有深刻的文化內涵,它是莊子的心齋哲學的鮮明呈現。在《莊子·人間世》中有云“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虛者,心齋也。”所謂的“心齋”是內心的寧靜、虔誠和心無旁騖。要如何才能在這俗世之中保持寧靜、虔誠和心無旁騖,做到“心齋”?郭象在閱讀到《莊子·人間世》中的“瞻彼闋者,虛室生白。”時,曾為此標注,他認為“闋”就意味著“空”,即空明。“室”則是喻指人的內心,心能空虛,則純白獨生。“瞻彼闋者”的意義就說說要達到一個“空”的心境狀態。“虛室”即指內心不雜糅無謂的欲念,內心純凈,“生白”意為光明綻放而后化為一片純白,即為“生白”。故而“虛室生白”即是指內心空明,無雜糅的欲念,保持空明、自然的心境而后得到一片光明。因此,“戶庭無塵雜,虛室有余閑。”就代表了陶淵明想要除去自己世俗的欲望,想要做到“無欲無求”,內心淡泊。
作為中國文學史上一個特別的存在,陶淵明在世俗中的沉浮和經歷,值得我們細細體味,他在世俗之中找到了自己真正的追求和思想的桃源,并獲得了超越平凡的精神追求和永恒價值。我們可以從《歸園田居(其一)》著手,仔細揣摩詩中的每一句詩,揣度陶淵明在仕與隱之間的徘徊和猶豫,體會到身處于那個境地之中所需承受的痛苦和尖銳的矛盾,深刻地領會到陶淵明對于自然和人生理想的永恒追求和不懈探索,這也正是陶淵明能夠不朽于世,陶淵明的精神能夠得以流傳的真正原因。
【參考文獻】
[1]方智范.語文教育與文學素養[M].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5.
[2]樓宇烈.老子道德經校釋[M].上海,中華書局,2008年.
[3]榮維東.語文文本解讀實用教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作者單位:無錫市玉祁高級中學)七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