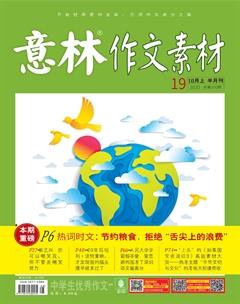誰知道夜幕后邊,藏下了那么多歡樂
小小波:或許是出生在秋季的緣故,每到九月,總讓我格外想回到故鄉,回到那個金燦燦一片忙碌和收獲的村子。大學時,偶然在圖書館看到張煒的《九月寓言》,讀完第一段話,農村那種自然蓬勃、野蠻生長的熟悉感便撲面而來,深深勾起我內心深處對故鄉的思念和熱愛,或許這就是我的“鄉愁”。借回宿舍,一個人關在屋子里一邊閱讀一邊忍不住流淚的場景,八年后依然記憶猶新。又一個九月里,重讀此書,里面純粹、熱烈的情感,依然讓我熱淚盈眶。這本書被評價為與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福克納的《八月之光》有著殊途同歸、異曲同工之妙。又一個秋天來了,我想將這本魔幻現實主義小說推薦給你,即便遠離土地、遠離農村鄉野,也能和我一起感受來自鄉村的熱烈,一起觸摸那份濃得化不開的熾熱,一種人類生存的原初狀態。
NO.01圖書簡介
《九月寓言》是個寓言性質的故事,形式上接近童話。但這個童話世界和我們的現實世界不是直接對應象征的,它是另外一個世界,完全獨立的一個特定的世界。作者刻意模糊了故事的時間背景和地點,但通過小說中“憶苦思甜”“工人階級”這樣的詞語和“紅小兵”這類名字,我們可以大致將時間推測為中國革命戰爭年代和社會主義建設初期,地點是作者的老家山東海邊農村。
《九月寓言》實際上是一個跑和停的故事。小說虛構了一個小村,以村里的姑娘肥與其丈夫挺芳的視角切入,在十幾年后的某一天,面對著荒蕪的小村與廢棄的碾盤,展開對小村過往的回憶。這個從遙遠的異地遷徙來的小村里,人們多少年來一直保留著一些特殊的生活習俗和行為特征,因而被本地人嘲弄,被叫作“?鲅”(一種海里的毒魚),可理解為諧音“停吧”,相當于村民停留在當下的生活狀態中。小村的生活寧靜而熱烈,九月是一個獨特的月份,是小村人賴以生存的地瓜收獲的時間,他們被地瓜養育著,火紅的地瓜填飽了肚子,也蘊蓄了灼人的內火——“瓜干燒胃哩!”于是,黑夜里,大姑娘小伙子在野地瘋跑,漢子們在炕席上讓老婆拔火罐、打老婆;土里刨食的人卑賤又桀驁,受盡苦難也活得有滋有味……小村有三樣被視為珍寶的東西,一是漂亮、結實的大姑娘趕鸚,她非常善于奔跑,是小村夜晚奔跑的孩子們的首領,由于她,小村的青年們晚上才有了事做——奔跑;二是趕鸚的爸爸紅小兵用地瓜蔓子釀的酒,使得整個小村充滿醉醺醺的氣氛,這種氣氛使停留的狀態令人迷戀;三是癡女人慶余“發明”的由發霉地瓜做成的黑煎餅,這讓開始以地瓜為主食的小村的吃食有了更大的保障。除此之外,還有老舊碾盤邊憶苦的習俗,這是小村人集體的冬夜生活,是他們的唯一的精神生活。憶苦思甜基本上由兩個人來進行,一個叫金祥,一個叫閃婆,一男一女。他們的苦處都是怎么樣從很遠的地方奔跑而來,怎么千難萬險,然后提醒大家如今的停留狀態是非常幸福的。小村附近有個煤礦工區,礦井在小村的地下縱橫交錯,四通八達,形成了另外一個世界,和上面的世界很不相同。首先,它非常黑,靠燈光照亮,沒有日光。其次,他們不吃紅薯,他們的食品是黑面肉餡餅。工區慢慢向小村靠近過來以后,小村的雞就變少了。村民想到的是工區的人來偷雞了,所以他們很諷刺地稱工人階級為“工人撿雞兒”。最終因為煤礦巷道穿透了地表,那富有象征意味的小村,終于悲壯地沉落了……
《九月寓言》像一曲寓言化的長歌,它凝聚了張煒對那塊土地的赤誠,贊頌著與土地萬物密切相關的、生命自身蓬勃生長的精神。
NO.02作家其人
張煒,1956年11月出生于山東煙臺龍口市,當代著名作家。1975年發表詩,1980年發表小說。長篇小說《古船》獲得人民文學獎。《九月寓言》獲得全國優秀長篇小說獎,并入選《百年中國文學經典》。小說《你在高原》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其作品被譯成英、日、法、韓、德、瑞典等多種文字。莫言評價張煒是這個時代作家里勤奮的勞動者、深刻的思想者、執著的創新者。
NO.03精彩選讀
第一章 夜色茫茫
肥沒法忘掉趕鸚,正像沒法忘掉自己是個“?鲅”、沒法忘掉那些夜晚一樣。那一夜一夜的游蕩啊,究竟從哪一天開始?如果沒有趕鸚,如果沒有冬天里的一場病……那個冬天肥病得好重,母親把屋檐下的草藥取下來煎水給她喝。喝了三天沒見好,只得求紅小兵出村請來赤腳醫生。……醫生拍了她(臀部)一下:“?鲅!”隨著那一下拍打,酒精溶液嘩嘩流下,一支長針猛地插上去。肥嘶叫了一聲,不顧一切地沖出門去。針頭在身上顫動,她懷著無限憤怒拔掉了它,擲到了黑夜的泥土上。
是的,就是從那個夜晚開始,她進入了奇妙的游蕩。午夜星空明亮,沒有月亮也沒有云彩。嚴寒沒有使她畏縮,反而令她大口地吸氣。從門口到街西碾盤那么短短一段路上,她竟覺得病全好了。萬籟俱寂,清風拂面。……媽媽一個人蜷曲在西間屋里睡著,花白的頭發搭在油黑的枕頭上,像撲散的楊樹花兒。她想看看女兒怎樣被年輕的醫生治好,就一直伏在門框上。醫生轉過臉來呵斥道:“多么分散精力!”媽媽的頭像小孩子那樣一縮,弓著背走開了。她還睡著,她的女兒跑到黑夜中去了。……有什么順著肥的腳背爬上來,肥把腳用力一甩,那東西飛到了遠處。等她把腳收回來,卻被什么揪住了。
肥那個夜晚被人拉下來,直拉到碾盤下面的空隙里。她沒有反抗,因為她聽出那人是個姑娘——令人吃驚的是,這時候還有人出來玩。她安靜下來,認出是趕鸚。她說:“真能鬧!”趕鸚說:“沒想到是你。你晚上也出來啊?”肥一聽就明白趕鸚夜間總是出來玩。趕鸚拉著她鉆出碾盤,告訴她,村里一伙年輕人差不多每夜都跑出來玩。“怎么玩呢?”“胡亂玩唄。”她說著四下張望,“不知他們這會兒躲到哪兒去了。走,我領你找他們去——也許他們在哪兒睡著了哩。”趕鸚拉著肥的手,走過村子南邊的小沙崗子,又走進小榆樹林子。最后趕鸚說:“在大草垛子里!”她估計得不錯。她們扒了幾下,一些麥草滑落了,露出一個黑深的洞口。兩人鉆進去,七拐八彎,才聽到很多人在笑。趕鸚說:“多熱鬧,俺!”
誰知道夜幕后邊藏下了這么多歡樂?夜晚是年輕人自己的,黑影里滋生多少趣事。如果要懲罰誰,最嚴厲的莫過于拒絕他入伙——讓他一個人抽泣……咚咚奔跑的腳步把滴水成冰的天氣磨得滾燙,黑漆漆的夜色里摻了蜜糖。跑啊跑啊,莊稼娃兒舍得下金銀財寶,舍不下這一個個長夜哩。……年輕人的事情早晚也瞞不過老人,他們聽著深夜街巷的腳步聲就議論起來,都說:“瓜干燒胃哩……”
【讀書筆記】趁著月色在村野之中奔跑,曾是農村孩子兒時最快樂的事。在無所事事的夜晚,它讓你對村子的每一個角落都熟悉起來,也讓你跟村外的野地聯系起來。你的周圍是你親密的同伴,你會覺得你是大地上最自由的活物,想去哪兒就去哪兒。這就是你愛著且回不去的童年、故土。所以當書中的人物做著同樣的事時,你的那份熟悉的感動自然而然就涌現出來。
第二章 黑煎餅
1
那時候的事就像在眼前一樣。人們出工回來,常常發現村子南頭的楊樹下站了一個破衣爛衫的女人,牽著一條狗。秋天里并不冷,可是她衣服上的破棉絮拖拉到下身。真是個古怪的女人哪。她頭發上粘滿麥草,也許夜間鉆進那個大麥草垛子里睡覺。她吃什么東西?誰也沒見她伸手討要。有人說秋天了,九月里田野上什么不能吃,只要撅著屁股彎下腰往土里一扒拉就行。……
出工的人們圍著她說亂七八糟的話。“你今年多大了?”臟女人咯咯笑:“二十八,騎大馬。”金祥提著褲子站在一邊,說:“聽她說話哪像癡人?苦命人倒是真……聽口音,千兒八百里外有了。”大家都不吭聲了。臟女人又說:“你打我,我就腫,會做針線會攤餅。”(村長)賴牙沖金祥嘿嘿笑了:“行啊,是個老婆料子。”賴牙問:“你叫什么?”臟女人答:“我叫慶余。”“嗯,這個名兒不錯。走吧慶余,跟我們去地里做活兒不行嗎?強似天天站著。”臟女人眨著糊了灰土的眼皮:“下地干活咱不愁,不過誰牽狗?”金祥說:“我牽哩。”他真的接過黃狗,帶上臟老婆一塊兒往前去了。
地瓜田望也望不到邊。分割田地的只是一些干涸的溝渠,里面紫穗槐和雜草繁茂。太陽熱辣辣懸在天上,地瓜葉兒打蔫了。這天要做的活兒還是刨地瓜,一直刨下去,刨到冰天雪地的季節。有人遞給臟女人慶余一把鐮刀,讓她隨大家一起割瓜蔓。她的鐮刀使得挺熟,一看就知道經常做活。賴牙說:“嘿嘿,是個有用的人。”
一群老婆婆跟在男人后邊,用一把銹刀切瓜干。她們每人帶一塊柳木板子,把剛刨出來的地瓜切成片片,然后攤在泥土上。瓜干經過幾個晴天曬干了,那就是村里人一年的吃物。秋天是收獲的喜慶日子,也是出禍患的日子。如果瓜干在變干之前挨上一場連陰雨,那么瓜干就變成灰色、黑色,咬一口苦澀澀。“老天爺今年讓咱吃苦食啦。”滿村里的人都這么喊。每個秋天都要遇上連陰雨,這是莊稼人的命啊。……
2
每年九月都躲不開的雨啊。一地的瓜干眼看著半干了,嘩啦啦一場雨落下來。全村男女老少都在雨中奔跑,嚷叫著,像求饒一樣。……天晴了,一地瓜干都變了色。到地里走一趟,到處是淡淡的醋味兒和酒味兒。有的瓜干爛得厲害,煮熟了喂豬,豬都不吃。就是這樣的瓜干也舍不得扔,照樣得收好,像往常那樣裝到紫穗槐囤子里。剛開始吃的時候肚子發脹,吐酸水,慢慢就好多了。碾盤上每時每刻都忙得很,家家排隊碾瓜干,碾成碎塊做干飯,碾成末末做糊糊。手巧的人家用黑地瓜面烙餅做面條、包白菜水餃,都沒法驅除苦臭味兒。那顏色跟土一模一樣。晚上躺在炕頭,肚子里火燒火燎,不停地翻身。“燒胃哩,燒胃哩!”第二天早上走上街頭,見了面都這樣嚷叫。
也就在這樣的日子里,慶余在小土屋里搗鼓出了奇跡。
她把一塊碎裂下來的瓷缸瓦片凸面朝上支起,陶盆里的瓜干黑面已經悶了半天,用水調弄得不軟不硬,散發出微微的酸甜。瓦片下不緊不慢地燒著文火,金祥一把接一把往空隙里揚麥糠,大股濃煙嗆得他淚流滿面。慶余用食指蘸一點兒唾沫描一下光滑的瓷瓦面兒,吱地一響。她伸手挖一塊面團,在手中飛快地旋弄旋弄,然后左手抓一塊油布擦擦瓷面兒,右手迅速地把面團滾一遍,一層薄薄的瓜面粘在了瓷瓦上。她趕緊取起泡在水里的一塊木板,用鈍刃兒在那層瓜面上刮。刮呀刮,刮呀刮,瓜面兒實實地貼在瓷瓦上,接著干了,邊兒翹了!她用殺羊的長把刀插進翹縫,像割韭菜一樣哧哧兩下,整張的小薄餅兒就下來了,比糊窗紙還薄。這些黑色的美麗的薄餅一會兒擺成了一尺高,金祥在一邊揀碎的邊邊角角吃。一陶盆瓜面都做完了,小土屋里有了整整兩大摞子小薄餅。慶余像做針線活兒一樣盤腿坐下,左手取薄餅,右手的殺羊刀一按一折,唰唰兩下,疊成了長方形。那個快哩!金祥快要樂瘋了,問:“年九媽,這是什么餅?”慶余閉著眼:“煎餅!”
瘦長的年九第一個叼塊煎餅跑上街頭,震動了全村。誰見了都問,問過還想咬咬。年九讓他們嘗,他們嚷:“哎喲這個脆呀!哎喲這個香呀!”正喊著金祥提著褲子踱出來,嘴里照樣叼個煎餅。人們說:“該死的金祥啊,好東西都讓你家吃了。”大伙兒一陣感慨:“吃著黑煎餅,摟著癡老婆,人家金祥過的才算日子!”一個老婆婆說:“快別說人家癡了,不癡的人也沒見做出這么好的餅來。”大家都不作聲了。了不起的慶余,她傳過來的手藝使一囤囤的瓜干有了著落。莊稼人心里一塊石頭落了地,禁不住長舒一口氣。……
大約過了兩個月,每家每戶都有了會做煎餅的人。了不起的吃物啊,莊稼人有了發明創造了。這功勞自然而然歸到了慶余身上,也歸到了收留她的金祥身上。后來慶余才告訴男人:在南邊黑乎乎的大山后邊,人人都會做煎餅。……她又說南邊攤餅可不用破瓷缸片,都用平底兒鍋,那是過生活的寶物啊,叫“鏊子”!天哪,鏊子鏊子,怎么不早說!金祥搓搓手,說他起早貪黑走長路,翻山越嶺也要背回一個鏊子——天底下還有這樣古怪物件!他說到做到,第二天,往腰上捆了一摞煎餅,雞叫第一聲時上路了。
【讀書筆記】食物是最重要的東西,在看天吃飯、沒有什么現代化技術的年代,因為天氣,人們只能眼睜睜看著即將收獲的一年的口糧壞掉,這種心痛,有過類似經歷的人一定能體會得到。而即便是物質豐富的今天,我們也還在提倡節約糧食,因為書中的那種艱苦,是上輩人經歷過的現實。我們也并非一定不會再遇到困難,書中人對食物神圣的態度,應該能給我們些許思考。
NO.04精彩書評
王安憶:《九月寓言》的心靈世界
□王安憶
《九月寓言》的世界絕對不是我們所熟悉的公認的現存世界,它是獨立的,有自己的邏輯,這個邏輯順理成章,但不是我們這個現存社會的邏輯,而它所使用的材料非常具體。比如憶苦思甜,使用了現實生活里的概念和形式。另外,工區和小村的關系,也是用了現實社會里工業化發展過程中的一些形態。它使用一些非常政治化的用語,比如,肥想自己是那樣的又白又肥,而她父母是吃不飽的,自己怎么能夠這么胖的?想了許久,她想起了一句革命歌曲:“陽光雨露,撫育我們茁壯成長。”這本書絕對不企圖象征什么,諷刺什么,對應什么,批評什么,它絕對不是那么狹隘的。它就是用我們的現存世界來創造一個特殊的東西,為此采取了童話式的手法。你會覺得小村和工區的人都非常孩子氣,或者說是動物化。比如憨人爸彎口的形象:“他的臉長得非常可愛,他的五官好像前面有只無形的手把它用力揪了一下。他吃煎餅的樣子是那么專注,再在自己的嘴上插一桿蔥,看上去像只老兔子。”《九月寓言》所描繪的一切都帶有一種奇異的狀態,但這些狀態的細節卻是我們所認識的具體現實的細節。張煒把這些已經成型的東西打碎,再重新組織起一個寓言世界。
《九月寓言》經過退稿,最終被接受時,出版社對它不得不抱了懷疑態度,不知道它好還是不好。我心里很難過,好和不好是那么清楚地放在我們的面前,可是很多人都不清楚。
(摘自《小說家的十三堂課》上海文藝出版社)
張煒:大地守夜人
□張新穎(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九月寓言》所寫,既不神秘也不玄虛,那是最實在的生活。為數不少的當代人因為遠離這種生活而不能理解、不能感受這種生活,像張煒說的那樣,“實際上這本書更接近很多人的鄉村生活回憶錄。”即使這樣的情景不存在于個體的記憶中,它也應該而且一定存在于一個種族、一個民族甚至是整個人類的歷史記憶中,我們人類就是從這里、從這樣的情景中走過來的。也許,我們已經走得太遠了。
張煒想表達人對于自我根源的尋求,而自我的根源也就是萬物的根源,即大地之母。
(摘自豆瓣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