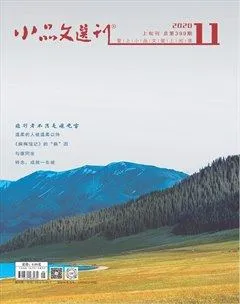《病梅館記》的“病”因
陳世旭
有清一代文學家,龔自珍是我印象較深者之一。他像一顆耀眼的流星劃過晚清晦暗的天空:27歲中舉,38歲中進士,48歲辭官,次年暴卒,享年不足半百,因其思想的精銳和著作的成就被譽為“三百年來第一流”(柳亞子語)。其名句“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和“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從小就耳熟能詳。
散文《病梅館記》則是我記憶最深的一則小品。
《病梅館記》寫了盛產梅花的江浙一帶當時的一種風氣:
為了迎合梅“以曲為美”“以欹為美”“以疏為美”,而“直則無姿”“正則無景”“密則無態”的觀點,有人把這種好惡作為品梅的標準,告訴賣梅的人,“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夭其稚枝,鋤其直,遏其生氣”,即砍掉端正的枝干,培養傾斜的側枝,除去繁密的枝葉,甚至折斷嫩枝,阻礙它的生長,來謀求大價錢。于是那一帶的梅都成了病梅。
文章用語辛辣,表現形式和手法極是特殊。段段寫梅,處處寫梅,通篇寫梅——產梅之地、夭梅之由、嘆梅之病、療梅之志之法,夾敘夾議,透過植梅、養梅、品梅、療梅的生活瑣事,由小見大,寫的是“梅”,重點在“病”。
姑且不論這篇寫于鴉片戰爭前夕的文章是怎樣的借題發揮、托物言志,也姑且不論這種與婦人纏足惡習無異的審美情趣是多么扭曲變態,僅僅就是這種把某一類人的好惡作為標準,“以繩天下之梅”,將“天下之梅”“斫直”“刪密”“鋤正”的做法,就大可討論。
物質產品必須“標準化”,而精神產品必須千姿百態,這是誰都認可的道理。
與《病梅館記》寫作相距三年,遠在歐洲的馬克思發表了《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酣暢淋漓地質問:你們贊美大自然令人賞心悅目的千姿百態和無窮無盡的豐富寶藏,你們并不要求玫瑰花散發出和紫羅蘭一樣的芳香,但你們為什么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只能有一種存在形式呢?
沒有證據表明馬克思讀過《病梅館記》,但他們觀點的實質驚人地相似。唯一不同的是,馬克思筆下的普魯士還能“贊美大自然令人賞心悅目的千姿百態和無窮無盡的豐富寶藏”,而龔自珍筆下的“文人畫士”卻“有以文人畫士孤癖之隱”,以賺錢為誘惑,強行要求鬻梅者“斫”“刪”“鋤”,刻意制造“病梅”。這就等而下之了。
循著這樣的思維邏輯,進入社會層面,必然導致對個性的扼殺乃至對人才的戕害。
《病梅館記》進一步指出:“才士與才民出,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于僇之”“徒僇其心,僇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為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只要出現了有正氣有才能的人,就加以督責、束縛、摧殘、扼殺,斫正刪密鋤直,從而排斥剛正之士,剪除有用之才,阻遏蓬勃生氣,豢養奸佞邪惡的小人。由此,作者激憤地抨擊:“文人畫士之禍之烈至此哉。”這里的“文人畫士”自然指的是走狗幫兇。
“予購三百盆,皆病者”,為病梅而“泣之三日”,特地開設一個病梅館來貯存它們。作者由病梅寫到病梅館,最后用“嗚呼”引出議論。發愿“誓療之”——假如“多暇日,又多閑田”,就要“廣貯……病梅”,“窮予生之光陰以療梅”,“毀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縛”“縱之順之”,在最短的期限里,“必復之全之”,一定要在完全自然的狀態下使它們恢復,使它們完好。為此,“甘受詬厲”,誰愛罵就罵去吧。
龔自珍對病梅的“誓療之”明顯有一種堂吉訶德式的悲劇感。且不說他的“生之光陰”是那么有限,就是他能長命百歲,憑他一人之力,又能救得了多少病梅呢?
但不管怎么說,這樣的悲劇感是令人尊敬的。
選自《今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