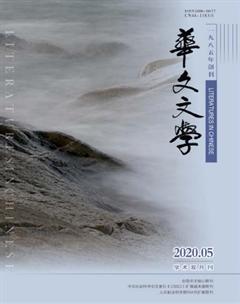從商業敘事到族裔發聲
陳連貴
摘 要:溫妮弗蕾德·伊頓的《紫藤之戀》作為20世紀初通俗小說,從羅曼司體裁、敘事元素到最終呈現均定位準確。作為美國華裔混血女性作品,該作品體現了作者對少數族裔女性處境和消費主義思潮的觀察和體悟。馬克思主義闡釋學堅持文本的語境化,挖掘形式和內容運動的潛在推動力,通過文本的政治無意識把握壓抑和掩埋了的歷史欲望,《紫藤之戀》因此具有了宏觀和微觀相結合的解讀意義,以“異己”姿態呈現出不同于一般浪漫愛情故事的歷史格局,為美國少數族裔發聲提供了新形式。
關鍵詞:溫妮弗蕾德·伊頓;紫藤之戀;商業敘事;族裔;政治無意識
中圖分類號:I10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677(2020)5-0117-06
《紫藤之戀》(The Wooing of Wistaria, 1902)是美國華裔混血作家溫妮弗蕾德·伊頓的第二部長篇小說,也是她以筆名“Onoto Watanna”①出版的第二部日本題材小說。豪威爾斯稱贊伊頓的小說“清新、精致、真誠”,代表一股“反潮流的文學力量”②。但因其血統、出生地、主要活動地及其作品內環境的不一致,作者伊頓的身份定位一直模糊不清。若不是索爾伯格、林英敏等族裔文學研究者的重新挖掘,這位20世紀初名噪一時的流行小說作家及其作品也會隨歷史湮滅。
受《日本的梅子小姐》商業成功的鼓舞,《紫藤之戀》顯示了更為自信的文本操縱手段,從敘事元素的擇取和安排到最終作品的市場呈現,均體現了伊頓對20世紀初美國消費資本主義發展的準確把握,因此這部小說的敘事策略便成為認識美國社會思潮和作者本人時代性的抓手,推動情節發展的矛盾沖突也因此具有了文本之外的象征意義。以詹姆遜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闡釋學派堅持文本的語境化,挖掘形式和內容運動的矛盾推動力,綜合考量文本、作者和語境的互動關系,通過文本的政治無意識把握壓抑和掩埋了的歷史欲望。文學作為歷史的“預先文本化”形式,采取“隱蔽和偽裝的策略”為社會矛盾提供“象征性”的解決方案。因此,以馬克思主義闡釋學的方法對文學作品“去蔽”(Unmasking),能夠揭示文本生產和社會生產的互動關系以及潛藏于文本運動內部的意識形態的作用方式。
一、商業文本敘事策略
20世紀初的美國消費資本主義發展迅速,消費成為表現“國民性”的一種形式,是“日常生活中民族認同的重要儀式”③。物質產品的“有用性”讓位于“消費性”,美國民眾在資本主義的消費邏輯中重新定位“物性”,消費成為商品生產的主動力。文學生產也未能擺脫商品經濟的沖擊,作家開始積極介入文化實在,與出版機構、劇場、電影產業共謀共生;讀者群也經過精心識別,即時聯系得到制度化,實質已形成以文學作品為借口的需求狂歡。
《紫藤之戀》將故事置于19世紀50年代資產階級革命前夕的日本,描寫日本面對西方現代文明時國內階級矛盾沖突和男女主人公的曲折愛情,重點講述賤民出身的女主人公紫藤姑娘在身份被披露后女扮男裝參與革命,彰顯女性獨特力量的故事。這種將人物“移置到一個遙遠的地理空間、久遠的歷史空間或幻想的地理或歷史空間,與種族異己或性別異己為伴”,通過“異己元素重新認識和定義自我”④的文學形式似乎與20世紀初美國現實主義文學主流格格不入,然而豪威爾斯評價的“反潮流”卻恰是伊頓順應時代潮流的商業策略的反映。
《紫藤之戀》的讀者群體定位是中產階級女性。自19世紀50年代起,日益成熟的暢銷小說作品“非常直接地、多方面地反映了那個伴隨著新中產階級家庭行為規范的建立而出現的女性與家庭生活的新領域的需要和她們的心聲”,并促進“文學交換模式的進一步形成和具體化”⑤,使這一群體成為作家們不可忽視的推銷對象。作者伊頓寫作時美國女性運動方興未艾,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維多利亞性別傳統受到挑戰。這一時期,社會要求“女性恪守婦道操持家庭的呼聲有多高,女性尤其知識女性的自我意識和反抗精神就有多強烈”⑥。伊頓捕捉到女性身份革命的社會能量,在《紫藤之戀》中塑造了一位智慧、叛逆且具有獨立精神的女主人公紫藤姑娘。紫藤姑娘以不自知的“階層冒充”和主動的“性別冒充”聰明且大膽地追求自己的愛情。伊頓通過紫藤姑娘的種種叛逆行為和危機關頭表現出的不輸男性的智慧和把控能力,表達美國女性對社會身份的渴望,迎合了女性獨立思潮的主流。同時,紫藤姑娘對傳統女性自我和情感特性的堅守,也使美國女性看到了不同時期女權主義者宣揚的“真女性”和“新女性”統一而在的可能,作品的讀者群體得以擴大。
紫藤姑娘堅強且不失溫婉的特性其實也是所有伊頓日本題材小說主人公的共性,如此性格符合美國民眾對“真女性”的期待,更滿足了他們對日本烏托邦式的幻想。日本因美國的強勢外交而打開國門,“融入”現代文明的版圖,堅信“天命論”的美國民眾也以提攜落后文明的功臣自居。但在1876年費城博覽會之前,美國民眾還只是通過旅日作家的游記或其他有限的帶有東方主義色彩的文學作品了解日本,得到是“誠實友愛、真誠有禮、情感豐富、忠心守孝”⑦的封建小國的日本印象。費城博覽會精致的日本展品令美國民眾眼界大開,日本符號成為中產階級時尚和身份的代名詞,加上日本積極向西方學習進行現代化改革的態度等因素,日本逐漸擺脫美國人眼中的落后愚昧形象,成為精神品位和現代性的結合體。與日漸改善的日本形象相比,20世紀初美國民眾眼中的美國形象卻每況愈下。“揭露黑幕運動”曝光了壟斷資本主義野蠻發展導致的政治腐敗、商業欺詐和畸形民生,獲知真相的美國民眾對個人生存和國家命運憂心忡忡。《紫藤之戀》此時以羅曼司的形式出現,滿足了他們在文學中尋找暫時精神庇護的欲望。小說刻意加重對傳統日本自然和人物意象的描畫,在稱呼和慣用語上保留日語表達,著力傳達日本人獨特的忠勇脾性,最大限度呈現古樸的原初特征,以強烈的“異己”特性吸引美國民眾烏托邦式的認同。
然而,《紫藤之戀》不是烏托邦文學,“烏托邦突出表現一個總體社會規劃,全面描繪社會生活和社會組織。對比之下,堅持局部時尚理想或從不將它們納入理想社會的理論家決不是烏托邦的。”⑧伊頓不過是借著浪漫主義的傳統將現實問題文學化,讀者從中讀到的不是社會問題的“總體解決”,反而是“總體包裝”,讀者享受打開商品包裝窺視內里的愉悅感覺。《紫藤之戀》并沒有倚靠純粹的復古幻想說服堅信“命定說”的美國讀者。在真實的歷史中,司令官佩里率領軍艦來到日本,以“高等文化的代表”的霸權姿態強迫日本開埠通商,將“山巔之城”的光芒播撒至這個落后的民族。《紫藤之戀》幾近真實地描寫了日本國內各股勢力在西方強權面前的反應——保皇或保將、拒夷或迎夷、分裂或團結、隱藏或公開,各種矛盾無一不鑲嵌在先進文明駕臨的大背景中。可以說,小說對日本矛盾刻畫越深刻,越能喚起美國讀者的文化優越感。伊頓充分捕捉到了這股現代工業文明造就的東方主義意識并加以利用,表面上逆流而動的《紫藤之戀》其實擁有堅實的意識形態基礎。
敘事元素與社會思潮的一致是《紫藤之戀》作為流行小說的基本要義,其最終產品化的呈現則顯性地表達了伊頓與其他利益方的共謀關系。小說以引導性的“副文本”將既定文學功能放大。副文本是文本與非文本(off-text)世界聯系的“過渡區”,是“實用性和策略性主導的區域”,是文本向讀者呈現并“施加影響”的必然步驟⑨。《紫藤之戀》最惹人注目的副文本特征是作者親現的扉頁造型圖及同頁右下角的日語簽名“渡名おのと”,伊頓身著和服手捧書卷向右站立,視線、書籍和署名三點一線,暗示作者乃至小說主人公“知書達理”的溫婉氣質和“自立進取”的求索精神。漢字加假名的日語簽名則強化作品的異質性,能夠滿足美國讀者對探求東方世界神秘性的渴望,又契合日本元素在美國民眾特別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家庭中備受歡迎的社會現實。
小說標題采用的是帶有藝術特色的半手寫體,與之相呼應的是頗有質感的竹質框架背景,仿佛由一位極具涵養的藝術家手握工藝筆于山間竹屋精心創作而成。正文部分也采用類似背景,文字均置于竹質框架之中。每一章的標題以紫藤花環繞,呼應小說主人公的姓名。新章節首頁左下角的竹質框架內是一幅日式閣樓隱現于山林之間的日本風景圖,閣樓上的和式雕花和懸掛的燈籠營造了濃濃的日本氛圍,不斷引導讀者對作品日本性的認同。
《紫藤之戀》對讀者群體的識別、定位和引導體現了作者伊頓的商業意識,反映了20世紀初美國文學在消費資本主義潮流中的生存狀態。小說文本,尤其是流行小說文本,開始以成為流通商品為目標。作為作者和利益相關方的經營手段,文學創作過程中的取舍無可指摘,但作為一定歷史條件催生的產物,文學不僅在內容上,更在形式上具有特殊的意義。伊格爾頓認為“形式通常至少是三種因素的復雜統一體”——“相對獨立的文學形式的歷史”“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結構的結晶”以及“作家和讀者之間的特殊關系”⑩。《紫藤之戀》采用復古腔調的羅曼司形式承載社會矛盾,通過浪漫主義文學的“間離”手段發揮歷史和政治因素的作用,因此只有進入該文本的歷史邏輯“潛文本”才能把握伊頓的真實之言,“作品一旦與作家的歷史條件分裂,必然會顯得意圖不明,神秘莫測”{11}。
二、多重矛盾的文本包裝
奪取并維持經濟力量是人類一切社會活動的根源,也是人類社會關系形成的條件。經濟力量在社會結構中的不均衡分布是階級形成和階級運動的根本原因。意識形態是階級認同和對話的基石。伊格爾頓認為,“要理解一種意識形態,必須分析那個社會中不同階級之間的確切關系,而要做到這一點,又必須了解那些階級在生產方式中所處的地位。”{12}
在《紫藤之戀》開篇,幼小的紫藤姑娘被置于錯綜復雜的群族矛盾中,紫藤的父親命令她瞪大眼睛記住殺母仇人毛利家族首領的樣貌,繼而是父親與其分離在鄉野之地過著隱士般的生活。小說將顯性矛盾置于未受現代資本侵襲的日本環境,以封建貴族經濟利益集團內部的恩怨作為伏筆,增加后文對紫藤乃至景琦的身份揭露對讀者的沖擊力。《紫藤之戀》真正吸引讀者的不是純潔的封建日本環境,也不是強勢的美國艦隊與浪人團伙的軍事沖突,而是一系列矛盾的生成和問題的解決。
小說的基本矛盾之一是封建貴族與賤民階層的隔閡,這是貫穿紫藤父親島津武士命運的核心要素,也是島津以女兒為犧牲操控毛利家族乃至帝國命運的出發點。后文紫藤姑娘賤民身份和女扮男裝事實的揭露迫使讀者閱讀產生人物系統的前后運動,在小于人物所知(相對于島津武士)——等于人物(相對于紫藤)——大于人物所知(相對于景琦)的三種狀態中持續探索。景琦以封建貴族的身份出現在敘事中,但他對紫藤成功追求及“羅密歐與朱麗葉”般的愛情悲喜劇反映的卻是貴族階層對新時代經濟關系的重新認識。景琦不止一次地表達“時代不同了”,只是內涵因針對封建制度或外來文明略有不同。景琦能與紫藤走到一起,關鍵在于他們對國內涌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統一認識,然而他也因擔心外來文明的“疾病、無禮要求、心胸偏狹和吹毛求疵”而對其警惕有加。景琦的階級局限性使他無法不考慮所在階級的經濟生存空間。
西方帝國主義勢力與傳統的日本封建體制的矛盾卻是解決前一矛盾的良方。景琦對時局的把握能力使其能夠認識社會的主要矛盾所在,現代力量入侵引起的社會恐慌掩蓋了國內矛盾的沖突,貴族階層找到了破解階級對立困境的良策,即維護封建體系的最高權威,吸收外來文明以抵御外邦。
小說對多重矛盾進行包裝和拆解,用男女主人公身份的隱匿和揭露推動矛盾的解決。矛盾的解決可能是臨時的,如景琦對外來文明態度的變化引起的帝國命運的轉變,再如紫藤的喬裝行為隨時可能被識破,但這些臨時的解決不僅沒有損害人物“表象”,即人物習性和能力,亦即人物所在階級與新時代經濟結構的聯系,反而是對表象的確證。可以說,《紫藤之戀》就是通過身份的“流動”來實現敘事邏輯的。
紫藤賤民身份和男裝身份的掩藏和揭露是故事的戲劇性所在,對男裝身份的暗示與景琦忙于政事卻偶感情愫的對比為整個敘事增添了喜劇色彩。這一喜劇色彩其實是敘事隱藏的政治歷史現實所在,“原本平庸的、經驗的事實被轉變成了解釋敘事所依賴的一些基本范疇”{13}。在傳統認識中,女性能力低于男性,女性的智慧和脾性不足以參與政事。但男裝紫藤多次挺身挽救危局,令包括景琦在內的男性社會汗顏。讀者的歷史預設成為作者的敘事框架和動力,使敘事“合理”開展。因此,在敘事中紫藤男裝雖相較于政治斗爭、外來入侵等矛盾處于邊緣化的地位,但與其說讀者在期待其身份揭露及與景琦相認,不如說讀者更愿意看到男主人公被表象迷惑窘態倍出,男權社會的成見被挑戰,社會即將轉型,這才是讀者的真實樂趣和期待所在。
紫藤男裝身份的揭露雖是羅曼司不可避免的修辭方式,但其體現的卻是傳統價值觀與新興資本主義矛盾的調和。革命之后開明貴族獲得合法地位,日本與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通商和文化交流;日本國家長久認同的傳統得以保留,男女愛情和家族親情沒有因時局動蕩而彌散,封建皇權也在新時期被賦予新的內涵,如敘事中不斷出現的紫藤、鳶尾花和出版物裝幀體現的日本審美元素一樣,傳統價值通過符號彰顯存在并獲得永恒。
小說不是政治歷史事件的簡單記錄,小說敘事在作者的控制下以更加隱晦和精妙的方式呈現社會矛盾,以“實驗性的運作”對“各社會階級的策略進行檢驗”{14}。《紫藤之戀》的特殊之處是它對美國現實文化的表面疏離,使美國讀者忽視其文本生產的真實語境。20世紀初美國國內因財富聚集社會階層分化嚴重,國民對國家道德狀態乃至未來普遍懷疑。《紫藤之戀》利用“多情態”的敘事形式將現實的美國階級矛盾轉移至50年代日本社會多重矛盾的文本呈現并加以象征性解決。
三、社會矛盾的象征性解決
詹姆遜認為“象征性行為開始于生成和生產其自身的語境,在出現的同一時刻又從其退卻出來,以對自身變化的眼光來審視自身。”{15}文學不僅是對社會現實的象征性表征,更以現實為鏡審查此表征的動態效度,文學生產體系本身便具有“否定之否定”的發展動能。換句話說,文學生產是作品的呈現,更是文學本體前在邏輯的塑形。這一前在邏輯以歷史或意識形態潛文本為載體,推動文學對自身的持續闡釋。文學文本是對先驗性潛文本的改寫或重構。“潛文本既不在場呈現,不是常識范疇的外部事實,甚至也不是歷史記載的傳統敘事,而是對事實的不斷構建或重構。”{16}潛文本以不在場的流動特質支配著文本生產的全過程,使原本紛雜的外部事實圍繞作者產生意義,因此,無論從形式還是內容上看,文學都是多重社會因素的載體,為“政治無意識”提供聲音。“文學文本在思想觀念上被賦予了某種反對甚至消解文化壓抑的力量,它提供了一種交流模式,使參與和體驗有意義的無意識經驗成為可能。”{17}
《紫藤之戀》小說的情境塑造和人物刻畫滿足了美國人的遁世愿望,美好的傳統得以保留,愛默生式美國性得以彰顯,美國人膨脹的力比多被控制到最溫和的程度,而日本傳統家庭的塑造將沒有令人作嘔的消費表演、沒有商品化的個人主體、沒有爾虞我詐的利益交往的美好過往以純凈的烏托邦形式向美國讀者呈現。小說中天皇的權威是各方勢力斗爭的焦點,這種看似封建體系內部的實力較量投射到文本之外時便是對終極信仰的渴求。《紫藤之戀》并不是簡單的日本羅曼司小說,而是圍繞歷史、社會和意識形態矛盾運轉的現實主義文本。經過包裝的歷史以“全然不同的生活模式質疑著現實主體的生活模式,給現實主體講述著他們‘所具有的、實質上和未實現的人的潛力,迫使現實主體對生命意義和生活世界重新思考,并激發著它對未來世界強烈的烏托邦沖動”,這股沖動“不斷塑造并改變現實主體,真正發揮過去歷史的現實作用。”{18}
伊頓的日本羅曼司作品幾乎每一部都包含或濃或淡的歷史色彩,尤其展現日本現代化進程中西方文明對于封建傳統的壓倒性力量,處于弱勢的“對立文化或意識形態往往采取隱蔽和偽裝的策略尋求對抗或破壞處于支配地位的價值體系”{19}。《紫藤之戀》的愛情故事并不能掩飾人物的矛盾性:具有獨立、堅韌、聰慧等美國精神的紫藤姑娘如何在囿于傳統的日本社會立足乃至有所作為?驍勇善戰、足智多謀的貴族景琦何以屢屢陷入他人的陰謀圈套(紫藤父親的欺騙,浪人集團的失信,貴族集團的背叛等)而失去對時局乃至自己命運的把握?“有情人終成眷屬”的浪漫結局是對歷史的虛化和掩蓋。景琦和紫藤攜手挽救國家于危局,并以開明上層階級的身份主導日本開埠通商。然而真實歷史是經歷長期鎖國的日本貴族集團對西方資本主義抱有極其強烈的排斥心理,統治階層擔心通商引起社會變革和利益流出,“融入現代文明”不過是維護日本性的手段,景琦呼吁的“平等權力”也只是封建體制岌岌可危之際對生產關系變革的被迫適應,同樣是亂世中確保經濟利益的努力之舉。
“詹姆遜把文學中的性壓抑表現看作一種受壓抑的經濟利益的掩蓋物”{20},《紫藤之戀》中兩處明顯的欲望壓制同樣體現了經濟利益的沖突,一是開篇貴族公子們(包括景琦)對紫藤姑娘的群體追求,二是景琦對男裝紫藤“次郎”的同性愛戀。
紫藤姑娘擁有清新、年輕的容貌,舉止優雅,散發著令人著魔的魅力,貴族公子們趨之若鶩,歷經辛苦的景琦成功追求紫藤并如羅密歐與朱麗葉般交往,但景琦敵對家族身份的曝光、紫藤賤民身份被利用并被父親勒令出家,令這段感情戛然而止。被設計陷害而滿心悲憤的景琦用嘶啞、可怖的聲音向紫藤大喊“神會原諒你。我,絕不會。”{21}而紫藤“在寺院門檻處猶豫”后,“靜靜地走進這隱沒于群山中的寂靜之所”{22}。小說在現實邏輯上將這對戀人充分隔離。表面上,這是因紫藤母親死亡導致的兩大家族矛盾的結果,實則是封建經濟模式愈加成為社會發展的阻礙,貴族勢力在動蕩的社會中謀取經濟利益和鞏固地位爭斗的結果。島津武士不惜犧牲女兒令毛利家族喪失貴族地位,經濟矛盾落實在景琦個人命運上即是對其性欲望的暴力壓制。
在與男裝紫藤“次郎”長期相處且多次一同出生入死后,景琦感到沒有次郎相伴便有“孤獨”之感,他對次郎的感情“有如偉大的靈魂需求呼應”,心中充滿渴望。雖然這份感情可能只是“同性的社會認同”(homosocial),而非“同性的身體欲望”(homoerotic){15},但無法排除景琦同性心理認同向愛戀轉化的可能,畢竟次郎身上體現的是愛人紫藤的全部氣質。紫藤適時的身份揭露使景琦回歸現實,終止了景琦的同性幻想,并將其轉化為傳統的異性愛戀。如此安排考慮了日本和美國的傳統性別觀念,流行小說作家伊頓絕無意在政治取向上冒險,因為小說的經濟利益鏈上不只是伊頓一人。考慮到作者特殊的種族身份和社會語境,紫藤“自揭身份”而不是“被人揭穿”又有另一層涵義。伊頓有一半的中國血統,而美國對少數族裔尤其華裔拒斥、排擠,但日本族裔因在美人數較少尚能得到白人群體的接受。伊頓選擇“冒充”,通過綜合商業手段在文本內外建立了日本族裔形象。這樣的冒充隨著伊頓名聲提高而難以為繼,因此伊頓在她日本羅曼司作品中對冒充的堅持其實是對美國種族主義偏見的挑戰,尋求主流社會對混血族乃至華裔群體特殊的身份認同。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下,這一努力自然與主流意識形態格格不入且注定失敗,但是作為提倡族裔“平等”權利的先驅,盡管形式隱蔽,伊頓這一既失敗又成功的努力卻是包括《紫藤之戀》在內伊頓小說的重要潛文本,體現作者“客觀的黨性”{24}。
因此,《紫藤之戀》等日本羅曼司小說滲透著作者作為社會個體遵行的意識形態力量,文本的政治無意識“在以象征的形式提出社會變化……的問題,并反問自己如何能想象回歸舊秩序必需的那種力量在這樣做的同時不那么強大和具有破壞性,不致在這個過程中毀了那種秩序本身。”{25}羅曼司小說的形式是伊頓權衡利弊后的謹慎選擇,在謀求商業利益和表達政治訴求之間找到了平衡。
四、結語
《紫藤之戀》并不是一次簡單的浪漫主義復歸,而是20世紀初美國華裔混血女性在消費現實主義語境中的一次特別發聲。作者伊頓以符合消費社會邏輯的形式,將其對美國女性主義、種族主義、東方主義等思想的觀察和體悟以文學的形式展現出來。小說從敘事元素、敘事方法到最終呈現無不體現對消費群體的精準定位。商業特征掩蓋下的歷史矛盾較之愛恨情仇更具意義。馬克思主義闡釋學堅持歷史和意識形態之于文學的前在邏輯,強調政治無意識對文學敘事和闡釋的構建作用,在考察形式和內容矛盾成因的基礎上,把握文本的歷史語境,文學成為社會群體命運的象征性表達。在此理論觀照下,《紫藤之戀》呈現了不同于一般浪漫愛情故事的歷史格局,將美國欲望的“符號化”通過“異己”地理和文化空間的人物典型展現出來,應和并邀請讀者解讀,因此也為美國華裔和混血族裔文學的歷史特征和地位賦予了新的論證邏輯。
① 溫妮弗蕾德·伊頓的寫作生涯各階段署名各有不同,從前期雜志刊文署名“Winnie Eaton”,到日本題材小說署名“Onoto Watanna”,再到后期自傳體小說的匿名和混血族敘事小說“Winifred(Eaton)(Reeve)”,反映作者的人生經歷和思想變化。“Onoto Watanna”也不是符合日語的組合規則,中文翻譯尚不統一,目前有“夫野渡名”、“小野登”、“小野の小町”等。
② Howells, W. D: “A Psychological Counter-Current in Recent Fiction”. North American Review. 1901,(173), p.881.
③ Mcgovern, Charles F: Sold American: Consumption and Citizenship, 1890-1945.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9, p.3.
④⑥ 潘志明:《作為策略的羅曼司——溫妮弗蕾德.伊頓小說研究》,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第x頁;第290頁。
⑤ 埃利奧特·埃默里:《哥倫比亞美國文學史》,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4年版,第383頁。
⑦ Duus, P: The Japanese Discovery of America. Boston, New York: Bedford Books, 1997, p.12.
⑧ Goodwin, B: Social Science and Utopia: Nineteenth-Century Models of Social Harmony. Sussex: Harvester Press, 1978, p.7.
⑨ Genette, G. & Lewin J. E: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2.
⑩{11}{12} [英]伊格爾頓:《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文寶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33頁;第74頁;第10頁。
{13}{14}{15}{25} [美]詹姆遜:《政治無意識》,王逢振、陳永國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49頁;第150頁;第70頁;第158頁。
{16}{19} Jameson, F: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p.81, p.84.
{17}{20} 施瓦布:《政治無意識的主體:對詹姆遜的反思》,《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2001年第00期,第36頁;第40頁。
{18} 楊生平:《馬克思主義不只是一種“闡釋學”——評詹明信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馬克思主義研究》2014年第11期,第89頁。
{21}{22} Watanna, O: The Wooing of Wistaria. New York, London: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02, p.185, p.19.
{23} Huh, J: “Detecting Winnifred Eaton”, MELUS, 2014,(39), p.90.
{24} 根據伊格爾頓的解釋,作家不必把自己的政治觀點硬塞到作品中,因為只要他揭示出在某個環境中現實的和發展的力量客觀地在起作用,那么在這個意義上講,他已經具備了黨性。
(責任編輯:黃潔玲)
From Commercial Narrative to Ethnic Voices: 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of The Wooing of Wistaria by Winnifred Eaton
Chen Liangui
Abstract: The Wooing of Wistaria by Winnifred Eaton, a popular novel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has an accurate positioning as written in the genre of romance, with its narrative elements and final presentation. As the work of a Chinese American of mixed blood, it reflects the authors observation 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ethnic minority women find themselves and the trends of consumerism. Marxist hermeneutics insist on the contexualisation of texts, excavating the potential driving force of the movement for form and contents and trying to get a hold on the suppressed and buried historical desire through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ness of the text. For this reason, The Wooing of Wistaria has acquired a combined microscopic and macroscopic reading significance, presenting a historical pattern as an ‘Other that is different from ordinary romantic love stories and providing the ethnic minority voices in America with new forms.
Keywords: Winnifred Eaton, The Wooing of Wistaria, commercial narrative, ethnic, political unconscious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