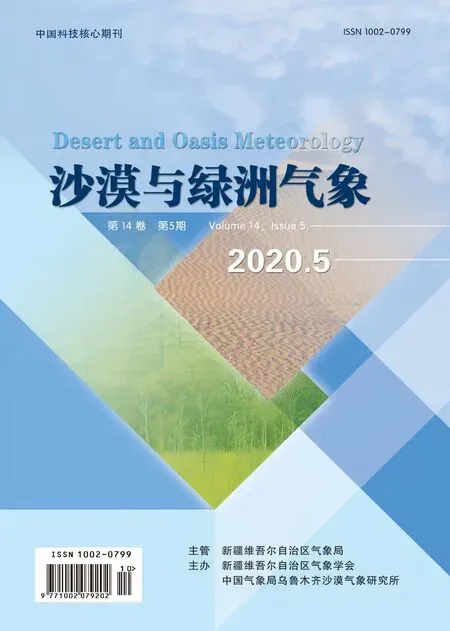沿天山地區一次暴雨動力過程和云中水凝物粒子特征的數值模擬研究
李 偉 ,張俊蘭 ,曾 勇
(1.新疆氣象臺,新疆 烏魯木齊830002;2.中國氣象局烏魯木齊沙漠氣象研究所,新疆 烏魯木齊830002;3.中亞大氣科學研究中心,新疆 烏魯木齊830002)
暴雨在地形附近產生時,具有與平原地區不同的動力過程和云中水凝物粒子特征,表現出具有明顯地形依賴性的成云致雨過程。地形分布特征往往決定著暴雨的落區和強度,發生在地形附近的暴雨可產生極端的局部降雨和洪水[1]。國外對地形暴雨的動力過程和云中水凝物粒子特征已開展了較為深入的研究。Caracenaet等[2]研究發現墨西哥灣豐沛的暖濕氣流遇到落基山脈后,迎風坡氣流出現明顯的輻合上升,同時,云中水凝物粒子快速聚集增長,準靜止的深對流可能產生突發性大暴雨。Nuissieret等[3]和Ducrocqet等[4]指出在阿爾卑斯山脈和法國中央山脈附近沿山暴雨過程中,暴雨的動力過程和云中水凝物粒子的分布和演變向著有利于增強暴雨的方向發生了變化,導致在有利的成云致雨條件下山脈附近地區出現數百毫米的強降雨過程。氣象學者們進一步研究指出,在地形暴雨過程中,氣流遇到山脈后的發展趨勢受垂直山脈方向上的水平氣流強度(特別是低空急流強度)、氣流的熱力學穩定度和山脈的高度共同影響[5-6];降水粒子落地時的分布位置則受地形的高度、地形的陡峭程度和微物理過程的時間尺度制約[7-8]。國內針對地形暴雨的動力過程和云中水凝物粒子特征也進行了許多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例如,盛春巖等[9]利用ARPS模式對北京山區附近的一次大暴雨進行數值試驗,表明大暴雨是在多尺度地形及一定的天氣系統配置下產生的,暴雨的動力過程很大程度上受地形影響,且在沿山地區上空云中水凝物粒子出現大值中心。段靜鑫等[10]利用WRF-Chem模式模擬了四川盆地暴雨過程后指出,盆地北部山區附近大氣強烈對流運動及其攜帶盆地內大量水汽有利于云系的垂直發展,云中水凝物粒子質量濃度明顯增大,使降水強度增強至大暴雨量級。董春卿等[11]利用WRF模式對山西南部垣曲縣喇叭口地形進行地形敏感性試驗后指出,地形的變化對積層混合云系的動力結構和水相物質的微物理結構變化有顯著的影響。可見,國內外氣象學者已經開展了許多有關地形暴雨的動力過程和云中水凝物粒子特征研究,得到了諸多有益結論,為地形暴雨的發生發展機理研究和預報預警業務提供了科學支撐。然而,相較于國外和我國中東部地區,目前對于新疆地區的地形暴雨,尚有一些認識上的不足。
新疆位于亞洲中部,遠離海洋,屬于典型的干旱、半干旱氣候區[12-13]。天山位于新疆中部,其巨大的體積深刻影響著新疆的天氣氣候。以往的諸多研究已表明沿天山地區暴雨過程中氣流的強度和三維空間分布結構對暴雨的產生有重要影響[14-19]。沿天山地區暴雨系統的動力和熱力結構演變及水汽分布特征與平原地區存在差異,從而造成沿天山地區暴雨的分布和強度演變具有不同于平原地區的特征[20-22]。許多氣象學者也針對天山地形暴雨的觸發、水汽的聚集、暴雨系統的增強等過程開展了研究,得到了一些有價值的結論[23-26]。以上這些研究成果一定程度上增強了人們對新疆地形暴雨的認識,對新疆地形暴雨的預報具有較好的指導意義。然而,以上有關新疆地形暴雨的研究大多利用再分析資料開展,資料時空分辨率有限。更重要的是,以往研究較少關注新疆地形暴雨過程中云中水凝物粒子的特征,而云中水凝物粒子的形成和增長與降水的關系最為密切[27]。加之新疆地域廣闊,各地區的地形暴雨存在一定差異,有必要對更多地形暴雨進行深入研究。高分辨率數值模式可為研究地形暴雨提供高時空分辨率的資料,其物理量計算過程可生成云中水凝物粒子,為研究天山地形暴雨的動力過程和云中水凝物粒子結構特征提供了可能和便利。基于此,本文選取2018年5月23—24日北疆沿天山地區一次典型地形暴雨天氣過程,在分析了地形暴雨產生的有利背景后,利用高分辨率數值模式WRF對此次地形暴雨的動力過程和云中水凝物粒子結構進行分析,以期為此類暴雨預報提供有益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本文所使用的資料為美國國家環境預測中心和大氣研究中心(NCEP/NCAR)再分析資料(時間分辨率6 h,空間分辨率1°×1°)、國家衛星氣象中心風云衛星遙感數據服務網提供的FY-2G逐小時TBB數據、新疆國家氣象站及區域加密自動氣象站降水資料和WRF3.8.1模式模擬輸出資料,在利用觀測資料和再分析資料對暴雨過程進行天氣學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應用高時空分辨率的數值模式WRF3.8.1模擬輸出資料,揭示天山地形在暴雨過程中的作用。
2 暴雨過程的觀測分析
2.1 天氣實況
新疆幅員遼闊,但僅分布著105個國家氣象站。近些年來,隨著新疆經濟和氣象事業的不斷發展,較為密集的區域加密自動氣象站得以建設和應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氣象站點稀疏的問題。目前,北疆沿天山地區氣象站網較為密集,但沿天山山脈較高海拔地區站點依舊稀疏(圖1a)。2018年5月23日12時—24日12時(世界時,下同)北疆沿天山地區出現了一次暴雨天氣過程,距離天山地形約50 km以內(44.5°N以南)地區的12個站點出現暴雨,然而距離天山地形約50 km以外(44.5°N以北)地區的站點僅出現了中雨以下量級的降雨(圖1b)。可見,此次降雨受天山地形的影響較明顯,屬于典型的地形降雨天氣過程。需要說明的是,北疆沿天山地區地理位置較為寬廣,東西跨度較大,本研究重點關注的是85.5°~86.5°E的北疆沿天山地區。進一步分析可知,此次沿天山暴雨過程最強降雨時段為23日18時—24日00時,6 h總降雨量分布與日降雨量分布類似,同樣體現出地形降雨的特征(圖1c)。從北疆沿天山地區的烏蘭烏蘇、石河子、石河子143團卡子灣攔洪壩、石河子北陽山機場和沙灣縣博爾通古鄉1號5個代表站的逐小時降雨量演變可知,最強降雨時段為23日18時—24日00時,且降雨表現出積層混合云降雨特征(圖1d),在較為平緩的降雨過程中出現短時強降水(烏蘭烏蘇站23日22—23時降雨量達10.4 mm)。
2.2 環流形勢
2018年5月22日500 hPa歐亞中高緯度呈現“高—低—高”的“兩脊一槽”環流形勢,歐洲地區高壓脊東移至烏拉爾山一帶與里咸海高壓脊同位相疊加,同時,新疆及其以北地區為高壓脊控制區,兩高之間的西西伯利亞地區為一低槽,且在中亞地區南部存在一短波槽。5月23日06時前后西西伯利亞低槽攜帶北方冷空氣進一步東移南下,與中亞南部短波槽在巴爾喀什湖地區匯合形成中亞低槽,新疆西部受槽前強勁的西南急流控制。隨著低槽進一步東移,北疆沿天山地區于23日18時開始受中亞低槽影響(圖2a)。此時,700 hPa上巴爾喀什湖和新疆之間存在至少4個短波活動,北疆地區的短波已進入新疆西部,同時該短波有較明顯的西北急流配合(圖2b),偏西地區已經出現降雨;850 hPa與700 hPa上類似,但系統位置更偏東,西北急流已經抵達北疆沿天山地區附近,北疆沿天山地區開始出現降雨。隨著中亞低槽進一步東移,23日18時—24日00時,700 hPa和850 hPa上低空西北或偏西急流加強并完全控制北疆沿天山地區,降雨強度明顯增強。隨著系統快速東移,5月24日00時后北疆沿天山一帶的雨強明顯減弱至停歇。

圖1 天山地形(灰階)和北疆沿天山地區氣象站點分布(a)、5月23日12時—24日12時總降雨量分布(b)、23日18時—24日00時降雨量分布(c)和23日15時—24日03時北疆沿天山地區代表站逐小時降雨量(d)(單位:mm)

圖2 5月23日18時500 hPa環流形勢(a)和700 hPa環流形勢(b)(紅色箭頭表示急流)
2.3 水汽輸送特征
暴雨的產生離不開豐沛的水汽輸送至暴雨區上空并產生輻合,烏拉爾山最高海拔為1895 m,700 hPa從西北部東南下的水汽輸送帶可翻越烏拉爾山進入新疆北部。由此次暴雨整層水汽通量和700 hPa水汽通量散度可見,5月22日12時巴倫支海水汽向東南方向經西西伯利亞平原輸送至巴爾喀什湖北部地區后轉向偏東方向輸送至中西伯利亞地區,此時水汽通道還未進入新疆地區,新疆為水汽弱輻合區(圖3a)。隨著天氣系統的東移南壓,水汽通道進行了相應調整;23日18時水汽通道在西西伯利亞中部地區轉向偏南方向輸送至巴爾喀什湖東部后再次轉向偏東方向輸送至北疆沿天山地區,該處水汽通量達 25 g·hPa-1·cm-1·s-1, 水汽輻合大值區也加強為-2×10-7g·hPa-1·cm-2·s-1左右(圖 3b),為北疆沿天山地區暴雨的產生提供了較好的水汽條件,該處降雨開始出現。同時,南疆盆地內也存在一條水汽輸送通道,但由于天山山脈的阻隔,對北疆沿天山地區暴雨影響不大。隨著水汽通道向東移出北疆沿天山地區,暴雨的較強降雨時段結束。當然,隨著系統進一步東移,在北疆東天山海拔相對較低地區,南疆地區水汽通道和北疆水汽通道將共同為降水提供水汽,但已不是本文重點研究的地區和時段。就此次北疆沿天山地區暴雨的水汽來源和輸送而言,巴倫支海是暴雨水汽的來源,水汽經過西西伯利亞平原長距離輸送至暴雨區并產生輻合;在輸送過程中發生了多次轉向,而這些轉向很大程度上受天氣系統調整的影響和制約。
2.4 暴雨云系特征
新疆地形復雜,衛星遙感資料對于暴雨系統的“捕捉”具有較強的優勢。以往新疆暴雨的衛星觀測研究表明,快速發展移動的暴雨云團或云系可造成較短時間內某處出現較強降水,云團或云系主要表現為孤立對流云團和積層混合云[14-16,25-26]。此次暴雨過程FY-2G衛星TBB資料顯示,造成北疆沿天山地區暴雨的是積層混合云。5月23日18時,積層混合云覆蓋了新疆偏西地區,云系前沿位于北疆沿天山地區;隨著云系的東移,23日20時,云系逐漸移至沿天山地區,云系強度基本保持不變;23日22時,云系主體已控制了北疆沿天山地區,TBB值達-44℃以下的云體覆蓋了暴雨區;24日00時,積層混合云強度已有所減弱,且主體已經移過北疆沿天山地區,該地區僅可見云系后邊緣較為零散的弱云團,此時暴雨的強降雨時段已經結束,僅有零散的弱降雨出現。

圖3 2018年 5月 22日 12時(a)和 23日 18時(b)整層水汽通量(箭頭,單位:g·hPa-1·cm-1·s-1,紅色長箭頭表示水汽輸送路徑)和 700 hPa水汽通量散度(陰影,單位: ×10-7g·hPa-1·cm-2·s-1)
3 數值模擬及驗證
3.1 數值模式方案
本文模擬采用的數值模式為WRF3.8.1,模式的初始場和邊界條件由NCEP/NCAR逐6 h的1°×1°再分析資料提供,模擬中心點設置在(44°N,86°E),采用三層雙向嵌套,三層區域的水平分辨率分別為27 km、9 km和3 km,相對應的水平方向格點數分別為 300×240、514×373 和 661×451,垂直層數取 50層,積分步長為60 s。微物理過程采用Thompson方案,積云參數化采用Kain-Fritsch方案(3 km層次關閉積云參數化方案),邊界層采用YSU方案,長波輻射采用RRTM方案,短波輻射為Dudhia方案,積分時間從8月23日06時—8月24日18時,共積分36 h。本文模擬分析所用資料均為水平分辨率3 km的模擬資料。
3.2 模擬結果驗證
由模擬的日降雨量分布(圖4a)與實況日降雨量分布(圖1b)對比可知,模擬結果基本反映出降雨量的實際分布情況,較好地再現出44.5°N以北地區為中雨以下量級降雨、沿天山地區為大到暴雨的分布特征。但也可以看到模擬降雨和實況存在一定的差異,特別是天山地區,模擬出了實況上不存在的較強降雨,而差異存在的最大原因是天山地區氣象站點稀缺(圖1a),沒有觀測資料;此外,模式自身精度限制、模式地形與實際地形的差異以及地形降雨的復雜性等原因也是導致模擬結果與實況存在一定差異的重要原因。進一步從降雨最強時段的模擬降雨分布(圖4b)與實況(圖1c)對比可見,雨帶分布和沿天山地區強降雨特征均得到了再現,模擬結果與實況較為接近。但也存在不足,模擬的強降雨中心強度較實況偏弱。總體來看,模擬結果已經可以反映出此次地形暴雨的雨帶分布特征,特別是模擬出了沿天山地區的較強降雨,可以利用模擬輸出資料對此次暴雨進一步分析。
4 地形暴雨產生的機制
4.1 地形對暴雨動力過程的影響
低空急流與地形的配合對暴雨的產生和增強具有顯著的觸發和增強作用[13-14]。從此次地形暴雨強降雨時刻的700 hPa低空急流和天山地形的配合可見,強降雨時低空急流發展強盛,急流核強度達30 m·s-1,北疆沿天山地區位于急流核前端,風速的輻合疊加地形的阻擋作用造成在3000 m地形處出現明顯的上升運動,最強上升速度達1.8 m·s-1(圖5a)。同時,低空急流造成的大氣不穩定性使沿天山地區出現明顯的正渦度和輻合(圖5b),為較強降水的產生提供有利的動力條件。從雷達組合反射率分布可見,積層混合云回波特征明顯,較強回波位于沿天山地區,在35 dBZ以上,而距離天山相對較遠的45°N附近地區,回波較弱,與衛星觀測到的云系特征一致,進一步說明了模擬的可靠性,且沿天山一帶較強回波與強降雨帶有較好的對應關系。由沿圖5b中黑色實線所做的組合反射率和風矢量剖面可見,氣流在天山迎風坡附近受地形阻擋抬升作用后向上發展,且迎風坡為較強回波區,說明迎風坡降雨強度較強。綜上,低空急流在天山地形的有力配合下,為此次沿天山地區強降雨的出現提供了有利的動力條件。

圖4 2018年5月23日12時—24日12時模擬的總降雨量分布(a)和23日18時—24日00時模擬的降雨量分布(b)

圖5 2018年5月23日21時3000 m天山地形(灰色陰影)、模擬的700 hPa風場(風羽,單位:m·s-1)、急流(彩色陰影,單位:m·s-1)和垂直速度(黑色實線,單位:10-1m·s-1)(a)、模擬的 700 hPa沿天山一帶渦度(彩色陰影,單位:10-5·s-1)和散度(黑色虛線,單位:10-5·s-1)(b)
4.2 地形對暴雨過程云中水凝物粒子特征的影響
Fan等[27]指出較強的上升速度與較多的水汽可以提高云系周圍環境過飽和程度,進而影響云中水凝物粒子。圖6為沿圖4b黑實線所做的云中水凝物粒子、溫度、垂直速度和風矢量剖面。強降水發生時,冰晶粒子主要分布在400 hPa以上高空,溫度低于-30℃區域,沿天山地區為冰晶粒子大值區,中心強度達0.011 g·kg-1,其下氣流遇天山地形后產生向上運動,對應了較明顯垂直速度(圖6a)。雪粒子分布較冰晶分布明顯更廣,主體位于400~800 hPa(對應溫度-30~0℃),雪粒子的強度也明顯強于冰晶,沿天山地區1.2 g·kg-1的雪粒子大值中心位于600~800 hPa,對應了較強的迎風坡輻合和上升運動。同時可見,在天山較高海拔直接與雪粒子接觸的地形處,高海拔地區地面可直接降雪(圖6b)。霰粒子主體分布在700 hPa以下的沿天山地區,與雪粒子大值中心相交,中心強度達0.16 g·kg-1(圖6c)。云水分布與霰粒子相似,沿天山地區為霰粒子大值區,中心強度達 0.24 g·kg-1。 同時,700 ~800 hPa分布為過冷云水,有利于向液態云水轉化,從而增強暴雨(圖6d)。雨水主要分布在800 hPa以下低空,沿天山地區大值中心達0.2 g·kg-1,與霰粒子、云水相接。可見,在沿天山地區有利動力作用下,水凝物粒子聚集、增長,固相粒子與液相粒子在垂直分布上相交,有利于固—液粒子轉化;霰粒子與過冷云水的存在,對于降雨強度的增強具有重要的作用。

圖6 2018年5月23日21時模擬的沿圖5b中黑色實線所做的云中水凝物粒子(彩色陰影,單位:g·kg-1)、風矢量(為分析方便,垂直速度 w×10)、溫度(紅色實線,單位:℃)、垂直速度(綠色虛線,單位:10-1m·s-1)和天山地形(灰色陰影)垂直剖面
5 結論與討論
2018年5月23 日12時—24日12時北疆沿天山地區出現了一次典型的地形暴雨天氣過程。本文重點分析了暴雨過程最強降雨時段23日18時—24日00時,得到結論如下:
(1)從暴雨區代表站的小時降雨演變和衛星TBB特征可判斷此次暴雨過程為積層混合云降雨過程;東移加深的中亞低槽是此次暴雨的影響系統;北疆沿天山地區暴雨的水汽來源為巴倫支海,水汽經過西西伯利亞平原多次轉向輸送至暴雨區;快速移動的積層混合云是形成暴雨的主要云系。
(2)利用高時空分辨率數值模式WRF對此次暴雨過程進行模擬,在模擬結果能較好地反映此次降雨性質、分布和大值中心的基礎上,利用模式輸出資料對此次地形暴雨過程進一步分析。模擬結果表明暴雨過程強勁的低空急流在沿天山地區形成了顯著的輻合區,在天山地形的抬升作用下,沿天山地區出現較明顯的上升運動,為此次強降雨提供了有利的動力條件。
(3)北疆沿天山地區上空的水凝物粒子(冰晶、雪、霰、云水、雨水)在有利動力輻合抬升作用配合下,不斷聚集、增長,在沿天山地區形成大值中心。固相粒子與液相粒子在垂直分布上相交,為固—液粒子轉化提供了良好的條件,而其中霰粒子和過冷云水對增強降雨強度具有重要的作用。
本文對一次地形暴雨過程在觀測分析的基礎上,重點利用數值模式對地形暴雨的動力過程和云中水凝物粒子分布進行了研究,揭示了天山地形對暴雨動力過程和云中水凝物粒子的影響。但本文僅僅是對一次過程得到的結論,未來還需要通過更多的個例研究進行驗證,為預報提供可靠參考。暴雨動力過程和云中水凝物粒子的影響。但本文僅僅是對一次過程得到的結論,未來還需要通過更多的個例研究進行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