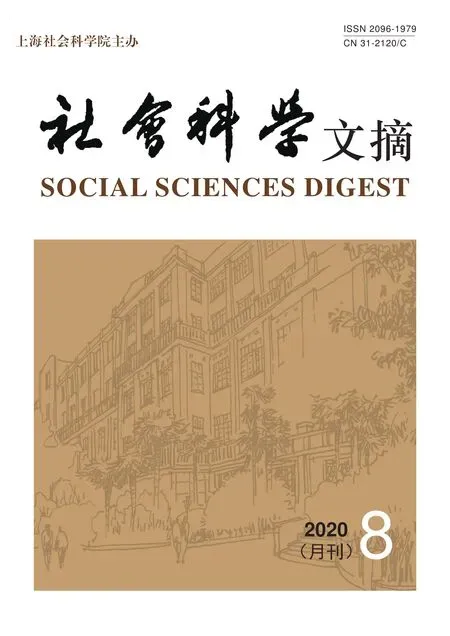浪漫精神的興衰:家庭、階級與文化幻象
文/南帆
一
1907年,魯迅在《摩羅詩力說》推薦和介紹了一批風格近似的歐洲詩人。“摩羅”為梵文的音譯,意指佛教傳說之中專事破壞的魔鬼。魯迅力圖轉借這個概念召喚摧枯拉朽的浪漫主義幽靈。
魯迅構思的“摩羅詩力”很大程度地指向了中國古典文化的傳統氣質:節制,內斂,保守,謹慎。許多時候,這些氣質是儒家文化人格理想的投射。儒家子弟必須以堅忍的姿態抵近目標,譬如“克己復禮”。“己”是一個蒙受貶義的概念,偉岸而醒目的自我并非儒家文化的贊許對象。儒家子弟遵奉不偏不倚的中庸哲學,最為標準的詩歌風格被定義為“溫柔敦厚”。魯迅心目中,儒家文化的傳統緊箍咒構成了人格的全面抑制。
中國古代文化存在另一個源遠流長的主題:超然與隱逸,猶如以出世的精神安慰士大夫之中的失意者。這些思想派別內涵各異,它們的共同特征是逾越儒家文化覆蓋的范圍,敞開另一種生活與另一種價值理念。這是一種冷寂的叛逆。冷寂的叛逆只能以退隱江湖的方式獨善其身,魯迅渴望的是一種強大而熾烈的反抗:吶喊的主體既是獨立的個人,同時匯聚成一個倔強的群落——“摩羅詩力”隱喻了他們的內在激情。
魯迅當然無法預料,開創現代浪漫主義文學的領銜人物竟然是他所不屑的郭沫若。郭沫若的《女神》完整地顯現了“摩羅詩力”的諸多特征。一個熊熊燃燒的浪漫主義形象從天而降。魯迅更多地傾心浪漫主義的傲視庸人、獨立不羈。相對于郭沫若的狂放與浮夸,魯迅顯現的是冷嘲與懷疑。他不適合扮演熱烈的歌者,寧愿充當暗夜的烏鴉。
面對盤根錯節的傳統社會,魯迅遠非那么樂觀。那些獲得各種新知熏陶的知識分子能否突圍?事實上,魯迅的小說更多地顯現了一批鎩羽而歸的知識分子。一種舉足輕重的解釋是,他們的啟蒙工作并未立足于撬動社會結構的理論支點:階級。
二
20世紀20年代末,許多作家已經對于“階級”的觀念耳熟能詳。回憶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一批經典之作可以察覺,作為一個社會學范疇,“家”——家庭或者家族——存留于文學之中的烙印遠為深刻。“階級”觀念開啟了嶄新的理論視野,那么,從倫理秩序、社會構造到勞動生產的經濟組織,“家”更像是傳統的遺物。“家”所制造的復雜糾葛仍然是作家銘心刻骨的人生經驗。相對于階級關系,“家”的內部包含了親人之間頭緒多端的情感漩渦——這幾乎是文學獨享的內容。
回溯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現代文學,“家”如同一個堅固的社會單元內在地嵌入人物的性格特征、命運軌跡以及各種戲劇性沖突。從魯迅的《狂人日記》、曹禺的《雷雨》、巴金的《家》到路翎《財主底兒女們》,“家”的豐富內涵壓縮于作品的各種皺折之中。父親的白發、母親的皺紋、兄弟姐妹的溫情無不意味著“家”所給予的情感庇蔭,另一些時刻,這一切可能轉換為令人生畏的負擔乃至情感鐐銬,甚至窒息投身于廣闊天地的激情與沖動。相對于清晰的階級對立,家庭內部的決裂往往帶有痛苦的情感糾纏。很大程度上,“家”的矛盾制造了許多階級矛盾無法包含的細節內容。
這個時期的文學出現了某種隱約的共識:知識分子投身社會革命之際,“家”往往成為必須跨越的首要障礙物。解放個性,自由地追求愛情;拋開沉悶乏味的日子,勇敢地踏入嶄新的生活,卷入波瀾壯闊的革命運動——無論如何,他們的行動無不具有一個潛在的前提:沖出傳統的家庭。庸俗的家庭軀殼無法孵化理想。駐守家庭如同駐守一具冰冷的傳統僵尸。
沖出傳統家庭耗盡了主人公的勇氣,他們幾乎無力對付后繼的社會壓力。許多作品帶給人們相似的感覺:作家擅長細膩地描述主人公與傳統家庭各種形式的相互沖突;然而,脫離了家庭、愛情主題之后的情節相對松弛乃至乏味。許多時候,階級并未作為另一個引擎助推后續情節的展開;進入寬闊的社會洪流,知識分子很快喪失了主角的位置,不再擔當更大范圍社會關系的組織者。正如毛澤東指出的那樣,新民主主義階段的革命領導者由無產階級承擔,知識分子毋寧是被組織的對象。階級與革命的社會圖景之中,知識分子的視角不再是作品的視角,例如《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或者《暴風驟雨》。知識分子的主角意識同時受挫,顯示出某種不適、茫然、力不從心乃至被動或者低落的狀態。對于再現知識分子成長史的作品而言,“家”或者階級構成的情節組織隱然地可以劃分為兩個段落,前者往往比后者成熟。
擺脫傳統家庭的束縛,知識分子那種激進而沖動的精神顯然屬于浪漫精神。施米特在《政治的浪漫派》之中說過,歷史上或者空間上遙遠的現實時常被浪漫主義當成“逃避當前現實的手段”。不愿意在無聊、刻板之中循規蹈矩地耗盡生命,許多知識分子追求值得以身相許的人生。這種情況之下,審美成為浪漫派的特殊表征。
浪漫派力圖以審美改造個人生活。擺脫傳統家庭可以視為這個拯救計劃的組成部分。如果階級觀念揭露出,令人厭倦的俗世包含了各種政治與經濟的不公,階級構成了這些不公的一個重要源頭,這時,浪漫派的審美不可能完成一個徹底解決的社會學方案。
因此,那一批熱衷于浪漫主義精神的知識分子通常被納入小資產階級范疇。尊重個人的內心、個人的激情,依賴一己之力獨立于渾渾噩噩的蕓蕓眾生,謀求個人生活的價值與意義而無視解放全人類的階級使命,這些浪漫主義的典型標志猶如小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產物。尖銳的文化批判背后,他們仍然與資產階級共享相同的社會關系。這種隱秘的共謀遭到了無產階級革命者的嚴厲譴責。革命領袖不斷地敦促小資產階級脫離資產階級社會關系,從而將立場轉移到工農兵陣營。
三
楊沫的《青春之歌》成功地將家庭與階級統一于革命邏輯之上。《青春之歌》設置了一段重要的情節:一次交談之中,林道靜懇求盧嘉川介紹她參加紅軍,她的抱負是在戰場上成為一個視死如歸的英雄。盧嘉川犀利地指出,這種英雄式的幻想只不過試圖逃避個人的平凡生活。革命工作并非滿足個人的浪漫情懷。《青春之歌》的出版產生了很大的反響,激烈的爭論接踵而至。爭論的焦點是小說流露的某種氣息,標準的術語稱之為“小資產階級情調”。修改《青春之歌》的時候,楊沫首先考慮的即是“林道靜的小資產階級的感情問題”。
20世紀50年代之后,批評實踐對于小資產階級的文學表現形成了愈來愈清晰的共識,否定的口吻愈來愈強硬。大約相近的時間,人們可以從文學批評之中發現相似的理論代碼,《青春之歌》《林海雪原》或者《三家巷》《苦斗》帶動的種種爭論仿佛表明,小資產階級的反面形象已經在批評家的論述之中逐漸定型。
張揚個性、傲視世俗的浪漫主義沖動曾經帶動一批知識分子掙開傳統禮教的束縛,那么,時過境遷,這種激情意外地演變為負面的文化資產。“個人”與“階級”的對立構成了演變的主要原因。考察20世紀50年至70年代的中國文學,如下幾種小資產階級情調的表現時常觸怒文學批評:
第一,“知識”往往被視為小資產階級思想的溫床。無產階級對于來自書本的知識抱有戒心。知識分子通常作為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出現。小資產階級的固執、迂腐、過度的自尊與不通世故等“酸溜溜”的情緒無不直接或間接地與“知識”聯系起來。
第二,多愁善感的內心世界。一個源頭不明的共識是,粗獷的工農兵大眾未曾也不屑于擁有一個幽深而細膩的內心世界。他們的精神領域充滿了明亮的陽光。小資產階級分子的內心世界包含了經濟利益的權衡,同時又遠遠超出經濟利益。從身世感嘆、憐憫同情、自怨自艾到貪生怕死的“一分鐘動搖”,小資產階級分子的內心纖弱、古怪、深邃、柔軟多汁同時又敏感病態,以至于可以藏匿種種資產階級的不潔病菌。知識分子往往將不健康的情緒寄托于文學藝術之中,陰陽怪氣,甚至冷嘲熱諷。
第三,除了文學藝術,多愁善感的內心世界渴求的另一個出口即是愛情以及婚姻。小資產階級分子往往信奉愛情至上的觀念。愛情至上顯然與個人主義僅僅一墻之隔。如同私有財產,愛情是個人的專屬用品,不可分享、出讓和贈送。愛情與婚姻組成的二人世界向階級共同體關閉,這個不透明的堡壘令人憂慮。兩個人之間的纏綿恩愛乃至生死不渝會不會削弱階級指令的傳導?二人世界內部是否存在某些政治無法抵達的死角?作為一個牢固的經濟單元,婚姻構成的家庭是否天然地傾向于維護個人利益?防范愛情制造的政治背叛甚至比防范對手的利誘更為困難,前者所遭受的譴責也遠遠不如后者。由于階級仇恨與跨階級的愛情形成的對決毫無勝算,一些作品干脆在批判小資產階級情調的名義之下繞開如此麻煩的情感糾葛。
第四,過分顯眼的個性以及獨特的個人風格。強大的個性時常讓批評家撓頭。當個性的邏輯溢出了階級形象的預設時,所謂的“魅力”就會成為理論無法消化的負擔。游離于階級的個人性格顯然只能判給小資產階級范疇。
上述幾種觀念顯然相互交織,彼此呼應,構成隱約而堅固的模式。由于這種模式的存在,批評實踐之中的小資產階級概念不僅擁有具體的內容,而且構成了判斷的依據。
四
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之初,恢復個性、個人風格乃至個人魅力的名譽成為文學的一個醒目的主題。人們很快接受了個性的觀念,同時,小資產階級概念逐漸式微。文學之中的“個人”形象逐漸豐滿起來。
這是一個隱蔽的理論轉換:撤消對于小資產階級的指控并非召回一個浪漫派的主體。人們的觀念是,知識、內心世界或者愛情毋寧是普通人的正常權利。一批詩人不再繼承浪漫主義的豪邁風格,他們以低沉的音調指出這個問題,并且表示了堅定的決心。一些批評家迅速地在這些詩歌背后察覺某種“新的美學原則”:“人的價值標準”發生了重要的改變。“異化”的現象必須結束。“異化”概念的重現很大程度上涉及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再研究。周揚在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際發表長篇論文《關于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專門論述“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的關系”。周揚“不贊成把馬克思主義納入人道主義體系之中,不贊成把馬克思主義全部歸結為人道主義;但是,我們應該承認,馬克思主義是包含著人道主義的”。
那些個性張揚的主體并沒有走多遠。浪漫、獨往獨來、落拓不羈或者超凡脫俗所遇到的相當一部分阻力不是來自政治觀念。世俗社會各種密集的關系如同蜘蛛網纏住了他們的手足,沒有人可以輕易地甩下。作為各種社會關系的生產機構和匯聚節點,家庭重新顯示了出其不意的作用。張承志的許多小說反復出現一個強悍而孤獨的男子漢形象。耐人尋味的是,這個男子漢所遇到的大部分阻力源于家庭,家庭時常成為世俗對于浪漫的羈絆。
許多女性作家心目中,那些爽朗、堅硬的男子漢形象時常顯現出庸俗小市民無法比擬的魅力,然而,當這一批男子漢被塞入家庭形式,令人欽慕的魅力迅速變質。張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線上》《我在哪兒錯過了你》與《我們這個年紀的夢》一直圍繞“家庭”徘徊不去。家庭的屋檐之下,女性能否始終溫柔地承受那些昂揚而堅定的強悍男子漢?從張潔的《方舟》《祖母綠》到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陳染的《私人生活》,失望正在使兩性共同組織的家庭形式成為一個愈來愈稀薄的影子。20世紀70年代末期,所謂的“傷痕文學”——例如盧新華的小說《傷痕》——即是從修復階級觀念損毀的家庭形式開始。云譎波詭的政治風云之中,家庭的穩定功能得到深入人心的強調。這個意義上的家庭通常被視為情感的歸宿。
浪漫精神之后的家庭形式迫使人們重估家庭的意義。如果說,儒家文化與階級觀念分別在倫理與政治的意義上定義家庭,那么,重估更多地在經濟學與社會學層面展開描述。
五
“愛”和“工作”分別在各自的領域運作。家庭是一個私人領域,這個空間由“愛”主管,經濟合同或者工資待遇的談判發生于家庭之外的社會領域。女權主義開始拒絕作為意識形態的“愛”,家庭是經濟體系之中遭受遮蔽的組成部分。剝去愛情制造的幻覺,家庭無異于另一個車間,按勞取酬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女性承擔無償勞動的歷史已經太久了。
這種觀念簡化了家庭的內容:家庭仿佛成為夫妻雙方計量勞動收入的爭奪戰場。多數家庭不僅存在兩性的抗衡,同時存在兩性合作——在合作的基礎上向社會爭取各種利益。池莉的《煩惱人生》或者劉震云的《一地雞毛》之所以引起廣泛的關注,恰恰因為揭示了家庭內部相互糾結的多種能量。主人公不得不從事雙重掙扎:狹窄的家庭內部,他們相互怨恨、斗氣同時又相互妥協、扶持——性別之爭很大程度地融化于不計其數的摩擦之中;浮出社會水面之際,他們不得不相互團結,同心同德地爭取各種利益最大化。
家庭清晰地顯示出賴以維持的經濟指標。異性組建家庭,同時也是一個改變出身、躋身于另一種生活質量的機會。借助家庭的跨越社會階層成為許多女性重置身份的特殊策略。家庭可能擁有的經濟指標充當了無可爭議的首要標準,情感歸宿的涵義甚至可有可無。池莉的一篇小說標題即是《不談愛情》。那些華而不實的愛情更像是擾亂心智的煙幕彈。這些主人公與魯迅的“摩羅詩力”、茅盾以及丁玲們的小資產階級或者《青春之歌》的林道靜已經相距何其遙遠。如果說,“家”曾經以反作用的方式推出了一批桀驁不馴、獨立不羈的青年,那么,現在的“家”終于讓他們平靜地安居于世俗之中。
浪漫主義精神對于財富的蔑視遭到了報復性的反彈。開始錙銖必較地計算財富之際,也就是將小資產階級身份置換為中產階級的之時。對于中產階級說來,工資、職務、房子、汽車、孩子教育以及娛樂和旅游循序漸進羅列于人生途中。理性不僅有助于安全的人生規劃,同時有助于社會穩定——后者是社會對于中產階級的期待。放棄各種非分之想,關閉種種思想維度,一切訴諸具體的物質和經驗,不再為那些看不見或者無法到手的東西浪費想象力。
叛逆的激情仍然會在某一個時刻掠過胸口。中產階級文化已經未雨綢繆,例如金庸的出現。許多年輕的中產階級分子感激地回憶說,金庸陪伴他們度過了危險的青春期叛逆階段。金庸塑造英雄大俠僅僅在繁忙的業務工作之余提供短暫的心理安慰,武俠小說并非認識歷史和現實的指南。
然而,撤消了歷史背景,人們可以在大跨度的跳躍之中構思各種別出心裁的文化幻象。安居樂業的氣氛過于沉悶的時候,不甘寂寞的中產階級可能暫時改弦易轍,快樂地重溫一回小資產階級的舊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