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水城文書所見元代亦集乃路的社會治安問題
侯愛梅
(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 古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101)
近年來,隨著黑水城文書的大量公布,學(xué)界出現(xiàn)了大量有關(guān)元代亦集乃路的研究成果。亦集乃路為元代的地方基層組織,屬于下路,地處西北邊陲,是中原到漠北的必經(jīng)之路和交通樞紐,據(jù)李逸友先生推測,亦集乃路總?cè)丝诩s在七千人以內(nèi)(1)參見李逸友:《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北京:科學(xué)出版社,1991年,第13頁。。居民的民族成分、戶籍成分和宗教信仰復(fù)雜多樣,居民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為生,兼營畜牧業(yè),商業(yè)發(fā)展有一定規(guī)模。整體而言,亦集乃路人口較少,經(jīng)濟(jì)落后、物資相對匱乏、加之自然災(zāi)害和戰(zhàn)亂,便會導(dǎo)致該路作奸犯科之事屢見不鮮,社會動蕩不安。本文主要通過黑水城出土的元代詞訟文書來對亦集乃路的治安狀況予以探析。
一、盜竊案件多發(fā)
從黑水城出土的元代詞訟文書來看,亦集乃路盜竊案件頻發(fā),在元末至元年間和至正年間此種情況尤為嚴(yán)重(2)張笑峰:《元代亦集乃路諸案成因及處理初探—以黑水城出土元代律令與詞訟文書為中心》(載《西夏學(xué)》(第一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一文,對案件發(fā)生年代做過相關(guān)統(tǒng)計(jì),認(rèn)為這些案件主要發(fā)生在元代晚期,尤其以元順帝至元、至正年間居多。。
1.盜竊案件頻發(fā)。
亦集乃路較為常見的盜竊案件是偷盜馬、驢、駱駝等牲畜。M1·0579[F111:W43]號文書中,案犯偷盜了馬和五只駱駝;M1·0583[F116:W171]號文書中,案犯偷盜一頭“七歲兒驢”[1](第四冊P720);TK231號文書中,案犯盜取官署的馬、氈等;OR.8212/737號文書中,案犯偷盜駱駝。此外,OR.8212/745號文書為刑房“追問亦速等被盜駝、馬公事”的殘呈[2](第一冊P218);M1·0589[F116:W288]號文書記錄盜馬案件;OR.8212/1122正背K.K.0118.p為“根捉盜馬賊人事”[2](第二冊P53)的卷封。由此可見,此類偷盜牲畜的案件為數(shù)不少。

元末至元年間,甚至有盜竊團(tuán)伙肆無忌憚的偷盜官署。俄藏TK231號文書記載:至元二年五月,首賊阿立渾、從賊帖木兒糾合也速答兒、楊耳、班梅等一干人偷盜官署的馬、氈等,被“公使人馬”[3](P242)捉拿歸案。偷盜官署案件的發(fā)生,也反映了當(dāng)時(shí)亦集乃路地區(qū)盜竊案件的多發(fā)和盜賊的猖獗。
2.官府大力捕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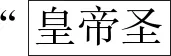
3.官府嚴(yán)懲盜竊罪犯
元代律令對盜竊罪犯的懲處較重,“諸強(qiáng)盜:持杖但傷人者,雖不得財(cái),皆死;不曾傷著人者,不得財(cái)徒二年半,但得財(cái)徒三年”,“諸切盜,初犯刺左臂,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項(xiàng)。強(qiáng)盜,初犯刺項(xiàng),并充警跡人”[4](卷49刑部十一P1625)。
對于盜竊牲畜的懲處為:“諸盜駝馬牛驢騾,一陪九。盜駱駝?wù)撸醴笧槭拙攀撸蕉臧耄瑸閺陌耸撸蕉辏涸俜讣拥龋蝗覆环质讖模话倨撸鲕姟1I馬者,初犯為首八十七,徒二年,為從七十七,徒一年半;再犯加等,罪止一百七,出軍。盜牛者,初犯為首七十七,徒一年半,為從六十七,徒一年;再犯加等,罪止一百七,出軍。盜驢騾者,初犯為首六十七,徒一年,為從五十七,刺放;再犯加等,罪止徒三年。”[6](卷104刑法志三P2657-2658)罪犯“皆先決訖,然后發(fā)遣合屬,帶鐐居役。應(yīng)配役人,隨有金銀銅鐵洞冶、屯田、堤岸、橋道一切等處就作,令人監(jiān)視,日計(jì)工程,滿日放還,充警跡人。”[6](卷104刑法志三P2656)

綜上所述,亦集乃路的盜賊叢生,盜竊案件多發(fā),有偷盜糧食、財(cái)物的,也有偷盜駱駝、馬匹的,甚至還發(fā)生偷盜官署的案件;有個人行竊的,也有偷盜團(tuán)伙集體作案的;從小規(guī)模的偷竊,到大規(guī)模有組織持刀仗盜竊,盜竊案件屢屢發(fā)生,即使官府大力捕盜,張貼防賊禁約令,給予盜賊嚴(yán)厲懲處等,也未能從根本上改變此種狀況。
M1·0584[F207:W4]號文書中,盜賊真布被捉拿到官后,坦言“雖是家貧,自當(dāng)守分”[1](第四冊P721),應(yīng)為明白事理之人,但卻于“廿九年四月廿二日巳時(shí)”偷盜完者忻的小麥,說明確為生計(jì)所迫,實(shí)屬無奈。由此可見,亦集乃地區(qū)盜竊案件多發(fā)的主要原因在于社會動蕩不安,民不聊生,于是只能鋌而走險(xiǎn),不惜付出巨大代價(jià),以維持生計(jì)。“廿九年”應(yīng)是至正年間,元朝已經(jīng)覆沒,北元政權(quán)在亦集乃路勉強(qiáng)維持。在社會大動亂的年月里,貧苦人民無糧充饑,被迫走盜竊之途,這較之中原農(nóng)民揭竿而起推翻元朝,在性質(zhì)和程度上還有很大區(qū)別(5)參見李逸友:《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第39頁。。
二、土地、財(cái)物糾紛及斗殺案件時(shí)有發(fā)生
亦集乃路居民中,土地、財(cái)物糾紛、打架斗毆及重大殺人案件時(shí)有發(fā)生,對社會治安造成嚴(yán)重危害和影響。
1.土地糾紛案件
亦集乃路地區(qū)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為主,土地是農(nóng)民主要的生產(chǎn)資料,因此,爭奪土地的糾紛較多,黑水城所出元代詞訟文書中,有關(guān)土地糾紛的文書共有108件。其中,M1·0603[F116:W98]號文書為孫占住與陳伴舊爭地案的告攔文狀,M1·0610[F116:W491]號文書為狀告僧人梁日立合只、古失赤馬合麻侵占土地偷種收割的訴狀,M1·0606[F9:W34]號文書為站戶汝中吉狀告土地被人強(qiáng)占布種等。還有因天災(zāi)人禍,負(fù)債累累而被質(zhì)佃土地的,例如M1·0604[F17:W1]號文書中,站戶吾七玉至羅因欠債將土地抵給債主,M1·0609[F14:W14]號文書也為質(zhì)佃土地的文狀。
水利是農(nóng)業(yè)的命脈,亦集乃路屬于沙漠戈壁包圍中的綠洲地帶,水利資源就顯得尤為重要,無水灌溉也就無糧可收,因此,爭奪水利資源,強(qiáng)行灌溉的事件在亦集乃路屢見不鮮。M1·0605[Y1:W66B]號文書即為狀告訛屈率領(lǐng)嵬如法師等20人,強(qiáng)行開閘灌溉。嵬如法師和上文提到的梁日立合只均為僧人,連僧人都參與爭奪土地和水利的事件中,可見生活在亦集乃路的居民珍視土地占有權(quán)和要求保證收成的迫切心情。
此外,亦集乃路還有居民想在城內(nèi)和關(guān)廂地帶的官府公地上,蓋房居住或者經(jīng)營生意,狀呈官府批準(zhǔn)并發(fā)給公憑。M1·0624[F116:W476]號文書為購買城南地土的呈狀,M1·0607[F209:W55]號文書中,昔寶赤軍戶狀呈官府想占用天牢南無主地基建房,諸如此類的占地申請,一般是由有權(quán)勢有錢物者呈遞的。
2.財(cái)物糾紛案件
從黑水城出土的元代詞訟文書來看,亦集乃路因財(cái)物糾紛而上告官府的文書不多,大部分為市民拖欠貨款抵賴不歸的案件。例如,M1·0597[F144:W6]號文書為狀告王旭拖欠貨款,故意到甘州躲債;M1·0595[F193:W12]號文書中,孫直在甘州路拖欠貨款后,逃回亦集乃路,被押解到官府。財(cái)物糾紛案件中,還有一部分為農(nóng)村居民遭受蒙騙,被騙走糧食、牲畜等的案件,例如,M1·0598[F79:W41]號文書中,朵立赤等趕走事主一只黑花牛; M1·0596[F4:W7]號文書中,狀告愛的斤與貝寧普騙取小麥。M1·0960[F1:W94背號文書中,欠債人已經(jīng)交付駱駝,并有字據(jù)為憑,而債主景朵歹卻要二次索取駝只。
3.斗毆和謀殺案件
亦集乃路地區(qū)時(shí)常發(fā)生打架斗毆事件,例如,M1·0563[F80:W9]號文書中,回回包銀戶亦不剌興狀告其侄女婿喬典,向其索要菜羊錢鈔十一兩,并對其進(jìn)行毆打;M1·0567[F17:W2]號文書中,狀告貫布思吉、贊布謾罵行兇。M1·0566[F146:W23]號文書為狀告不闌奚弟子、孩兒持棍打人。其中,有因打架斗毆致傷或致死的,例如M1·0562[F111:W74]號文書中,官府派人對被毆人耳為立進(jìn)行傷檢、調(diào)查并差袛侯將涉案人員監(jiān)押到官;文書M1·0564[F2:W54]中,捨赤壓供認(rèn)在雙方斗毆時(shí)將對方捆綁,用“褐一卷,口內(nèi)填塞身死”[1](第四冊P700)。
亦集乃路還發(fā)生過一些故意殺人,通奸謀殺等重大刑事案件。M1·0568[F166:W12]號文書中,罪犯將人“燒殘,紅柳棒打傷身死”[1](第四冊P704);M1·0570[F21:W3]號文書中,皇慶年間,婦人忽都龍供認(rèn)在奸夫指使下扼殺其夫。這些重大刑事案件的發(fā)生,在亦集乃路造成了重大的社會影響。
三、流民問題嚴(yán)重
1.亦集乃路的流民問題
流民,在元代始終是一個嚴(yán)重的社會問題,大量編戶齊民為躲避戰(zhàn)亂、自然災(zāi)害或繁重賦役等,外逃流徙,政府無法控制,在影響稅收的同時(shí),也加劇了整個社會不穩(wěn)定的因素。流民大量出現(xiàn),標(biāo)志著社會矛盾趨于尖銳化,而流民問題愈來愈嚴(yán)重以致政府無法控制時(shí),大規(guī)模的農(nóng)民起義也就迫在眉睫了。[7](P132)

因亦集乃路地處西北荒漠之中,雖地瘠民貧,但相對而言,戰(zhàn)亂較少,紅巾軍起義波及該地較晚,因此,有不少外地編戶齊民因種種原因逃到亦集乃路,這些流民應(yīng)該為數(shù)不少,多于亦集乃路流出的人口。
2.流民引發(fā)的社會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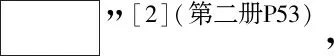

3.官府管理流民的措施
從黑水城出土的元代詞訟文書來看,亦集乃路官府對于該路的外逃人員,采取支持其回到亦集乃路復(fù)業(yè)的政策。也火汝足立嵬地土案件中,也火汝足立嵬家族本為亦集乃路站戶,因躲避戰(zhàn)亂逃亡別處,時(shí)隔九十年后,又回到亦集乃路要求復(fù)業(yè),甘肅行省指示亦集乃路總管府辦理此案。亦集乃路總官府縣查明過去的土地檔案,進(jìn)而派人丈量土地,調(diào)查也火汝足立嵬家族原有田地的使用情況等,應(yīng)該說亦集乃路總管府審理此案的態(tài)度比較積極,這與亦集乃路站戶消乏嚴(yán)重,急需站戶及元政府招誘、鼓勵流民復(fù)業(yè)的政策有關(guān)。
但對于涌入本地的流民,亦集乃路總管府并沒有采取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而是任其自生自滅,這在客觀上加劇了亦集乃路社會動蕩,治安混亂的狀況。
四、百姓違抗官府事件
亦集乃路自上而下的各級統(tǒng)治機(jī)構(gòu)完備,亦集乃路總管府在組織軍民興修渠道、開發(fā)屯田、發(fā)展經(jīng)濟(jì)以及維持封建統(tǒng)治秩序等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因元朝統(tǒng)治日益腐敗,加之戰(zhàn)亂、農(nóng)民起義和自然災(zāi)害的嚴(yán)重影響,元末時(shí)期亦集乃路地區(qū)百姓的生存狀況日益惡化,難以維持生計(jì),在此情形下,如遇官府壓迫或不公,難免發(fā)生毆打職官,公然違抗官府決議的事件。
1.毆打職官
M1·0561[F116:W294]號文書中,“取狀人王漢卿,右漢卿年四十六歲,無病,系冀寧路汾州孝義縣附獲民戶,家在□□住坐,即目見在亦集乃屯田耳卜渠羅信甫家安下,今為務(wù)官西卑祿壽狀呈漢卿等將伊毀罵,將欄頭阿立嵬毆打等事,已蒙取允漢卿,略莭招伏,照收在禁。致蒙再責(zé)已來,漢卿依實(shí)招責(zé),根腳元系冀寧路汾州孝義縣附獲民戶”[1](第四冊P697),末尾有王漢卿的畫押。該件文書為犯人王漢卿的取狀,王漢卿招認(rèn)毀罵稅務(wù)官西卑壽祿,并毆打欄頭阿立嵬。
亦集乃路設(shè)有稅使司,專門負(fù)責(zé)錢物課程,凡屬抽分羊馬、商業(yè)貿(mào)易等稅務(wù),均由稅使司辦理。稅使司設(shè)有大使、副使及稅務(wù)官,并在各渠社委派欄頭,負(fù)責(zé)抽分羊馬,即征收牲畜稅,均折價(jià)收取銀鈔。亦集乃稅務(wù)官員在征稅過程中,霸道無禮,甚至不給正式收據(jù),較為混亂,個別稅務(wù)官員甚至到其轄區(qū)外征稅,M1·0066[Y5:W11a]號文書就是甘肅行省指責(zé)亦集乃稅務(wù)官員進(jìn)入肅州路阿兒巴地面抽分羊馬的劄付。不少欄頭隨意在亦集乃路境內(nèi)點(diǎn)視和抽分牲畜,百姓對此怨聲載道,王漢卿,年已四十六歲,出手毆打稅務(wù)人員可能正是出于此因。對于稅務(wù)吏目竟敢毆打辱罵,必然要被官府收禁審訊。王漢卿有理抗稅,但一經(jīng)出手打人,便構(gòu)成了毆打職官罪。元代律令規(guī)定:“諸以物毆傷職官者,加一等,笞五十七。諸小民恃年老,毆詈所屬官長者,杖六十七,不聽贖。”[6](卷105刑法志四P2674)在王漢卿的取狀中,只寫明毆打職官,并未提及被毆者是否受傷,很可能被毆者并未體破受傷,但無疑王漢卿定遭官府笞杖嚴(yán)懲。
2.違抗官府決議
M1·0606[F9:W34]號文書中,站戶汝中吉的土地被人強(qiáng)行奪占布種,且不交租稅,汝中吉兩次告狀,甚至赴省告狀。該案件發(fā)生在至正十八年,當(dāng)時(shí)農(nóng)民起義風(fēng)起云涌,亦集乃路也受影響,民不聊生。一些農(nóng)民在人帶領(lǐng)下,聚眾奪去站戶汝中吉的土地,官府派員初次歸斷無效,汝中吉無奈,二次上告,官府?dāng)M做二次歸斷。為保證驛站暢通,官府定會支持站戶,至于二次歸斷能否有效,已無從得知。
由此可知,元末的亦集乃路,為生存所迫,民不畏官,甚至敢于公然抗官,不執(zhí)行官府決議,雖為個別事例,但也足以說明元末亦集乃路官府的統(tǒng)治已岌岌可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