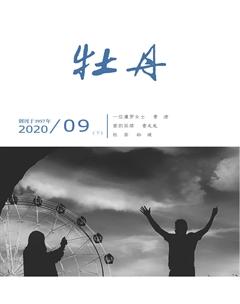《寒夜》中的婆媳矛盾分析
劉張賀薇
巴金的小說《寒夜》描寫了抗戰勝利前夕,國統區里一個普通小家庭的悲劇故事。該小說以婆媳矛盾作為主要矛盾,婆媳矛盾是文本敘事的重要組成部分,推動了劇情的發展。文本中,樹生與婆婆之間的矛盾表面看是對同一個男性的“愛”的爭奪,但其深處隱藏著的是家庭結構中的權力爭奪以及女性的“自我厭惡”,展現出現代女性的生存困境和巴金對新舊女性生活方式的思考。事實上,《寒夜》中的婆媳矛盾構成一對功能性關系,用以指稱新舊女性觀念間的沖突與裂痕。
一、《寒夜》中婆媳矛盾的表層及深層闡釋
在中國社會中,男人價值的獲得來自“霸權世界的爭斗”,在對社會生存資源以及權力的爭斗中獲得自我主體性和身份的確認。男性在這樣的霸權斗爭中獲得以“男人之間的紐帶”為表現形式的“男性同性社會性欲望”,形成某種同性的社會性共同體。同性社會共同體其實是對分配社會資源的成員的資格確認,也是對自我和社會身份的確認。在中國社會長久的發展過程中,女人以歸屬男人為取得社會成員資格的唯一途徑,即女性一般通過成為“媽媽”“妻子”“女兒”,與某一個特定的男性建立聯系而實現自我身份的確認。因此,傳統社會中的所有女人都因男人的歸屬而互為潛在的競爭對手。婆媳之間的矛盾正是這種“競爭關系”的最好表述。
在《寒夜》中,婆媳之間的沖突可以表述為對汪文宣的“愛”的爭奪或者說“控制”的爭奪。從對話上看,首先呈現為頻繁出現的冷落忽視對方以及壓制對方話語的策略。在汪文宣得肺病后,汪母請張伯情來看病,后發生以下對話:“‘哪里有藥醫不好的道理?母親不以為然地說,她拆好了藥方。‘我去給你拿藥。她拿著手提包,預備走出房門。‘你身邊的錢不夠罷?他問道。‘我這里有錢。妻馬上接嘴說。‘我有。母親望著他說,并不看妻一眼,好像沒有聽見她說話似的。”在這一段對話中,曾樹生想借承擔買藥的開支拉近與婆婆的關系,對在這個家庭中的成員身份進行確認,汪母拒絕使用樹生的錢,事實上也試圖否認樹生以及文宣之間的“丈夫-妻子”聯盟。
汪母與樹生之間的爭奪還體現在以話語壓制對方,從而對文宣的行動進行掌控。文宣病后,公司派鐘老傳達辭退信息,引發文宣的傷感,樹生與文宣搭話以調節其煩悶的心情,但這時汪母突然插入,打斷了對話。小說文本寫道:“‘宣,你講話太多了。睡一會兒罷,又快要吃藥了。母親不耐煩地干涉道。妻暗暗地瞪了母親一眼。她走到方桌前坐下來。她坐在那里不知道應該做什么事好。沒有人理她,連小宣也不過來跟她講話。”在《寒夜》中,這樣的打斷式對話不止發生過一次,婆婆打斷兒子、兒媳之間的對話,并對兒子進行命令式的勸告,從而對自己的家庭地位進行確認。在樹生走后,這種控制就跳過了打斷這一迂回的手段,擁有了直接的顯性表達。例如,小說文本寫道:“他也喜歡看書,走動,說話,這使他覺得自己的病勢不重,甚至忘記自己是一個病人。但是母親不讓他多講話,多看書,多走動;母親卻時時提醒他:他在生病,他不能象常人那樣地生活。”從汪母的角度來看,她對于兒子的病甚至報以“慶幸”的態度,由于生病,兒子重新回到“兒童”狀態,不得不依靠她的照顧,而看病、煎藥、照顧這一過程也使她重新擁有了對兒子的“掌控”。汪母將為兒子吃苦,照顧兒子,甚至為兒子獻出生命,視為自己的價值,并在這一過程中實現對自我主體性的確認,對她來說,媳婦的出現妨礙了這一價值確認的過程。
《寒夜》中,婆媳之間對家庭權力的爭奪還運用了“他者化”的策略,將對方與自己劃分入不同的“陣營”。例如,“妻從窗前掉轉頭來,冷笑道:‘我好另外嫁人——這樣你該高興了!‘我早就知道你熬不過的——你這種女人!母親高傲地說。她想:你的原形到底露出來了。‘我這種女人也并不比你下賤。妻仍舊冷笑說。‘哼,你配跟我比!你不過是我兒子的姘頭。我是拿花轎接來的。母親得意地說,她覺得自己用那兩個可怕的字傷了對方的心。”在這段爭吵中,汪母與樹生分別將自己與對方劃入“我這種女人”與“你這種女人”兩個互相對立的陣營。汪母以是否拿花轎娶來的為劃分依據。父權制對于女人與孩子的歸屬做出規定,在某一男子的支配或控制下的那女人和孩子被分配一個特定的席位,而在父權制社會中沒有登記注冊的女人則無法獲得席位。在男權社會下,男人以此制定劃分“娼妓”與“圣女”的標準。而生長于舊社會的汪母顯然已經將這樣的標準內化為自己的價值觀。于是,她將具有一定現代性的樹生作為不可理解之物,從“我們”中放逐出去,完成“他者化”的過程,其背后其實也隱隱可以看出汪母身為女性的自我厭惡。女人作為“社會性弱者”,不可避免地面臨著“范疇的暴力”,制造與劃分范疇的是具有支配性力量的社會集團,女性事實上并沒有參與制造話語體系并選擇話語范疇的自由,有的只有被迫接受某一種范疇規定的“自由”。而由男性制定的“女性”之范疇,其中自然而然地承載了男性對于女性的輕蔑。當汪母出生之時,“女人”“母親”的定義已經被事先規定,她只能接受這樣的一個“范疇”,但在她接受“范疇”時,必須同時接受這個范疇中承載的“歷史負荷”。對于“女性”這一性別的自我輕視事實上已經存在于汪母的價值體系中。在性別與身份的差異被視為無可更改的命運時,這種自我輕視未必會得到清晰的體現,而樹生的出現意味著傳統性別與社會身份的結構在某種程度上出現了松動,在這樣的對比中,汪母對于自我性別的輕視其實已經“爆發”。為了重新在自我輕視與自我價值之間找到平衡,汪母于是采用這種“他者化”的邏輯,將“同為女人”這一“公約數”去除,使得性別與社會地位之間的關系重新歸位于具有決定性的命運。
二、婆媳矛盾的敘事意義
雖然婆媳矛盾是《寒夜》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內容之一,但《寒夜》顯然并不以討論婆媳問題為主要目的。20世紀初,西方涌入的文化思潮與中國社會內部的改革動力,共同形成沖擊傳統思維文化的合力。而作為舊道德與舊倫理的代表,傳統的家庭制度也成為被批判與否定的對象,女性作為被壓迫、被奴役的代表,開始走進人們的視野,走進文學的敘事領域。現代男性作家書寫婆媳之間的矛盾,一般都帶有反對傳統、反對封建的目的。《寒夜》中的婆媳關系更多的是一種具有功能意義的指稱,以婆、媳代表當代女性的兩種生存狀況,并通過最后的悲劇性結尾對這兩種生存狀況背后的生存邏輯進行反思。
籠統而言,可以將汪母與樹生歸為“新”與“舊”的不同陣營。樹生受過新式的教育,與文宣通過自由戀愛而結合,有自己的工作并且具有一定的經濟能力。汪母則是舊式社會下的才女,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嫁給了汪父,是賢妻良母型舊式女人的代表。但巴金對于所謂“新”“舊”的態度并不是簡單的二元對立。樹生有自己的工作,但所謂職業不過是在銀行里當當“花瓶”,究其實質只是對女性的性別符號的利用,很難真正地被認為是一種職業。樹生也曾對“花瓶”的位置有過不滿,但在敘事發展中逐漸演變為一種“慶幸”以及“沾沾自喜”。小說文本寫道:“她并不愿意做‘花瓶,她因此長苦悶,發牢騷,可是為了避免生活上的困難,為了避免吃苦,她竟然甘心做‘花瓶”。在與婆婆博弈的過程中,擁有經濟來源一直是樹生的底氣所在,也是她劃分“我”與“你”的維度,但是她所謂的經濟獨立仍是依附于強大的男權話語,將身體作為謀生的本錢。與汪母依靠家庭而活其實并不存在本質上的區別。樹生希望自己旺盛的生命力能夠得到伸展的空間,她在給文宣的信中寫道:“我的錯處只有一個。我追求自由和幸福。”但是,她所追求的生命力與自由實際上是一個虛無縹緲的概念,“我愛動,愛熱鬧,我需要過熱情的生活”。她的追求也不過是個人的享樂。她常常覺得苦悶與空虛,卻以為這僅僅是無名的惆悵,從來沒有想過這種苦悶事實上是來自沒有出路的未來與無法解決的矛盾。她甚至從不曾為改變生活做過任何斗爭,她不愿做“花瓶”又滿足于“花瓶”帶給她的較為充裕且輕松的生活,她仍然愛著、關心著文宣,卻仍為陳經理的追求與愛慕沾沾自喜。她最后選擇離開家庭,雖然暫時地擺脫了婆婆的仇視與丈夫的懦弱,但她接下來的生活會是怎樣的呢?固然,她并不十分愿意嫁給比自己小的陳經理,但她或許仍難以擺脫他的“糾纏”。與陳經理決裂對樹生來說意味著必須離開大川,重新安排生活,但這樣的勇氣顯然是她不具備的。巴金猜測“她可能會在陳經理的愛情里尋找安慰和陶醉”,但這仍是作為某個審美符號依附著男權社會而生存。
汪母是舊式家庭中典型的“妻子”與“母親”。她愛文宣,愿意和兒子一起吃苦,愿意為兒子當掉自己僅有的財產。但是這種愛也是極其自私且頑固的。她對樹生的敵意背后其實是對于新式生活的不適應。新式家庭中的媳婦不再對婆婆百依百順,這似乎讓汪母覺得自己“多年媳婦熬成婆”的辛苦都付諸東流。她看不慣媳婦“花瓶”的生活,自尊心讓她難以接受用媳婦的錢度日,但她不得不間接地花媳婦的錢。她總覺得兒子落得這樣的境地,是因為媳婦“不能像她那樣把整個心放在一個人身上”。在《寒夜》中,汪母很大程度上是傳統的父系社會法則的執行者,在新式生活面前手足無措的汪母仍極力想要維持她所熟悉的男權文化等級性行為的社會規范。
婆媳之間的劇烈矛盾與沖突事實上或許代表著女性心靈的兩種探索。當曾經熟悉的社會規范逐漸解體時,在新與舊的交界處,該怎樣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其實是婆媳兩人代表的兩類社會人群所面臨的共同困境。固守傳統秩序的汪母失去了唯一的支柱,而出走的樹生最后無家可歸,兩種生活方式的探索最后都走進了黑暗中。即將崩潰的舊制度、舊社會與剛露出曙光的新制度、新社會,像兩座大山,這兩個“發狂”的人雖然瘋狂逃竄,但是隨后仍落入夾隙之中。在小說的結尾,樹生從蘭州回到重慶,熟悉的“家”卻已經在無聲中分崩離析,“死的死了,走的走了”。明天又該如何呢?樹生最后試圖回歸的嘗試是十分具有象征意味的結尾,出路到底在哪里呢?或許只有兩種女性氣質的結合才能在那樣的年代找到出路。但在那時的國統區,似乎根本不存在讓她們結合的機會,“她等待著明天”,但是明天似乎那么的遙遙無期,剩下的只有無盡的寒夜。
(廈門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