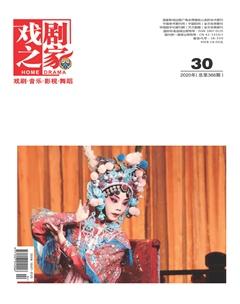古希臘城邦政治的“陰謀”
鞏睿鋒 馬忠臣
【摘 要】古希臘悲劇作為被公民和希臘城邦所崇尚和重視的嚴肅劇,在維護希臘各城邦的繁榮與和諧中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亞氏的“模仿說”與西方的藝術發展之間有著不可言喻的聯系,本文通過分析亞里士多德《詩學》中悲劇“行動的摹仿”與“情節中心”的前后關系,得出悲劇對希臘公民行為選擇的節制作用。筆者結合上述結論,再聯系城邦和公民之間的關系,結合亞里士多德的其他觀點,闡釋出古希臘悲劇在維護城邦和諧完善作用中對公民的作用。
【關鍵詞】模仿說;古希臘悲劇;詩學;嚴肅劇
中圖分類號:J805 ? 文獻標志碼:A ? ? ? ? ? ? ?文章編號:1007-0125(2020)30-0015-02
目前,關于藝術的起源有著眾多說法,亞里士多德的觀點——藝術“模仿說”,對西方藝術發展產生了廣泛且深遠的影響。亞里士多德的不朽名著《詩學》無疑是一篇有分量、有氣度的大家之作,在《詩學》中亞氏探討了人的天性與藝術摹仿的關系、構成悲劇藝術的成分、悲劇的功能、情節的組合等等。《詩學》中的相關理論、觀點對學者們研究古希臘戲劇提供了有效的參考依據。古希臘悲劇作為被古希臘公民和城邦所崇尚和重視的嚴肅劇,在希臘城邦的和諧完善中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根據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對悲劇的闡釋,他認為悲劇“是對行動的摹仿”,強調悲劇組成的成份中,情節是靈魂。那么,亞氏為何會強調悲劇中的“情節中心”作用,又為何定位悲劇是對“行動”的摹仿。筆者認為,應該首先理清希臘悲劇“行動的摹仿”與“情節中心”的前后關系,再結合亞里士多德的其他觀點,聯系城邦和公民之間的關系,總結古希臘悲劇對古希臘城邦公民行為選擇的節制,闡釋古希臘悲劇在維護城邦和諧完善作用中對公民的作用。
一、悲劇“行動的摹仿”中的“情節中心”
亞氏的《詩學》當中關于悲劇的相關論述:“悲劇是對一個嚴肅、完整、有一定長度的行動的摹仿,它的媒介是經過‘裝飾的語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別被用于劇的不同部分,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動,而不是敘述,通過引發憐憫和恐懼使這些感情得到疏泄。”[1]按照這樣的定義,悲劇摹仿的“行動”是有著一定長度的行動,是悲劇作品中悲劇主人公經過思考,并且有目的的一種行為活動。因而“行動”是一個貫穿悲劇始終的行動,是導致悲劇結果的關鍵,這種一定長度的行動當中,恰恰體現著表現亞氏的悲劇要求的另一個觀點——“情節至上”。
古希臘悲劇家索福克勒斯的悲劇作品《俄狄浦斯王》被亞里士多德稱為“十全十美”的悲劇,以該劇為例:悲劇《俄狄浦斯王》中主人公俄狄浦斯的行動,分為得知預言離開自己的養父母、來到忒拜城誤殺自己的親生父親、猜中謎語當上國王、按照習俗娶母為妻、消除瘟疫追查兇手、得知真相刺瞎雙眼。當俄狄浦斯得知弒父娶母的“神示”,并做出躲避這一預言的一系列行動,他的悲劇就注定了。同樣,在另一部悲劇《被縛的普羅米修斯》中,普羅米修斯將火的秘密透露給了凡人,也因此受到天神宙斯的懲罰;在悲劇《美狄亞》中,美狄亞跟伊阿宋在一起,并殺害自己的弟弟,伊阿宋移情別戀,美狄亞殺死自己的兩個孩子等,悲劇主人公的這一系列“行動”,構成了悲劇的“突轉”和“發現”,也構成悲劇作品的整體的悲劇情節。因此,悲劇對一定長度的行動的摹仿需要情節的顯現,“行動摹仿”是前提,“情節中心”是總括,前者是后者的基礎。
二、悲劇情節的“行動節制”功能
亞里士多德將悲劇的構成成份歸納為六個部分,分別是:情節、性格、言語、思想、戲景和唱段。在他看來,悲劇人物的行動所誘導的故事情節是古希臘悲劇的靈魂所在。行動的摹仿構成了悲劇情節的“突轉”和“發現”,順承地也構成了悲劇的簡單情節和復雜情節。亞里士多德倡導的“情節中心”與“人物中心”不同,表現人物的“性格”和“言語”并沒有情節重要。從人物的性格和品質來看,悲劇人物可能偉大,但造成人物悲劇的結果主要是情節引發的“行動的摹仿”。
在《解讀亞里士多德<詩學>中的情節中心論》一文中,作者結合了《尼各馬可倫理學》《政治學》等著作的相關觀點,分析出了亞里士多德重視情節、強調行動的原因,分析了構成悲劇情節的“行動”的倫理功能、政治功能、教育功能。這里需要單獨指出的是,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悲劇能產生一種對“行為”的節制功能,這是悲劇產生的獨有的效果。而所謂“行為節制”,就是希臘公民通過觀看悲劇時產生的憐憫和恐懼,從中審視自身命運,激發對情節引發悲劇的人物行為的遠離意識,從而選擇并控制自己的行為。正如亞氏所說的:“人的性格決定他們的品質,但他們的幸福與否卻取決于自己的行動。”[2]在古希臘的悲劇演出中,演員和合唱隊共同承擔演出任務,演員扮演角色,合唱隊負責開場結尾、場景轉接和氣氛的吟唱。在悲劇演出時,演員時常會發出對人性脆弱、生命無常、命運難逃的感嘆和感慨,甚至會說出一些警示世人的話語。這些言語會讓古希臘公民產生憐憫和恐懼,激發對悲劇人物導致悲慘命運的行為的遠離意識,并從中審視自身命運,從而選擇并控制自己的行為。作為觀劇的公民在觀看悲劇時,常常會通過這種方式和悲劇情節中人物的悲慘命運,認識到命運的不可抗拒和不可知性,并在以后的生活中時刻警惕自己的行為,避免自身悲劇的發生。行為由自身發出,自身的行為通常能改變抉擇、選擇命運。悲劇中人物因行為而導致的命運悲慘,讓古希臘公民在觀看悲劇時受到強烈的震撼。因此古希臘悲劇有著“行為節制”的功能,這種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規訓著公民自身的行為。
另外,古希臘的悲劇作品的“行為節制”作用,也借助悲劇作品中的“神”來發揮效果。比如在悲劇《被縛的普羅米修斯》中,普羅米修斯將用火的秘密泄露給了其他人,從而受到來自宙斯的懲罰。“神”的參與,更加讓劇中人物的悲劇彰顯出一種命運的不可抗拒性。這種命運的不可抗拒,更加讓古希臘公民產生恐懼,進而使他們審視自身,規避導致劇中人物悲劇的行為。
三、古希臘悲劇與城邦政治間的關系
公民的生活是否和諧,自身的命運是否悲慘,由自己的行動決定。古希臘公民通過觀看悲劇不僅能陶冶情操,審視自身行為,還能通過悲劇對自身起到一定的教育作用。一方面,在古希臘時期,公民想要受到教育,通過讀書寫字基本是不可能的,因為當時沒有造紙術,只能用昂貴的羊皮來寫字,普通公民用羊皮來學習,是不太現實的。觀看戲劇的門檻則比較低,只要能看,能聽,便可以。“戲劇表演一年中約兩三次,其中以三月份的大型狄奧尼索斯節的戲劇表演最為熱鬧,一般為期6天,以悲劇為主。戲劇節期間每天至少上演3部四聯劇,因此,天一亮就開演,一直演到晚上。觀眾必須帶足食物、水果和飲料。”[3]觀看戲劇表演成為了古希臘公民主要的娛樂活動之一。另一方面,亞里士多德的另一著作《尼各馬可倫理學》對城邦公民的行為進行了論述,該著作中談到了德性問題,認為德性意味著選擇,人要進行正確的選擇,就要培養公民德性,而德性需要學習和摹仿。這可以與悲劇對“行動的摹仿”中強調的行動聯系起來。悲劇是“嚴肅”的,能感染和熏陶公民情感,刺激他們的行動。這樣看來,觀看悲劇不僅僅成為了希臘公民重要的娛樂活動,悲劇劇場也成為了公民接受教育的重要場所。
亞里士多德所處的年代,正是古希臘大小城邦之間戰爭不斷的時代,亞氏不僅重視公民教育,對城邦的和諧完善也十分重視。古希臘時期,希臘的主要的政治形態是城邦,在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中,“城邦正是若干公民集合在一個政治團體以內就成為一個城邦。所以,公民是城邦的基本要素,他們是屬于城邦的人。”[4]“說明了公民是城邦的基本構成,只要有公民的存在,形成一種政治團體加以管理,那么城邦就是存在的,并且公民不屬于家庭,也不屬于個人,他們是屬于城邦的。在亞氏的眼里,城邦是唯一的國家架構方式,并且還可以實現城邦與公民的和諧統一。”[5]公民與城邦是共同體,公民會對城邦有一種集體認同的精神。實現城邦和諧不僅要依靠公民的德性行為,依靠公民之間產生的同類感、社區感和同胞感,也要依靠公民之間相互關愛、相互承擔命運的使命和共同承擔城邦和諧完善的責任。正如英國政治學家瑪莎·努斯鮑姆所講的一樣:“人性的同情與關愛是支撐希臘民主制度的情感基礎。”[6]
四、結語
古希臘悲劇在于“嚴肅”,而不在于“悲”,是希臘公民所崇尚的嚴肅劇。一方面,悲劇得到了城邦的大力支持。不僅希臘的悲劇作家得到了重視,并且城邦發放“觀劇津貼”鼓勵公民參加觀看。另一方面,悲劇摹仿的“是比今天的人好的人”,通過觀看悲劇表演,能讓希臘公民在觀看到悲劇時引發自己的情感和恐懼,審視并節制自身行為,避免悲劇命運發生在自己身上。由此可見,亞氏的《詩學》將古希臘悲劇定義為“行動的摹仿”,在一定程度上都發揮著培養公民德性行為、維護城邦和諧完整的作用。
參考文獻:
[1][2]亞里士多德.詩學[M].陳中梅,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3]哈里斯.古希臘的生活[M].李廣琴,譯.太原:希望出版社,2006.
[4]亞里士多德.政治學[M].吳壽濤,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5]趙彩絨.城邦正義、德性行動與公民幸福[J].社科從橫,2016.
[6]瑪莎?努斯鮑姆.藝術不制造敵意,而在于用愛求正義[EB/J].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