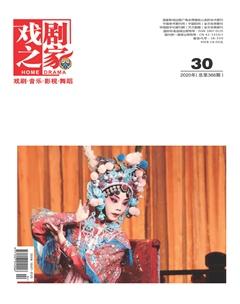“后真相”時代網絡謠言的話語空間與輿論話語場研究
李蓉蓉
【摘 要】2016年《牛津英語詞典》將“后真相”收錄為年度熱詞,開啟了“后真相”時代。隨著互聯網的發展給網絡謠言提供了更有力的條件,網絡謠言的標題、傳播內容、傳播機制成為了重點研究方向。除此之外,受眾為何在官方辟謠后仍持懷疑態度,輿論的主流話語場和網絡話語場存在什么樣的關系仍需要仔細研究考慮。
【關鍵詞】后真相;網絡謠言;輿論話語場
中圖分類號:G206.3 文獻標志碼:A ? ? ? ? ? ? ?文章編號:1007-0125(2020)30-0185-03
移動互聯網時代,社交媒體的發展讓原本社會化的媒體逐漸轉向為圈層化、部落化。大數據計算、精準推送加速了圈層化的快速形成,同時“信息繭房”也促進網民在自己的小小圈層中獲得信息、分享資訊、宣泄情感以及進行人際交往。因此,導致了圈層產生過濾氣泡,對于某些圈層不利的負面消息被自然過濾,使得受眾獲得的并非全面完整的信息,而是被扭曲甚至是篡改過的信息。這就導致了人們在接受到一些被過濾信息后會被情緒左右從而失去了理性判斷的過程,這就促進了所謂的“后真相”時代的來臨。也正是在網民被情緒所左右的時代里網絡謠言變得越發肆意,例如在新型肺炎期間利用網民對于某些敏感事件進行謠言傳播,引發社會大眾的不滿情緒,后又陸續出現主流媒體對相關謠言進行辟謠,既引發了社會恐慌也浪費了公共資源。所以,本文將對網絡謠言的話語空間、辟謠的有效途徑以及兩種輿論話語場進行分析探究。
一、“后真相”時代網絡謠言的話語空間
(一)“后真相”時代的概念
2016年“后真相”被收錄為《牛津英語詞典》年度詞匯,隨著信息傳播的“繭房化”和社會關系的圈層化,信息傳播的是否是事實已經變得不再重要,情緒和情感變成了評判信息的重要因素。后真相時代,事實真相并沒有被扭曲、改變,只是真相變成了次要的條件,網民不再相信媒體呈現給他們的事實,只相信自己的感覺,只愿意去聽、看自己所相信的東西。例如前兩年的重慶公交車墜江案,在還沒有調查清事故的主要原因時,僅憑當時的幾張圖片,網友就將事故的主要責任人認定為對面車道的女司機。這類事件并非個例,或許是女司機給公眾的刻板印象,讓網友不加思索地就將全部的悲憤情緒發泄在了女司機身上。調查結果出來后,輿論立即發生了反轉,網友紛紛道歉。這樣的事件近年來屢屢發生,更加印證了后真相時代的特征。
(二)網絡謠言標題修辭策略
互聯網時代信息碎片化和內容隨機抓取,導致了“標題黨”的出現。這類人群的主要目的是通過吸人眼球的標題來促使網友點擊觀看,但內容與標題嚴重不符,標題超過內容成為了信息消費的“抓手”。因此對于標題如何建構的研究有著重要的價值,以往傳統媒體下,新聞大多采用單行標題或兩行標題的形式,所以對于傳播者和受眾來說在標題中可以獲得最有價值的信息。但在互聯網平臺上不難發現標題呈現出越驚奇越受歡迎的態勢。據相關統計,新聞媒體的新聞標題平均為16個字左右。字數越多意味著可以提供的信息越多,如《李天一他媽的要求 高律師不干了》這個標題中涉及到了三個人物、狗血的情節還有懸念大吊人胃口。同時,更多的字數提供了更多轉移視線的空間,便于標題制造轉折,增加標題的戲劇性和張力。①在很多謠言的標題中大多使用的是第一或第二人稱,從表面上制造出自己是事件的親歷者,講述的是自己的故事,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并且方便制造出一些內心自我獨白來引起受眾的同情心。并且在標題中喜歡用“某某專家”“學者”“業內人士”等字眼來增加消息的權威性。
(三)網絡謠言議題建構策略
如果說標題的修辭是謠言傳播的形式,那對于謠言內容最為重要的就是相關議題的建構,謠言議題的建構是將謠言進行傳播包裝的有效手段。在謠言的議題中不難發現,科普類和社會時政類的謠言在數量上涉及較多,這類議題可以非常輕易地勾起人們對于自身和社會黑暗面的恐慌,所以更加有利于增加點擊量。例如近期的新冠病毒防疫工作中,民眾在聽到雙黃連可以有效防止病毒的傳播后紛紛不加思考地去藥房進行購買,短短一晚上雙黃連就脫銷了。后來被官方證實并無科學實驗可以證明雙黃連對于新冠病毒有預防的效果,這則謠言正是抓住了當時人們對于病毒的恐慌心理。
網絡謠言在敘事結構上多采取程式化的結構方式,標題必須駭人聽聞,內容必須由當事人進行描述,專家進行權威解讀。講故事也成為了謠言傳播的一個主要形式,例如在騰訊2017年關于食品安全謠言方面的第一條是《xx店承認:在中國所售糕點含致癌橡膠底原料》,用講故事的形式將謠言傳播出去,既有故事情結又有戲劇沖突。隨著媒體傳播的多樣性,網絡媒體下常常有人會說“有圖有真相”,但在高科技手段下,有的圖片或視頻傳播者只是截取了其中想要讓受眾了解的一部分來進行傳播從而達到傳播謠言的目的。例如在近期的新冠病毒防控期間有人將微信聊天進行截圖,發布到網上引起網友的瀏覽關注,但后來都一一被官方辟謠。隨著老年人入駐微信等社交平臺,由于對于網絡世界還未深入了解,對于一些醫療、食品安全和聳人聽聞的消息他們常常會不加篩選地分享到微信群聊中以此來彰顯自身的社交存在感。
(四)網絡謠言傳播機制
“后真相”時代帶來的信息“繭房”,讓各個圈層之間的壁壘更加穩固,圈子內部所帶來的情緒化感染遠遠超過了事實真相本身。因此網絡謠言的傳播機制也與傳統媒體謠言截然不同。所有的謠言都會經過傳播-高潮-下降-消失這樣一個傳播過程,但網絡謠言有所不同的是它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快速發酵,如果官方不辟謠就會在到達高點后一直保持,有時官方辟謠后仍會有網友表示是官方在掩蓋事實真相。因為他們只相信他們認為正確的,這也是由于媒體公信力在網絡環境下逐漸下降所導致的。造謠者大多以草根賬號為主,這讓一些剛剛接觸互聯網的老年人誤認為是由官方媒體發出的消息,從而進行大量的轉載和傳播,網絡謠言就是這樣愈演愈烈的。這樣的謠言“搬運工”除了老年群體外,一些中老年女性也成為了主力軍。這類人群的主要特征就是:對于新媒體了解程度不深、對于真相的辨別能力較弱,大多數都是媽媽、婆婆等喜歡看一些養生、社會安全等的相關信息。
網絡謠言傳播機制除了抓住特定人群的心理外,還讓事實讓位于立場。在謠言發生后,官方媒體及時找專家進行辟謠,公眾在辟謠后認識到了其存在的危害性。但過了不久后此類謠言又會以另外一種形式成為新一輪的謠言,再次引發公眾的集體恐慌。這樣謠言的周期性“發作”也就是謠言的逆火效應,“逆火效應”最早是內燃機的專業術語,即引申為“適得其反,事與愿違”。在鄒振東的《弱傳播》一書中這樣寫道:“輿論世界在爭奪關注時強者占優勢,在爭取認同時弱者占優勢,在爭搶表層中‘比表面積大者占優勢。”
二、“后真相”時代網絡辟謠措施與路徑
(一)占據主導地位:及時主動
馬克吐溫曾說過“謠言傳遍了大半個地球,真相還在穿鞋”,在網絡時代常常會遇到這樣的場景,謠言的瀏覽量眾多,但用于澄清的辟謠文章瀏覽量卻遠遠低于謠言傳播量,這就對辟謠產生了一定的難度。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不斷發展,只有在謠言出現時對信息源進行準確的辨別,通過大數據計算的方法來辨認是否具備謠言傳播的特征因素,確定后對其進行鎖定從而降低謠言傳播的范圍和速度。網絡謠言傳播在一些與自身利益相關的核心人群中最先開始爆發,從核心人群傳播到邊緣人群會有一定的時間滯后性。這種滯后性恰好有利于人工智能進行數據抓捕、分析。所以謠言確定后進行關鍵詞的辟謠和阻截,有利于停止謠言擴大傳播。
在許多網絡謠言傳播中,不難發現傳播的是否是事實已經不重要了,關鍵是能否引發網友的熱議和煽動他們的情緒。社群、圈子成為了傳播的基本單元,情感共鳴成為了傳播的基本動力。傳統的媒體依靠事實為傳播的核心力量,網絡媒體依靠的是情感。因此,想要有效避免網絡謠言的發生,及時主動地占據傳播的主導地位成為了一項關鍵因素。
(二)掌握關鍵節點:描摹重點人群
在網絡謠言中,除了要對相關內容進行辟謠和識別外,更為重要的是對相關圈層的人群和他們的心理情緒進行了解掌握,這樣才能對后續的網絡謠言事件進行有效預防和抓捕。首先,部分平臺應該要求用戶實名制進行賬戶注冊并且對其身份進行相應的標注,特別是對于一些具有較大群眾基礎的公眾號進行明確的標注。在一些網絡謠言傳播過程中,很多人無法清晰地辨認出誰是官方媒體,誰是冒充的,很多沒有新聞采編發權的公眾號因為關注人群多發送了一些未經核實的信息造成了公眾的輿論恐慌心理。隨著移動互聯網的發展,看似傳統媒體的“意見領袖”在日漸消逝,但新的互聯網意見領袖在慢慢出現。在發生一些重要事件時,一些明星、微博大V就成為了公眾眼中新的意見領袖。在微博剛剛出現時,姚晨作為當時微博首位關注人數破千萬的“微博女王”擁有著巨大的影響力。這才僅僅是在微博剛剛開始使用時關注的人數,當下的微博中一些明星的關注量甚至超過了五千萬,這就意味著他們發出的一條消息可以被千萬人收到,影響力相較于傳統的“意見領袖”更加重大。
除了對于公眾號、“意見領袖”的實名認證之外,建立相應的社會網格也非常重要。信息的接收者單單憑借內容、身份很難準確地辨別出謠言和真相,所以通過網格化的劃分將一些發布者不明、內容有待檢驗的信息進行篩選、阻截,有利于降低謠言傳播的速度和范圍。所以,對于網絡謠言要緊緊掌握相關人群信息和屬性、把握關鍵的傳播點才能有效減少網絡謠言的傳播。
(三)提高媒介素養:加強科普教育
通過許多公眾事件不難發現,事件的當時人并非有意傳播謠言而是缺少一定的媒介素養。懷揣著看熱鬧不嫌事大或是大家一起來做吃瓜群眾的情緒來進行謠言的傳播,由于看熱鬧導致的謠言在災難事件中屢屢發生。所以在信息發達、媒體傳播速度加快的當代,對公眾進行媒介素養教育迫在眉睫。早在20世紀30年代著名的新聞記者戈公振就說過:“若使現在每一個國民,都能知道報紙從什么需要而來,報紙有何種力量,報紙受何種影響。那么,他才可以對報紙有理解和正確的態度……所以我敢說,新聞學無條件是一切國民的必修課。”(《新聞學》,1940年)由于普通公民很少有機會接觸媒體,所以媒體被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成了某種供人敬仰、膜拜的對象。早在19世紀的歐洲就經歷過這樣的一個階段,民眾盲目地認為報紙上刊登的都是正確的。因此,“媒介素養”是指讓民眾了解媒介究竟是如何進行傳播的以及有效地辨別虛假信息。
“后真相”時代最為突出的表現就是能夠讓受眾看到新聞后情緒先于理性思考,不加思索地進行言論評判。情感能量的聚集與動員一般有三種敘事方式來進行:仇恨敘事、悲情敘事和惡搞敘事。②通過對受眾的情緒調動從而讓受眾暫時忘記了判斷、確定、核查事實。所以有效降低謠言的傳播除了從信息源頭進行攔截,對于在傳播過程中的受眾進行媒介素養的教育與提升也是相當必要的。
三、“后真相”時代輿論話語場角力
(一)公眾情緒表達與官方辟謠
互聯網時代對于謠言的判斷不僅限于傳統媒體下的真相與謊言之間的角力,更多的其實是傳統媒體公信力和受眾經驗自我判斷之間的角力。在近期新冠病毒防控期間就發生了多起微信群聊被截圖或是用武漢當地人視角來進行拍攝的視頻來宣傳疫情的嚴重和防控措施不到位的謠言信息。其中,與民眾利益緊密相連的就是在疫情期間有謠言稱武漢重災區生活物資嚴重缺乏,醫院口罩、防護服等匱乏,后來經多家主流媒體證實雖然存量不足但仍能夠維持并且有全國四面八方的物資正在緊急調運,并不會影響武漢市民的正常生活和醫護人員的人身安全。除此之外,在政府出臺一省幫一市的政策后,有人稱會將大量的病人緊急空投至相應的幫扶省份,這就引起了當地民眾的恐慌,后經報道只是緊急抽調醫護人員去當地參與醫療保障工作。在武漢方艙醫院剛剛接收病人后,就有人在網上說醫療條件、設施差,醫護人員不夠,官方在當天的記者發布會上就進行了辟謠,方艙醫院中收治的都是一些輕微患病人群,準備時間不夠充分但還是能保證病人基本的生活保障并且患者的醫藥費、伙食費全是由政府出資,不需要花費一分錢。
互聯網給予了普通民眾更多的話語權和言論自由權,也讓信息可以傳播得更快更廣。但正是因為紛繁復雜的信息接踵而至,讓普通的民眾不能夠及時識別出什么是謠言,什么是事實真相,并且由于政府在某些行為上可能采取的行動不及時讓公眾失去了對它的信任。所以官方輿論場和民間輿論場逐漸產生了壁壘和隔閡,在“有圖有真相”的時代里學會了“看圖說話”。
(二)時效性與事實核查競爭
新聞的事實核查是在20世紀首先興起的一種新聞編輯室內部的核查手段,針對新聞來源、新聞背景、新聞引語等新聞內容進行核對、核實。最早由美國的《紐約客》《時代周刊》等雜志最先開始設置所謂的“事實核查員”崗位。其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為了尊崇新聞專業主義,保持新聞的客觀性和真實性。近些年,尤其是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英國“脫歐”等“黑天鵝”事件頻發后,新聞事實核查逐漸跳脫出新聞編輯室內部的新聞生產流程,成為了一種相對獨立的新聞樣式,諸如美國的Polity Fact、Storyful等事實核查機構應運而生,并且還清晰地分為了政治新聞核查和社交新聞核查等多個領域。
中國還未單獨成立一個專門的機構進行事實核查,但也有逐漸發展的趨勢。“后真相”時代的移動互聯網新聞由于太過于追求時效性從而破壞了新聞原本的一些原則要求,這就造成了網絡謠言的廣泛傳播。例如在重慶公交墜江事件中從最開始的女司機逆行導致事故的謠言,到有一名學生成功跳窗逃生,再到司機徹夜K歌導致睡著、女乘客生前吵架視頻網上流傳……多條不實傳言在網絡流傳。一些主流媒體也因為沒有準確地進行事實核查而導致事件中原本的受害者變為了謠言的加害者。所以時效性與真實性競爭從某種方面來說也是時效性與事實核查之間的競爭,如何正確把握兩者之間的平衡對當下的新聞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結語
互聯網時代信息更加多元化、傳播速度更加及時、獲取信息更加便捷,但在享受其帶來便利的同時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由此帶來的弊端。“后真相時代”所帶來的情緒在先的行為是一種“非理性”的行為,外加網絡謠言之所以能夠在短時間內傳播迅速并且范圍廣是利用了謠言的標題修辭夸張吸引人、選題大多迎合受眾心理并且掌握了謠言傳播的機制進行了所謂的有效傳播。因此,要想阻止網絡謠言傳播除了要對信息源進行抓取外,還需要對謠言的傳播內容進行抓取、辨別,這樣才有利于后面的謠言阻截工作。在不同的輿論話語場中對同一信息有不同的理解方式,所以也需要積極提高新聞工作者和受眾的媒介素養,還需要有效有序進行事實核查工作。
注釋:
①李彪,喻國明.“后真相”時代網絡謠言的話語空間與傳播場域研究——基于微信朋友圈4160條謠言的分析[J].新聞大學,2018,(02):103-112+121+153.
②郭小安.公共輿論中的情緒、偏見及“聚合的奇跡”——從“后真相”概念說起[J].國際新聞界,2019,41(01):115-132.
參考文獻:
[1]郭小安,董天策.謠言、傳播媒介與集體行動——對三起恐慌性謠言的案例分析[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3,35(09):58-62.
[2]郭小安,張榮.謠言心理的三個研究維度:理論整合與現實關照[J].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14,16(03):41-50.
[3]雷霞.“信息拼圖”在謠言傳播中的作用研究[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4,21(07):65-79+127.
[4]劉栢慧.從江歌案透視后真相時代專業媒體輿論引導失范行為——以“局面”為例[J].新媒體研究,2019,5(02):54-55.
[5]李彪,喻國明.“后真相”時代網絡謠言的話語空間與傳播場域研究——基于微信朋友圈4160條謠言的分析[J].新聞大學,2018,(02):103-112+121+153.
[6]徐天博.“后真相”時代的真相建構——基于行動者網絡理論的分析[J].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43(02):135-140.
[7]雷海平.微博話語場中的意見領袖[J].現代交際,2011,(08):5-7.
[8]武澤新.微博“即逝意見領袖”探析[J].新聞世界,2013,(07):194-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