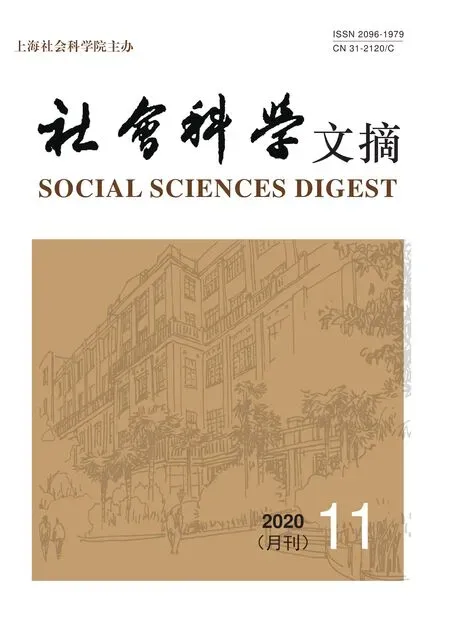“以中國為方法”辨析
——兼與楊光斌教授商榷
楊光斌教授的《以中國為方法的政治學》(以下簡稱“《以》文”)一文的目的是回答“中國性”的問題。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作者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被引進中國學術界的西方民主理論、治理理論、合法性理論進行了反思。作者反思的結果是:西方以“理性人”假設為前提的西方政治學說和“個體理性”不符合中國這樣的文明體國家,因此,構建“中國性”必須以中國歷史為基礎。客觀地說,筆者非常贊同作者“以中國歷史為基礎”來構建中國歷史政治學。但是,《以》文試圖用“治體論”來替代西方政治學說中的“政體論”,“以本土化中國為中心”構建中國歷史政治學的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并借助溝口雄三以“中國基體論”為基礎的“把中國作為方法”的觀點,提出了“以中國為方法”的歷史政治學路徑。“以中國為方法”源自日本史學家、中國學專家溝口雄三《作為方法的中國》一書。比較《以》文與《作為方法的中國》之后,會發覺其內涵是完全不一樣的。也正是筆者與楊光斌教授對溝口雄三“以中國為方法”含義的不同理解,促使筆者就這一問題向楊光斌教授請教。
關于《以》文所涉及的主要概念問題
《以》文梳理西方政治學理論的同時,也在批駁西方政治學理論,并在剖析概念的基礎上來構建“以中國為方法”的政治學。但是,文章對有些概念的理解似乎是模糊的,且有的還存在著自相矛盾之處。
第一,《以》文說:“人民主權是實質民主。”眾所周知,第一個闡述人民主權思想的是法國思想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他的人民主權有一個前提,就是“公意始終是公正的,永遠以公共的福祉為宗旨”。這實際上是一個理論上的理想假定。另外,人民主權思想強調,一是集體行使,即直接民主;二是強迫服從,也就是以“公意”否定個體及少數人的意志和利益訴求。僅從這兩點來看,人民主權并不是實質民主。盡管迄今為止,對于人民主權思想,無論西方還是中國,都沒有任何人提出質疑,但人民主權思想的前提即“公意永遠是正確的”“公意永遠追求公眾利益”,在思想界始終是存疑的。
第二,《以》文批駁了西方“選舉民主”的失效,但似乎沒有闡明社會主義民主的內涵,卻簡單地把社會主義民主歸結于孔孟的民本思想,或者說中國的民主是“以治理為主要訴求的民主觀”。孔孟的民本思想目的是君權的穩定,“民本”只是工具,鞏固君權和君臣秩序才是目的。至于如何理解“治理為訴求的民主觀”,則需要弄明白治理的內涵究竟是什么。廣義來說,治理應該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內容,而以互動為特征的治理,無論是在寡頭政治、集權政治,還是其他類型的政治之下,都會或多或少地存在。這并不體現政治的民主與否,只有在政治上的治理即政治權利“分配”的互動中才會體現政治民主。因此,不能簡單地說中國是“以治理為訴求的民主觀”,否則會在注重增加社會經濟福利水平和文化權利的同時,忽視民眾的政治權利。
第三,《以》文借用了王紹光教授的概念即“區別于西方代議制民主的中國代表型民主”來闡述中國民主是一種實質性民主,并且用“政府的代表性、政策所反映人民的訴求、政治制度能夠產生諸如社會正義、良治、福利、‘民享’等實質效果”來證明中國民主是實質民主。筆者認為,代議制民主和代表型民主雖然有較大差別,但也有不少相同的地方,二者都有選舉的成分。更值得注意的是,《以》文和王紹光教授在批評代議制的時候,似乎忽視了中國學術界乃至官方早就承認并接受了一個事實,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也是一種代議制的形式”。關于《以》文用來衡量“中國實質性民主”的一些標準同樣存在著問題:政策反映人民的訴求和政治制度產生社會正義、良治、福利,就一定是民主政治嗎?開明專制政治下也有“盛世”,“盛世”在一定程度上也會體現為社會正義、良治、福祉水平的提高。古今中外的歷史都可以找到這樣的證據。因此,我們有必要區別一下“政治民主”與“政府民主”、“協商民主”與“協商治理”這兩組概念。政府的民主不完全等于政治民主,民主治理也不完全等于民主政治。協商民主主要是指政治權利范疇的民主,它指向的是執政集團與參政精英之間的協商;而協商治理則主要是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范疇的民主,它指向的是政府、社會成員、市場主體等之間的互動。《以》文在概念上的模糊表達導致了論證邏輯上的矛盾性:一方面把協商治理等同于協商民主,即把社會經濟權利上的協商等同于政治權利上的協商;另一方面在社會危機的認識上,卻又把轉型危機視為經濟社會領域內的危機,是國家治理和社會轉型的普遍現象,而不是權力上的合法性危機。更進一步的是,一方面,《以》文用社會經濟建設所取得的成就來證明政治體制的“固有”優勢(實際上就是合法性資源);另一方面卻又否認社會經濟上出現的問題即“轉型危機”是政治合法性危機,而只是國家治理和社會轉型的普遍現象。如果是社會轉型中的普遍現象,那么如何理解一些國家尤其是中國沒有出現“轉型危機”,而俄羅斯和東歐一些國家卻出現了嚴重的“轉型危機”呢?那是否可以認為中國的社會轉型不是“普遍現象”?或者說,中國非常有幸地避免了社會轉型的“普遍現象”?要知道,中國的社會轉型是最具有普遍性的:從落后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
第四,民主集中制政體與代議制政體在政治學理論上究竟是什么關系?《以》文似乎認為民主集中制政體一直就是低于代議制政體。筆者不知道《以》文這種認識的依據是什么。聯系楊光斌教授前幾年發表的《論作為“中國模式”的民主集中制政體》一文,不難看出作者似乎認為民主集中制政體理論在中國迄今為止尚未確立起來,因此他在文章的結語呼吁“確立民主集中制的政體理論地位”。更重要的是,作者梳理了民主集中制在中國的發展進程之后,認為“民主集中制不僅體現在政治制度和組織制度上,更是統率政治過程的一個大原則”,那么又為什么會覺得中國民主集中制的政體理論尚未確立?筆者認為這是對中國民主集中制政體欠缺客觀和科學的認識。
中國模式體現中國的國家性嗎?
《以》文為了構建“扎根中國大地的政治學”,提出了中國“國家性”的問題。為此,《以》文借用了溝口雄三“基體論”這一概念而提出了“中華文明基體論”概念。筆者對溝口“歷史基體”的理解,簡而言之就是所謂的歷史傳統因素,以及由此而導致歷史發展進程的路徑依賴。
溝口指出,“一個全面否定或者全面肯定自己的歷史、無法將自身相對化的人,也不可能客觀地、相對地來看待他者”。所謂“相對化”就是反思性的同義詞,溝口關于日本中國學研究的自我相對化就在于,他不同意日本主流學界基于“先進—落后”的模式對中國產生的看法,而認為“中國的近代既沒有超越歐洲,也沒有落后于歐洲。中國的近代從一開始走的就是一條和歐洲、日本不同的獨自的歷史道路,一直到今天”。因此,即便是與“西方”對立的“東方”,在擺脫了“先進—落后”模式的認識以后,也就不再是“古代的東方”,而是一個新的東方。溝口進一步進行“自我相對化”的反思,即對當今世界無節制的資本主義發展所具有的反道德性等問題進行正確的自我檢討:切不可妄自尊大。這才是溝口“歷史基體論”的用意所在。
然而,《以》文借用溝口的“基體論”走向的是相反的方向,不是“自我相對化”,而是強化中國歷史傳統因素,甚至把歷史上的“大一統”體制、郡縣制、科舉考試等都囊括在“中華文明基體”之中,認為這些是構成中華文明共同體的關鍵要素。這不能不讓人覺得似乎一切存在的便是合理的。《以》文把中國共產黨依然定義為“建國黨”,這本身就犯了一個國際法的常識性錯誤;而把中國共產黨的成功和蘇聯共產黨的失敗歸結于“歷史文明基因的差別”,這顯然是陷入了“歷史決定論”之中,更忽視了中國共產黨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從而也會把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視為是一勞永逸的。
從“中華文明基體論”到當代中國國家性的討論,《以》文認為,當代中國的國家性就是由“文教傳統”所延續下來的中華文明基因共同體,且以中國模式體現出來;而為了賦予中國模式以政治意義,“對中國模式的一種合理化解釋,就是‘民主集中制政體’”。何謂國家性?筆者認為,所謂國家性應該是指思想,它是沉淀在國家的文化血液之中,并內化為一個國家精神品質的思想因素,國家性標識著一個國家的特殊品格。國家性可以引發出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一個民族的行為方式,但發展道路和行為方式絕對不能代表或體現國家性。因此,中國模式即便存在,也只是一種具體的發展方式,這種發展方式并非固定的,而是可以隨著實踐、環境、形勢的不同進行調整的,因而它并非溶于思想血液之中的國家品性。《以》文把民主集中制作為中國模式的核心內容,也作為當代中國國家性的體現,可民主集中制是列寧提出來的,最初在蘇聯政治體制上運用,在一定時期內是非常成功的。如果按照《以》文的邏輯,那么民主集中制也應該是蘇聯的國家性。兩個國家擁有同樣的國家性核心要素,這聽起來就會讓人覺得不可思議。
“以中國為方法”是否可以成為一種“世界性標尺”?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以》文“以中國為方法”的內容,“不但是要‘以中國為中心’,立足中國、回答中國問題、提出中國性命題;而且意味著以中國為中心所產生的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知識能夠成為一種世界性的尺度”。“以中國為方法”最終能否把“一種世界性的制度”作為最終的目的?為了回答這個問題,筆者覺得非常有必要比較《以》文與溝口雄三的著作在“以中國為方法”上的重大區別。
溝口的“以中國為方法”,不是一種排斥歐洲的“世界”,也不是建構“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標尺”,而是承認歐洲的“世界”作為世界一元的前提下,也承認中國作為一部分“世界”的重要價值。換言之,“以中國為方法”只是觀察世界、考察歷史的方法之一,并不是否定和排斥其他的方法。因此,溝口所持的是多元主義的世界歷史觀。
我們再來看《以》文的觀點,“以中國為中心”是《以》文的邏輯起點,“以中國為尺度”才是其邏輯歸屬。因此,盡管《以》文“以中國為中心”同溝口的觀點一樣,以去“西方中心主義”為前提,轉向歷史制度主義;但是,《以》文單純從中國的歷史傳統來認識世界、研究中國,也就是所謂的“歷史政治學”,而不是如溝口那樣把中國歷史傳統作為認識世界、研究中國的方法和視角之一。建立一種“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性標尺”,其前提是去“西方中心主義”,但把“以中國為中心”作為一種“世界標尺”,就意味著在去“西方中心主義”的同時,構建一個“中國中心主義”,也就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中國歷史政治學的使命是什么?
使悠久的歷史因素成為推進當今中國社會的動力,這就是歷史政治學的使命。筆者非常贊同歷史政治學最重要的任務是“重建政治價值體系”。但要說構建中國政治學理論的知識體系,可能是多余的。因為政治價值不可以在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不同政黨之間分享,但知識體系卻是可以共享的。
嚴格來說,歷史政治學不是一門學科,而是一種研究政治學科的歷史關懷;并不是要把政治學“帶回歷史”,而是使歷史于現實政治實踐中“在場”。“帶回歷史”會讓人覺得歷史是可以倒回的,而讓歷史“在”現實政治實踐中的“場”,恰恰就是歷史的積極因素作為“基體”而對現實政治實踐產生影響。因而,政治科學的研究就必然要從歷史中尋找經驗和教訓。
《以》文所主張的從歷史中發現中國,這并不是目的,目的是構建中國特色的政治學理論學科。這也是當今中國學術界責無旁貸的學術使命。我們絕對不能否認來自外部的哲學社會科學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所作出的重要貢獻,但中國這樣的大國不能沒有自己原創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不能沒有原創的哲學社會科學思想體系。然而,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具體而言是構建中國特色的政治學理論,不能僅僅從中國的歷史傳統中去尋找智慧,還應該橫向學習他國的智慧。在這一點上,盡管楊光斌與姚中秋都倡導所謂的歷史政治學,但二人的觀點和價值立場是有區別的。從《以》文來看,楊光斌強調的是去“西方中心主義”,構建中國的“世界標尺”,落入了“中國中心主義”的陷阱之中;而姚中秋主張“不把某個國家、文明預設為標準,而是把所有國家、文明平等地放在面前進行比較,分析其異同,比較其制度之利弊得失,比較政治學才有可能生產政治新知識”。可以看出,姚中秋的觀點更接近溝口雄三“以中國為方法”的本意。
結束語
政治學是一門政治科學,那么作為一門軟科學,概念的使用應該是準確的,表達的意義也該是明確且精準的。但是,《以》文在使用所涉及的概念的時候是混亂的,文中概念的內涵也有不一致之處。概念內涵的模糊性必然導致邏輯判斷上的問題。《以》文認為“歷史政治學”可以避免歷史碎片化,但從《以》文的概念使用和論證邏輯來看,文章本身就在“碎片化”歷史,即以自己的方式解讀歷史現象,使之符合自己的論證需要。
溝口的“以中國為方法”是倡導研究中國要走出“西方中心主義”,不能以歐洲作為世界的標準來衡量中國。但是,溝口不是為了否定歐洲的“世界”,而是為中國研究的路徑提供更多一種的選擇,倡導世界的多樣性。然而,《以》文在去“西方中心主義”的同時,卻陷入“中國中心主義”的陷阱之中,把中國歷史傳統作為唯一的要素來闡釋當代中國的政治實踐,以作者所理解的“中華文明基體”來構建中國政治學理論知識體系的唯一骨架。這種想法可嘉,但實踐上難以回避既有的知識(來自國外的政治學理論知識,這已經成為中國政治學知識體系的重要存量之一)。再說,中國的政治實踐和相應的學術研究,早就形成了中國獨特的政治學知識體系,但因種種原因學術界尚未構建起中國特色的政治學理論。不過,從實際情況來看,中國政治學的關鍵使命,不是構筑中國政治學理論知識體系來批駁外部的知識,最迫切的是要構筑中國的政治價值體系來整合中國內部。知識無論來自何處,都可以進行改造和利用;政治價值是一個國家所獨有的,只有政治價值才能夠在多樣性的文化要素系統中發揮整合社會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