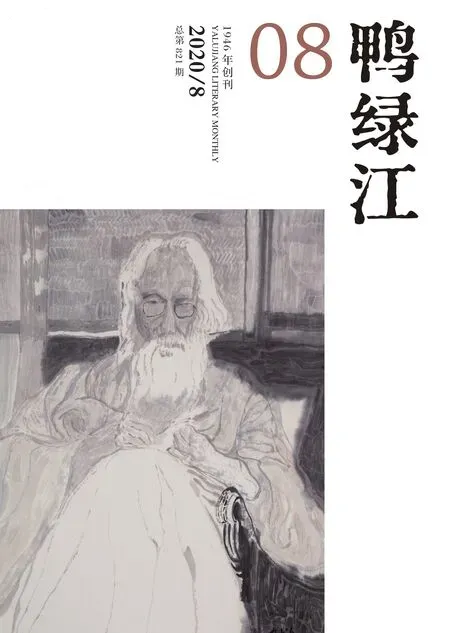小說的裝置(對(duì)談)
——從梁寶星的《海邊別墅》說起
陳培浩 王威廉 梁寶星
1
陳培浩:本期我們一起從梁寶星的《海邊別墅》說起。應(yīng)該說,這篇小說從題材到寫法都和我們這個(gè)欄目很配。寶星是近年頗受關(guān)注的“90后”作家,《海邊別墅》寫得很有特點(diǎn)和想象力,寶星先請(qǐng)你談?wù)勥@篇小說寫作的緣起和背景吧。
梁寶星:去年十二月,我一個(gè)人沿著海邊旅行。從北海到海口去的時(shí)候,我在海上漂泊了一個(gè)晚上,船在海口靠岸的時(shí)候是早上六點(diǎn)鐘,我暈乎乎的,沒有馬上打車,而是沿著西海邊的公路走了好遠(yuǎn)的路,走到黃金海岸才停下來。那時(shí)天還早,我在海邊的鐵椅上坐下,太陽尚未出來,海特別藍(lán),身后就是一排無人居住的別墅。我喜歡海邊城市,我當(dāng)時(shí)就冒出了一個(gè)念頭,我身上只有一個(gè)背包,尚未訂酒店,倒是可以在晚上無人察覺的時(shí)候爬進(jìn)這些別墅過夜。最后我當(dāng)然沒有那樣做,我在附近找了一家酒店,接下來的兩天時(shí)間就在四周觀察這些無人居住的別墅。我原本的構(gòu)思是:一對(duì)情侶在旅途中看見一所無人居住的別墅,他們搬進(jìn)去在別墅里理所當(dāng)然地度日,后來又搬進(jìn)來一對(duì)情侶,兩對(duì)情侶為了生活空間明爭暗斗。后來覺得這個(gè)故事過于簡單瑣碎,我就把后面來的那對(duì)情侶變成了鏡子里的人。而“鏡像”是我一直想寫的題材,兩個(gè)題材相遇,就構(gòu)成了這部小說。
陳培浩:《海邊別墅》里包含著一個(gè)關(guān)鍵詞,叫“鏡像對(duì)稱”。它讓我想起基耶斯洛夫斯基的電影《薇羅妮卡的雙重生活》,香港譯作《雙生花》。電影里有兩個(gè)叫薇羅妮卡的女孩子,一個(gè)在波蘭,一個(gè)在法國。她們名字相同,容貌相同,性格相同,會(huì)唱歌的才能也相同。波蘭薇羅妮卡有疾,卻仍參加歌唱團(tuán),并在一次排演時(shí)發(fā)病身亡。那一刻,法國的薇羅尼卡正在和男友做愛,她莫名地感到一陣難過。基耶斯洛夫斯基讓兩個(gè)薇羅妮卡有著神秘的心靈感應(yīng)。兩個(gè)薇羅妮卡僅有一次現(xiàn)實(shí)的相遇:有一次,波蘭的薇羅妮卡在一個(gè)廣場(chǎng),看到了正在忙著上車的法國的薇羅妮卡。她看著那個(gè)和自己一模一樣的女子,十分震驚。幾年以后,法國的薇羅妮卡和作家在旅館里,作家翻出薇羅妮卡當(dāng)年拍下的相片,相片上正是穿著一身黑衣的波蘭的薇羅妮卡。法國的薇羅妮卡看著相片,突然哭了起來,因?yàn)樗緵]有這件黑色的衣服,她感到,她一直感覺到的自己擁有的兩個(gè)生命竟如此真實(shí)。我想寶星你一定看過《薇羅妮卡的雙重生活》,我想它講述的是生命一種內(nèi)在的神秘,很多人在出發(fā)時(shí)可能是一樣的種子,后來卻擁有了不一樣的命運(yùn)。波蘭薇羅妮卡和法國薇羅妮卡,基耶斯洛夫斯基讓她們作為如此相同卻又如此不同的雙生花,意在發(fā)出這樣的追問:我是誰?我是絕對(duì)唯一的嗎?假如在我之外還有另一個(gè)我,那我的意義何在?等等。當(dāng)然,《海邊別墅》跟《薇羅妮卡的雙重生活》有相似之處,但又很不一樣。《海邊別墅》書寫的是一種鏡像對(duì)稱的存在。你自己怎么理解《海邊別墅》和《薇羅妮卡的雙重生活》的聯(lián)系及區(qū)別?
梁寶星:其實(shí)我沒有看過《薇羅妮卡的雙重生活》,不過從您的話中我基本理解了那是一部什么樣的電影。《海邊別墅》跟《薇諾尼卡的雙重生活》的相似之處或許就是對(duì)自我存在的探討:我是誰?不同之處在于《薇羅妮卡的雙重生活》中兩個(gè)薇羅妮卡生活在同一個(gè)世界,而我在《海邊別墅》的構(gòu)思當(dāng)中,鏡里鏡外是兩個(gè)世界,跟平行宇宙有相似之處,只是平行宇宙中的那個(gè)“我”可能是完完全全的一個(gè)陌生人,或者是完完全全的另一個(gè)“我”,而鏡中的“我”是“我”的一部分。善的人在鏡中看見自己惡的一面,惡的人在鏡中看見自己善的一面。我們真正了解自身嗎?這是我在《海邊別墅》中想去探討的,“鏡”是為我提供對(duì)照物的工具。我們都渴望跟善者生活在一起,但在現(xiàn)實(shí)世界中,這種想法往往難以實(shí)現(xiàn),我們?cè)讷@得他人的善的時(shí)候,還得承受他人的惡。
陳培浩:威廉,你對(duì)《海邊別墅》有什么觀察和解讀?
王威廉:寶星的《海邊別墅》挺讓我驚艷的,這部小說彌漫著哥特式的恐怖緊張氣息,讓人能夠沉浸其中,跟人物一起去感受那個(gè)詭異的世界。作為小說,很多細(xì)節(jié)特別好,一讀就知道寶星是認(rèn)真打磨過的,這些細(xì)節(jié)猶如鉚釘,把這個(gè)有些玄幻的故事跟現(xiàn)實(shí)背景緊密結(jié)合在一起。培浩兄想起的是基耶斯洛夫斯基的電影《薇羅妮卡的雙重生活》,我想起的是一個(gè)短篇小說——麥克尤恩的《立體幾何》,其中的主人公按照一種方式來折疊人體,讓自己成功地從這個(gè)世界上消失不見。因此,我也不免猜測(cè),寶星會(huì)不會(huì)讓主人公也消失在另外一個(gè)鏡像世界當(dāng)中。但小說的結(jié)局,最大的悲劇出現(xiàn)了,那就是平行的鏡像世界的消亡,被粗暴的司徒砸碎了另外一個(gè)空間的門徑。那么,讀者的閱讀期待自然就掉到了地面上,很痛,但讓人更加清醒。由此來說,我覺得寶星可能是一個(gè)悲觀主義者,他期待另一個(gè)不同的鏡像世界,但又知道那只是一種鏡像,是注定要破碎的。鏡子,除了映照之外,似乎就是為了破碎而誕生的。
陳培浩:我想接著上面提到的“鏡像對(duì)稱”這個(gè)概念來談《海邊別墅》,這篇小說非常特別的想象在于,它想象一對(duì)青年男女闖入了一座空置的海邊別墅,后來又意外地發(fā)現(xiàn)了存在著另一座完全相同的別墅。這兩座別墅的關(guān)系不是重疊,不是回聲,不是影子,它們是一種鏡像式的對(duì)稱。“鏡像對(duì)稱”的意思是我們?cè)阽R子里看到的自己左臉在右邊,右臉在左邊,借由鏡子看到的自我并不完全等同于別人眼中看到的自我,但它被主體認(rèn)同為自我。《海邊別墅》因此就包含了一個(gè)青年主體探索自我的問題,在它的視界中,主體和自我不是凝固的,而是游移的。因此,這座別墅里住著一對(duì)女受男施的伴侶,另一座別墅里則住著一對(duì)男受女施的搭檔。他們之間就構(gòu)成了某種“鏡像對(duì)稱”,或者說互為倒影。這意味著主體長成什么樣子,并非必然,同一種子可能孕育出相反的面相。同時(shí),《海邊別墅》中還存在著另一種對(duì)照關(guān)系,即顯與隱的關(guān)系,闖進(jìn)別墅者是顯,而離開別墅者則是隱。如果我們將別墅視為當(dāng)下的自我,那么隱者則是自我的過去,現(xiàn)在是自我的此在,這在另一個(gè)層面上暗示著自我的流動(dòng)性。
王威廉:《海邊別墅》確實(shí)涉及主體的思辨問題。拉康認(rèn)為,意識(shí)的確立發(fā)生在嬰兒學(xué)會(huì)語言之前的一個(gè)神秘瞬間,即“鏡像階段”。兒童的自我和其完整的自我意識(shí)由此開始出現(xiàn)。當(dāng)一個(gè)6-18個(gè)月的寶寶在鏡中認(rèn)出自己的影像時(shí),他尚不能控制自己的身體動(dòng)作,但他卻能認(rèn)出鏡中的影像就是自己,也就是說,他通過鏡像意識(shí)到自己身體的完整性。因此,當(dāng)在小說當(dāng)中設(shè)置一個(gè)鏡像世界的時(shí)候,無疑蘊(yùn)含著作者對(duì)于主體完整性的一種沖動(dòng)。這種沖動(dòng)甚至表現(xiàn)在寶星作為男性而使用女性第一人稱的敘事上邊,這敘事本身便蘊(yùn)含著對(duì)人類無性別主體完整性的探索欲望。拉康將一切混淆了現(xiàn)實(shí)與想象的情景都稱為鏡像體驗(yàn),無疑,寶星的《海邊別墅》是一篇聚焦于鏡像體驗(yàn)的小說,這讓我耳目一新,還比較少看到這方面的小說,特別希望年輕作家能有這樣的探索精神。讓我覺得稍有遺憾的地方倒不是結(jié)尾的鏡像世界的破滅,而是對(duì)于主體完整性的沖動(dòng)最終讓位于對(duì)他者的欲望。“我”與鏡像世界中那個(gè)善良的“司徒”在一起才體驗(yàn)到了真正的激情與愛,但實(shí)際上,鏡像世界最神秘也最恐怖的地方,恰恰不在于另一個(gè)司徒,而在于另一個(gè)“我”。
陳培浩:寶星,《海邊別墅》還有另一個(gè)感興趣的地方,你作為一個(gè)男性作者,從女性視角來敘述這個(gè)故事,一開始令我頗有“出戲”之感。因?yàn)榧偃鐝摹艾F(xiàn)實(shí)主義”的評(píng)價(jià)看,你敘述的某些女性感受令我感覺不是很女性。比如讀到你這樣的描寫:“我只穿著白色背心,胸罩忘記戴了,黑色荷葉裙下面是一條四角打底褲,腳上是一雙人字拖,盡管穿得這樣少,胸前背后還是冒出了汗。”“目送司徒去釣魚以后,我走進(jìn)浴室,想洗個(gè)澡來緩解疲憊。解開背心,脫下內(nèi)褲,面對(duì)噴灑而下的熱水,我一只手抓住頭發(fā),一只手在乳峰間搓洗,浴室里蒸汽騰騰,燈光和鏡子變得模糊。”這些描寫讓我忍不住笑出聲來,因?yàn)樗凹佟绷耍鳛榕砸暯堑臄⑹拢挠谜Z卻充滿了男性的“欲望凝視”感。但是,我還是替你找到了一個(gè)解釋,這不是一篇寫實(shí)小說,而是一篇實(shí)驗(yàn)小說,而且它的關(guān)鍵詞就是“鏡像對(duì)稱”,男性和女性也構(gòu)成了某種性別上的鏡像對(duì)稱,小說中的那個(gè)女性敘事人,她是一名作家,與音樂人男友幾無情感交流,某種意義上她也在浸入男性體驗(yàn)而習(xí)得一個(gè)男性的自我。因此用這種男性語言來書寫她的自我觀看,似乎也有某些合理性。不知這是有意為之,還是誤打誤撞?
梁寶星:這是我第二部用女性視角來敘事的小說,也算是在嘗試女性視角敘事。您所說的在讀小說的時(shí)候感覺敘述語言很不女性,我是可以接受的,像您所說的敘事上的細(xì)節(jié)問題我在這部小說上確實(shí)沒有做好。我是那種內(nèi)心活動(dòng)非常豐富的人,乘車路過一個(gè)地方或者在咖啡店往窗外張望的時(shí)候常常揣測(cè)從眼前經(jīng)過的人心里面到底在想些什么。還有就是,很多不認(rèn)識(shí)我的人,看到梁寶星這個(gè)名字的時(shí)候竟然會(huì)覺得我是個(gè)女孩。第一次以女性視角來敘事的時(shí)候我覺得挺好玩,我想讓別人看見我的文字就覺得我是個(gè)女孩。如今看來這種做法顯得幼稚,而且是不成功的。我覺得無論梅蘭芳的身段多么柔軟,聲音多么細(xì)膩,他也會(huì)暴露出他的男性特征,在男性作者的文本敘事當(dāng)中,想要達(dá)到這種女性視角的真實(shí),毫無疑問是艱難的。《海邊別墅》沒有把男性視角隱藏得足夠好,才顯得滑稽。其實(shí)使用女性視角來敘事是我有意為之的,也跟小說中的“鏡像”有關(guān),男性跟女性在“鏡像世界”中可能也是一種對(duì)照,現(xiàn)實(shí)當(dāng)中的男性在“鏡像世界”里面是女性,男和女不過是兩個(gè)世界的兩個(gè)概念,僅此而已。于是,我想,既然要寫“鏡像”和“自我”這么個(gè)小說,干脆做得更徹底一些,把敘事視角也換掉。
2
陳培浩:寶星,近年在廣東的90后青年作家中,你是受到較多關(guān)注的一位。獲得了“有為杯”長篇小說獎(jiǎng),得到廣東省作協(xié)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項(xiàng)目的扶持,等等。談?wù)勀銓懽鞯膩砺泛脝幔?/p>
梁寶星:我在90后群體當(dāng)中算是發(fā)表文章比較晚的一個(gè),2018年才開始發(fā)表第一篇小說,我覺得是我運(yùn)氣好,認(rèn)識(shí)了陳崇正、鐘道宇、葉由疆、范俊呈等良師益友,他們給了我很多的幫助,我才真正走上了文學(xué)的道路。這兩年在不斷碰壁中掙扎度過,學(xué)到了不少東西。這兩年對(duì)我而言是改變特別大的兩年。首先是寫作題材的改變,受到生活的沖擊,“城市”成為我的書寫對(duì)象。其次是語言的改變,我在寫作和閱讀上面對(duì)文本的語言特別挑剔,所以在敘述語言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后面的寫作才顯得自由輕松了一些。寫作生涯剛開始,真正的考驗(yàn)還在后面。
陳培浩:哪些作家構(gòu)成了你的寫作資源呢?
梁寶星:海明威、村上春樹、馮內(nèi)古特、川端康成、加繆、余華、薩特、菲利普·迪昂。
陳培浩:目前來說,你追求一種什么樣的寫作?或者,進(jìn)一步說,你有所謂的寫作觀嗎?
梁寶星:我沒有特別成熟的寫作觀,在我看來,我只是在寫自己喜歡的小說,至少是現(xiàn)階段自己喜歡的小說。就文本而言,我想達(dá)到的是一種既簡單又復(fù)雜的境界,用最簡單的文字去寫最復(fù)雜的故事。所以我需要時(shí)間把文字打磨好,不干巴巴的、不重復(fù),簡單也可以詩性,簡單也可以細(xì)膩。世上最復(fù)雜的,我想就是人心了,用最簡單的文字剖析最復(fù)雜的人心,想必是一件極有趣的事情。我不想把寫作生活弄得太復(fù)雜,時(shí)間充裕的時(shí)候,思維活躍的時(shí)候就多寫一些,實(shí)在寫不出來就緩一緩。寫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已,虛構(gòu)的世界應(yīng)該是給我自由和快樂的空間,假如寫作不能讓我達(dá)到這兩種狀態(tài),我想對(duì)我而言寫作的意義不大。
陳培浩:我們這個(gè)欄目叫作“新城市·新青年”,談?wù)勀銓?duì)“城市文學(xué)”寫作的理解吧。
梁寶星:我對(duì)城市文學(xué)是滿懷期待又憂心忡忡的,期待是因?yàn)閲鴥?nèi)城市文學(xué)的缺失,這個(gè)空間足以讓它往四面八方延伸;擔(dān)憂也是因?yàn)槌鞘形膶W(xué)的缺失,我們?cè)撚檬裁礃拥奈淖謥硖顫M它。這兩年,關(guān)于城市文學(xué)的討論很多,但是城市文學(xué)的成果依然不夠。文學(xué)的進(jìn)度是緩慢的,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是飛速的,還有一個(gè)因素,在互聯(lián)網(wǎng)社會(huì),文學(xué)生態(tài)受到擠壓,年輕寫作者群體越來越小,作者群體老齡化,所以城市文學(xué)的發(fā)展進(jìn)度可能會(huì)更慢。在關(guān)于城市文學(xué)的探討中,爭論得最多的可能就是城市文學(xué)和鄉(xiāng)土文學(xué)之間的界線。這樣的討論也就是要給城市文學(xué)做一個(gè)定義,到底什么樣的文學(xué)才是城市文學(xué)。我覺得,在城市文學(xué)發(fā)展的上升期,不妨讓其自由地發(fā)展,不要一開始就把那團(tuán)火給掐滅。城市文學(xué)最基本的特征或許就是城市因素,所謂的因素不是必須要寫“城市”,“城市”是個(gè)主體,我理解中的城市因素更多是指城市經(jīng)驗(yàn)。一個(gè)在城市里生活、生活過的人(不以人為敘事對(duì)象的小說除外),他可以帶著他的城市經(jīng)驗(yàn)出現(xiàn)在任何地方。他可以在樹林里、在海島上、在封閉的墳?zāi)怪猩睿墓适卤仨殠в谐鞘薪?jīng)驗(yàn)。另外,我認(rèn)為城市文學(xué)的敘述語言需要用城市語言,寫當(dāng)下的城市生活就應(yīng)該用最當(dāng)下的語言。《海邊別墅》所寫的是一個(gè)網(wǎng)絡(luò)作家跟一個(gè)音樂人在海島上的生活,我覺得這部小說在城市文學(xué)的范疇內(nèi)。
3
陳培浩:我想從《海邊別墅》來談?wù)勑≌f的裝置性。小說的裝置性并非所有的小說都有,它是有意識(shí)將藝術(shù)裝置植入文本的結(jié)果,在傳統(tǒng)以故事、人物、情節(jié)、環(huán)境等為要素的現(xiàn)實(shí)主義敘事中幾乎不會(huì)出現(xiàn),在現(xiàn)代主義的實(shí)驗(yàn)小說探索中較為常見。裝置這個(gè)詞來自于視覺藝術(shù)領(lǐng)域,對(duì)于視覺藝術(shù)來說,藝術(shù)和思想表達(dá)天然地需要通過視覺化的裝置來呈現(xiàn)。對(duì)于小說這樣的語言藝術(shù)形式來說,藝術(shù)裝置植入小說,其實(shí)是小說實(shí)驗(yàn)吸納轉(zhuǎn)化其他藝術(shù)領(lǐng)域經(jīng)驗(yàn)的結(jié)果。《海邊別墅》中那本《平行鏡像分析》的書就構(gòu)成了理解作品的重要裝置。
王威廉:裝置,換個(gè)詞來說,就是設(shè)置。現(xiàn)實(shí)主義作品不需要裝置,不需要設(shè)置,因?yàn)樽x者和文本享用的是同一套設(shè)置,現(xiàn)實(shí)的機(jī)制,大家都懂,都明白。但在現(xiàn)代主義乃至后現(xiàn)代主義的藝術(shù)作品里邊,作家硬性對(duì)世界進(jìn)行規(guī)定,在我的作品中,世界的規(guī)則只能如此,然后你們看到了和這個(gè)現(xiàn)實(shí)世界不大一樣的面向。現(xiàn)代藝術(shù)包括小說經(jīng)過了這么年的發(fā)展,這認(rèn)為“設(shè)置”已經(jīng)深入人心,人們甚至對(duì)此帶著極大的閱讀期待,期待著看到作者的藝術(shù)世界是如何設(shè)置的。因此,大家都發(fā)現(xiàn),文學(xué)和藝術(shù)對(duì)于思想的要求越來越高,原因就是只有好的思想才能提出更加具備思辨性的設(shè)置。當(dāng)然,不否認(rèn),一兩個(gè)好的想法,可以支撐起幾部好作品,但是,作為職業(yè)乃至志業(yè)的作家,幾個(gè)好想法很快就會(huì)用完,還是需要背后有源源不斷的思想力量去支撐繁多的設(shè)置,這種設(shè)置在藝術(shù)作品中就是裝置,就是錘子、釘子、鋸子,可以在板結(jié)的觀念地圖上進(jìn)行改造。還有一點(diǎn),現(xiàn)實(shí)已經(jīng)變得繁雜多變,傳統(tǒng)的現(xiàn)實(shí)主義作品與讀者之間的默契也不斷被打破,因此,新的現(xiàn)實(shí)主義作品必須包蘊(yùn)現(xiàn)代主義的精神,必須使用裝置重新恢復(fù)和現(xiàn)實(shí)之間的有效聯(lián)系。
陳培浩:我想起你的小說《城市海蜇》,這篇小說中海蜇就是一個(gè)具有很強(qiáng)裝置性的物象。《城市海蜇》采用你慣用的雙線人物模式,主要人物孔楠和張鋒是城市化過程中二個(gè)相互對(duì)照的主體。孔楠是那種從職業(yè)(攝影師)到趣味(喜歡透過鏡頭和女友做愛)到生活方式已經(jīng)被全面城市化的主體。這個(gè)在深圳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攝影藝術(shù)家從內(nèi)陸來到沿海,他無可避免地卷入了深圳生活的深處。不同于母親對(duì)城市的陌生和恐懼,他看似成為城市潮人,開著奧迪,從事著不無潮流意味的工作,可是高房價(jià)的城市顯然拒絕了他的安居。作為孔楠發(fā)小的張鋒大學(xué)畢業(yè)后回歸家鄉(xiāng),過起了穩(wěn)定的公務(wù)員生活。這似乎是大多數(shù)夢(mèng)想屈服于現(xiàn)實(shí)者的生活路徑,從此安逸而自閉地過起小城市人的日子。你在張鋒線索上做了不確定性處理。一種可能是張鋒在女友文櫻病逝之后用文櫻的身份繼續(xù)生活。他已經(jīng)厭倦了被父親操縱的“張鋒”身份,文櫻為他提供了一個(gè)身份避難所。有趣的是,張鋒的精神危機(jī)來自于母親的失蹤。母親的失蹤則由于張父的不忠,張母逃進(jìn)深山去尋求宗教的庇護(hù)。可見,城市病的擴(kuò)散不僅發(fā)生于巨型都市,被瓦解的傳統(tǒng)家庭倫理成了張鋒精神坍塌的緣由。換言之,活在小城市的張鋒并沒有逃過城市巨獸的吞噬。理解這篇小說,無法拋開城市海蜇這個(gè)裝置性的意象。小說中,孔楠經(jīng)常寄明信片給張鋒,吸引著張鋒和文櫻的明信片上的“城市海蜇”后來被證明不過是一堆白色垃圾。借著“城市海蜇”這個(gè)裝置,你在小說中結(jié)構(gòu)了一種“真”與“擬真”的視野。“真”是傳統(tǒng)社會(huì)的倫理和審美基礎(chǔ),而現(xiàn)代都市則在科技推動(dòng)下日益進(jìn)入了“擬真”世界,并建構(gòu)了一種全新的倫理和審美。書寫都市熙熙攘攘的都市故事是不夠的,只有深入都市內(nèi)部的倫理和審美變遷才是真正捕捉住當(dāng)代都市騷動(dòng)的魂。如果我們將漫山遍野的花稱為真的話,一張關(guān)于漫山遍野的花的照片則是一種擬真。城市化的生存,擬真越來越超越了真本身而成為另一種霸權(quán)式的真實(shí)。由此看來,作為攝影家的孔楠,這個(gè)身份不是可有可無的,它是支撐小說隱喻非常重要的設(shè)置。小說中,孔楠的感情包括性都被攝影這個(gè)介質(zhì)所中介化,只有看著鏡頭里的女友,他才激發(fā)起無比的欲望。這意味著,擬真已經(jīng)成了他生活中更真實(shí)的部分。城市海蜇,明信片中大片的海蜇究竟往何處尋?這種奇跡般的海上生命景觀究竟是真還是擬真?這些構(gòu)成了小說很重要的精神追問。
王威廉:《城市海蜇》沒有涉及專門鏡像,但確實(shí)涉及了你說的擬像問題。明信片上的美麗海蜇,其現(xiàn)實(shí)生產(chǎn)居然是基于白色的塑料垃圾,這兩者之間的關(guān)系是這個(gè)時(shí)代及其之后時(shí)代的關(guān)鍵隱喻。鏡像已經(jīng)伴隨人類太多年,但今天人類正在大規(guī)模生產(chǎn)擬像,在今天的擬像世界之內(nèi),已經(jīng)包含著傳統(tǒng)的鏡像。當(dāng)我們?cè)?jīng)只能和鏡像同時(shí)出現(xiàn)、同時(shí)消失之際,那個(gè)完整的主體的確還能在時(shí)空層面確定自身的完整。但今天我們迷失在鏡像的叢林當(dāng)中,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擬像出現(xiàn)在不同的時(shí)空,我們得反復(fù)確定那就是“我”。實(shí)際上,我們對(duì)那個(gè)擬像感到的是無比陌生。尤其是生產(chǎn)擬像的工具不斷進(jìn)化——自動(dòng)美圖、美顏的相機(jī),生產(chǎn)出那個(gè)我們更愿意接納的自我擬像,但這個(gè)自我擬像離主體的現(xiàn)實(shí)實(shí)際上越來越遙遠(yuǎn),人們也就越加無法接納這個(gè)現(xiàn)實(shí)。擬像的瘋狂,已經(jīng)讓人類愈加迷失在人類中心主義的迷霧深處。今天,如果我們提到現(xiàn)實(shí),而把擬像擯除在外,那樣的現(xiàn)實(shí)將和我們的實(shí)際狀況毫無關(guān)系。
陳培浩:葉芝曾經(jīng)說過,當(dāng)隱喻“還不是象征時(shí),就不具備足以動(dòng)人的深刻性。而當(dāng)它們成為象征時(shí),它們就是最完美的。”誠然,隱喻是作為修辭的局部存在,而象征則是輻射全局的精神光源。當(dāng)代生活內(nèi)部光怪陸離、溝壑萬千,如果不能探究其本并為其創(chuàng)造一個(gè)精神象征,小說就只能在故事層面上打轉(zhuǎn)。因此,小說裝置其實(shí)是將小說從故事和敘事層面引渡到精神敘事的橋梁。
王威廉:隱喻可以是零星的,但象征必須是龐然大物。前者可以像鳥群掠過,后者必須像山峰聳立,無情地阻擋人們的視線,讓人們的視線必須落在它們的身上。小說的裝置,在操作層面上表現(xiàn)為設(shè)置,就是在尋找那樣的象征。很多作家、藝術(shù)家都在不斷強(qiáng)調(diào)自己的某個(gè)、某幾個(gè)隱喻,通過一個(gè)隱喻的譜系進(jìn)而建構(gòu)一個(gè)象征的煌煌宇宙。這是不容易的,哪怕是零星的隱喻背后,都隱藏著作家對(duì)于世界的根本性看法,更不要說一個(gè)宏大的象征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