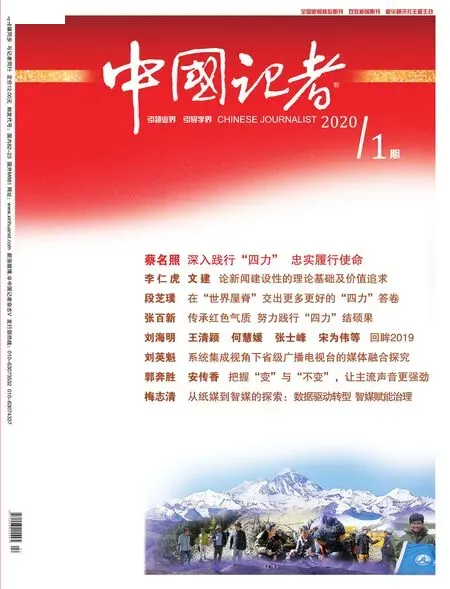在高寒地區“尋寶”的“四力”感悟
□ 張京品
西藏有一句話:遠在阿里,苦在那曲。在不少人眼里,平均海拔超過4500米的阿里與那曲,是極其偏遠荒涼的高寒地帶,是報道資源偏少的“新聞洼地”。但正是這些人跡罕至的地方,成就了我在藏8年最大的收獲。
2019年春節前夕,我和同事到藏北那曲市安多縣采訪。安多縣距拉薩500多公里,北接青海省,地處唐古拉山麓,平均海拔5200米。西藏老百姓說,安多有“三多”:風多、雪多、冷天氣多。
出發前,青藏鐵路公司唐古拉線路車間副主任馬祎俊發來暴雪紛飛的視頻說:“這么大的雪,路上一定結冰了,你們別來采訪了,太危險!”安多縣氣象局值班人員說:“這個季節縣里不少干部都休假走了,也從沒有記者這時候來采訪我們。”
盡管安多最低氣溫已達零下30攝氏度,盡管安多“已是風雪百丈冰”,盡管當地干部勸我們換個季節再來,但為了走近高海拔地區的堅守者,我們毅然前行。
我們深入“天下第一氣象局”——安多縣氣象局,世界海拔最高有人值守火車站安多火車站,青藏鐵路海拔最高、養護難度最大的唐古拉線路車間等地,采寫了《天路之巔看不見的“軌枕”》《海拔4700米的春運時光》等一批反響強烈的稿件,挖掘出扶貧干部典型、藏族村支書古多的先進事跡。其中,《解碼風云錄 逐夢天地書——“世界最高氣象站”三代氣象人的守望》,被中宣部、中國記協評為“2019年新春走基層中央新聞單位增強‘四力’優秀作品”。
安多縣多瑪鄉是一個在電子地圖里都搜索不到的地方。當地一些干部說,多瑪就是“一個被人遺忘的地方”。因為沿途沒有網絡信號,我們翻過“雄鷹飛不過”的唐古拉山,邊打聽邊探路,終于抵達了多瑪鄉。見到我們,當地干部驚訝地問:“你們究竟是怎么找到這里的?”
就是這么一個不起眼的地方,我2019年先后兩次前往。在這里,我和同事完成了青藏邊界糾紛的調研報道,引起有關部門重視,推動了問題的解決。報道作為踐行“四力”的優秀作品,獲評2019年上半年新華社優秀新聞作品。
這是我在藏西、藏北基層一線收獲的第二篇新華社優秀新聞作品。2018年9月,在分社主要領導帶隊下,我和同事到阿里地區調研,行程5000余公里,翻過4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山,期間克服重重困難,抵達中印邊境楚松村,這是中央媒體首次抵達這個邊境小村。我們采寫的《西藏阿里楚松村“四代房”:中國邊陲巨變的縮微影像》,獲評2018年下半年新華社優秀新聞作品,收錄進《新華社踐行“四力”優秀作品選》。
新華社每天發稿量很大,因此,想獲評新華社年度優秀新聞作品,并不容易。連續兩年收獲兩篇“獨家的”新華社優秀新聞作品,更不容易。這說明只要深入踐行“四力”,人跡罕至的高海拔地區照樣能成為“新聞富礦”;證明了西藏分社將高海拔地區作為踐行“四力”主戰場的遠見卓識。
實際上,在高海拔地區踐行“四力”,我收獲的遠遠不止這些報道,更多的是心靈的觸動、思想的錘煉、精神的洗禮。“在高原上工作,最稀缺的是氧氣,最寶貴的是精神”。毫無疑問,在西藏,4500米以上的極高海拔地區更艱苦,但堅守在這里的干部群眾的精神更感人。2019年5月,我和同事挖掘出山東籍教師夫妻杜安東、曹曉花十余年扎根全國海拔最高縣小學,把自己的孩子寄養在老家、當藏族孩子爸爸媽媽的事跡,引發廣泛關注。西藏自治區召開黨委常委會,要求健全完善制度機制,關心關愛長期在高海拔、邊遠地區工作的干部職工。一方面,我們為高海拔地區的堅守者鼓與呼,另一方面,也被他們堅守的精神深深感動著。有時候覺得苦、覺得累,想想他們,就覺得自己吃的苦也算不上什么。
回顧我的新聞時光,從一個學習日語的非新聞專業大學生,到今天能在新聞領域取得一點成績,正是得益于“四力”這個方法論。我的感悟是:
一、踐行“四力”,要有一股尋求未知的求索精神。毛主席詩詞說,“無限風光在險峰”。王安石《游褒禪山記》中有一段話,“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于險遠。夫夷以近,則游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我喜歡到“來而記之者已少”的地方。8年間,我走過西藏74個縣(區)中的70個縣(區),8次到世界最高鄉、海拔5373米的普瑪江塘鄉采訪,到過西藏最偏遠的村莊,到過難以抵達的邊境哨所,有5個春節在西藏度過。盡管很艱辛,甚至很危險,但“人生從來沒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數”。走過的這些路,經歷的這些事,夯實了我作為新華社記者的基石。抵達是新聞報道的基礎。很多時候,就是“腳力”到了,好作品可能也就有了。我的很多報道,都是下鄉采訪過程中偶然發現的“活魚”。
二、踐行“四力”,要有一股堅定理想的無畏精神。腳力是踐行“四力”的基礎已經成為廣大新聞工作者的共識,但走好腳力背后,則有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堅定的理想信念。
作為一名新聞工作者,當面臨危險挑戰時,當面臨困難時,能否下定決心前往新聞現場,是否愿意主動前往艱苦的新聞現場,就是考驗記者職業素養的重要指標。2019年第1期《求是》雜志發表的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文章《辯證唯物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中指出,我們黨強調理想信念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強調“革命理想高于天”,就是精神變物質、物質變精神的辯證法。回顧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追溯一代代新聞人創作新聞名篇的過程,就能發現正是堅定的理想信念讓他們在面對艱辛和危險時,勇敢地邁出了“腳力”。十八軍克服高原反應,邊修路,邊戰斗,完成了進軍西藏的光榮任務。著名記者郭超人克服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跟隨中國登山隊攀登珠穆朗瑪峰,登抵海拔6600米高度,寫出《紅旗插上珠穆朗瑪峰》等佳作。他還不顧個人安危,在1962年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中堅持到炮火紛飛的戰場采訪。這些都是以理想信念走好“腳力”的生動體現。可以說,新聞工作是一項充滿危險、充滿挑戰、充滿艱辛的高強度工作,沒有堅定的理想信念,是做不好新聞報道的。
三、踐行“四力”,要有一股潛精積思的鉆研精神。對于很多西藏的記者來說,有時候難熬的,不是高寒缺氧的自然環境,而是語言不通。他們常常抱怨,感覺受訪的農牧民講了很多,但翻譯卻只有兩三句話。有前輩給我說,在西藏當記者,要融入普通藏族百姓的生活,就要努力學習藏語。在前輩的鼓勵下,我2012年大學畢業到西藏的第二個星期,就自費報名到拉薩一家語言學校學習藏語,從最基礎的藏語字母學起,到日常對話,最多的一年寫了21本藏語作業本。只要不下鄉,我都堅持去上課,下鄉出差也隨時帶著藏語口語教材,如今基本完成了小學藏語文的課程學習,具備了一定的藏語聽說讀寫能力。盡管我的藏語水平還不高,但到了藏族百姓家里,也能用藏語和他們交流一番,他們因此特別高興,距離感自然就小了,愿意和我分享更多的故事。從入社時起,就不斷有新聞前輩和我說,要努力做專家型記者。在分社支持下,2016年我考取了西藏大學藏族歷史專業博士研究生,希望以此增進對西藏的認識,把涉藏報道做得更專業。學藏語、研藏史,對我到農牧區采訪、采寫涉藏深度報道提供了很大幫助。
四、踐行“四力”,要有一股行思坐想的思考精神。新聞工作的本質是政治工作,是理論與實踐、存在與思維相統一的產物,極大考驗記者的發現力、把握力、分析力、辨別力、判斷力。提高這些能力,就必須養成善于學習、善于思考的精神,必須養成從報道中總結經驗教訓、提煉理論觀點的習慣。在分社的倡導下,我養成了把新聞報道與理論思考相結合的習慣。近三年,我在《中國記者》《青年記者》《西藏研究》等刊物刊發業務文章23篇,極大提升了自己的新聞理論素養,反過來也促進了新聞實踐。
五、踐行“四力”,要有一股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新聞界流傳著一句話,新聞無學,文無定法,但隨著自己的新聞實踐越來越多,我對這種說法越來越不認可。因為“新聞看起來無學,但實際上處處有學;文章看起來沒有定法,但實際上處處有法”。增強“四力”教育實踐工作開展以來,我深刻體會“筆力”的內涵,認識到寫稿子也是一門手藝。馮驥才先生在《俗世奇人》中寫道:“手藝人靠的是手,手上就必得有絕活。”手藝人靠對技藝的不懈追求,贏得社會的尊重。當前,國家大力弘揚的“工匠精神”,對于記者來說,同樣適用。因為稿子就是我們的手藝,必須抱著“文無止境”“止于至善”的態度,對稿件的每一句話、每一個詞、每一個標點認真推敲打磨,讓稿件“漂漂亮亮”“干干凈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