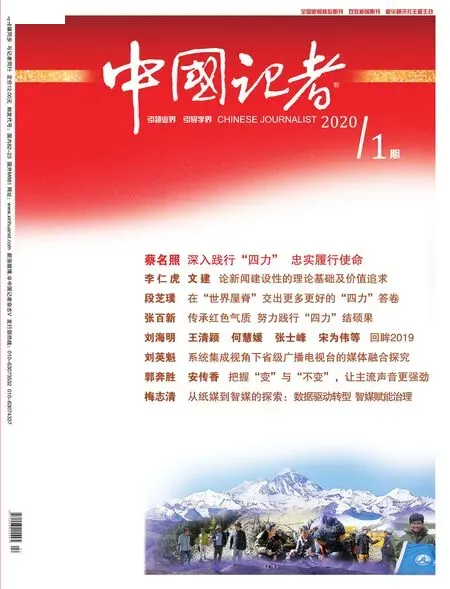意識形態偏見與西方媒體涉港報道的選擇框架
□ 王潤澤 徐誠
內容提要 在近期涉港問題報道中,部分西方媒體以“不客觀”“不平衡”的報道表現出明顯的意識形態偏見。西方媒體的報道偏見深植于政治與文化意識形態,常常將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置于“他者化”的新聞框架,以報道的“雙重標準”造成新聞內容的失衡。本文從報道的理論分析出發,對西方媒體報道出現問題的原因進行梳理,并聯系公共輿論安全討論了媒介報道中意識形態偏見的應對策略。
2019年夏秋以來發生在香港的修例風波、極端暴力事件不斷升級。暴力行為的嚴重性、香港這一地域的重要性與敏感性使得涉港問題報道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鋪天蓋地的報道使新聞事件延伸至更為宏觀和政治化的層面,部分西方媒體的報道從雙重標準出發,以偏概全、主題先行,引發新聞報道“偏見壓倒客觀”的質疑。西方媒體對涉港問題的報道在實踐層面表現出一定的選擇框架與意識形態偏見,報道失衡、不客觀、有失真實的“傾向性新聞”成為西方媒體在新聞市場中爭取觀眾,服務于輿論戰的工具。
一、問題的提出:意識形態偏見與西方媒體涉港問題報道
“對那些在自我利益和社會利益之間存在沖突的人們來說,意識形態是一個重要的決定因素”,在新聞框架的傾向性研究中,意識形態被視為促使報道產生媒介偏見與新聞傾向性的要素之一,在新聞實踐中媒介偏見與新聞傾向性主要體現在新聞事件的選擇框架與報道方式上。[1]沃爾特·李普曼將“刻板印象”與媒介偏見相聯系,“一篇報道是知情者和已知的事實的混合產物,觀察者在其中的作用總是帶選擇的,而且通常是帶想象的。”[2]媒介偏見的消極影響是多方面的,夾帶偏見的新聞報道無法全面反映新聞事件,妨礙了受眾對真實情況的了解,同時,媒介偏見導致新聞事件中某一部分群體受到不平衡、不公正的報道,這將造成社會團體、族群的隔閡,引發社會動蕩,危及社會安全。在國際新聞的跨文化傳播中,媒介偏見更加明顯,西方媒體的新聞報道常將發展中國家置于“他者化”框架,將其與落后、混亂、人權問題等聯系在一起,報道基調呈現出負面內容大于正面的現象。作為現代理性精神的對立面,“他者”被視為異端,與愚昧、混亂、邪惡、骯臟等聯系在一起,為的是證明與維護“我們”在現代生活中的價值。[3]例如,在涉藏報道上西方媒體就以顯著的選擇框架對新聞事實進行加工,中國被視為西方社會的對立面,大量的西方報道對涉藏問題的新聞事實進行歪曲,顯示出明顯的意識形態偏見。[4]
香港發生修例風波、暴力破壞活動后,大量的西方媒體報道將中國大陸與中國香港建構成為彼此對立的兩派,以非常鮮明的選擇框架將香港警察、中國大陸建構為一個與之敵對的“他者化”形象,這些報道往往以偏概全、主題先行,在選擇框架背后隱藏了西方社會的意識形態偏見。美國媒介分析家愛德華·赫曼和諾姆·喬姆斯基在《制造共識:大眾媒體的政治經濟學》一書中提出“宣傳模型”的概念,指出宣傳模式導致了“輿論同化”現象。[5]在對華報道中,特別是在對西藏問題、香港問題等的報道上,西方媒體以其“東方主義心態”顯示出強烈的媒介偏見,使得西方新聞界標榜的客觀性與獨立性的原則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6]例如,英國《衛報》、英國廣播公司(BBC)等西方媒體2019年7月30日報道了一則消息:香港警察用搶指著抗議群眾,并配有圖片或者剪輯過的現場視頻,英國廣播公司甚至斷章取義地將新聞標題定為“警察拿槍指著抗議人士”。據《中國日報》調查,7月30日晚,在香港葵涌警署外,一群“黑衣人”號稱“和平示威”,但卻用磚頭砸、激光筆照、棍棒打等攻擊警察。現場拍攝的完整視頻也顯示,兩名落單警察被近百人圍住并毆打,暴徒向警察投擲不明物體,還用激光筆試圖使落單警察喪失防衛能力。在此情況下,一名警察揮舞警棍自衛,一名白衣警察迫于無奈舉槍。31日,前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陳祖光回應記者采訪,當晚的情勢下該警察舉槍完全沒有問題。
傳統的新聞框架理論圍繞媒體新聞報道的傾向性,認為新聞記者在報道過程中主觀地構建了一個社會“真實”,這一框架受到記者主觀意志的影響。就概念的理論內涵而言,新聞框架的構建圍繞新聞內容的選取與舍棄,主要包括了“選擇”“凸顯”“遺漏”與“包含”等內容。[10]例如,在英國《每日電訊報》8月2日的報道中,報道稱香港的抗議者為與警察作斗爭不得不采取創新手段,如設立路障、使用激光筆(鐳射槍)等。實際上,這種激光筆具有攻擊性的事實被西方媒體報道有意“遺漏”,報道也因此具有了明顯的選擇框架。據《中國日報》調查,自6月以來,香港示威者多次在沖突中使用激光筆照射警察眼睛,已導致多名警察受傷與不適。8月7日香港警方在記者會上現場演示經激光筆照射后的情況。現場一名戴著黑色防護鏡的人員手持銀色激光筆,近距離照射紙張,大約十秒,紙張上出現白煙,繼續照射后,紙張被燒穿起火。
從文字、圖片與視頻的展示都能看到,西方媒體對涉港問題的報道已經從各個方面建立了選擇框架,這種框架使得新聞報道出現了清晰的價值判斷,將中國香港與中國大陸置于兩個彼此對立的陣營。事實上,回顧此次事件的發展過程不難看出,西方媒體的報道存在明顯的“選擇”,報道出現明顯的失衡。長期以來,香港一直是西方媒體對華報道的一個重要議題,作為香港暴力事件的導火索,《逃犯條例》的修訂旨在處理有關香港居民涉嫌在臺灣殺人案件的移交審判問題,同時堵塞香港現有法律制度的漏洞。香港特區政府于2019年4月向立法會提交了《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以使香港可與尚無長期司法互助安排的司法管轄區展開個案合作。但是無論是報道展現的香港問題具體細節,還是在對香港暴力活動的報道上,西方主要媒體的報道都顯示出很強的同化性,這一現象展示出西方話語對“香港問題”獨有的意識形態偏見:一方面,西方話語中的香港具有殖民地色彩,在這一情境中,中國大陸與中國香港的關系具有復雜性;另一方面,刻板印象與意識形態偏見強化了西方媒體報道的傾向性,破壞了新聞報道的客觀性。概言之,在大眾媒體、西方話語和東方主義刻板印象的綜合作用下,輿論放大了公眾對于香港問題的偏見,使得西方媒體在迎合讀者的商業訴求驅使下構建出傾向性明顯的新聞框架,近乎一致地選擇新聞議題,報道體現出更為明顯的偏見。
新聞選擇框架的傾向性研究存在一個前提,即多數媒體主張新聞報道的客觀性,并認為新聞工作者存在客觀報道的義務。與新聞的客觀性相區別,框架理論認為記者在報道過程中所建構的“真實”帶有一定的主觀性,這個“框架”是記者主觀意志的體現。因此,就西方媒體涉港問題的具體報道而言,新聞框架的構建更加顯著,凸顯了中西方報道差異,這背后是西方話語中心對香港問題的巨大意識形態偏見。在文字報道中,英國廣播公司(BBC)和英國星空電視(SkyNews)始終用爭取民主的抗議者(Protester)來稱呼那些破壞公共秩序和設施的暴徒,更為鮮明的是圖片報道和視頻的選取,網絡與社交媒體的傳播中西方媒體對文字、圖片、視頻的選取都說明西方媒體的涉港問題報道已經從各方面凸顯了選擇框架。
二、西方媒體新聞報道中意識形態偏見的原因分析
中西方媒體報道存在明顯差異,特別是在涉港、涉藏問題的報道上,西方媒體在報道基調上展現出一貫性與一致性。在新聞實踐中,西方話語往往將中國建構為一個敵對的“他者化”形象,充滿了落后、混亂和人權問題。從新聞框架的理解看,中西方媒體報道之間存在差異的原因主要為西方對中國的意識形態偏見,在全球化背景下這種偏見催生了西方媒體所使用的選擇框架。另一方面,受到商業化運作和西方客觀報道準則的影響,西方新聞報道中的媒介偏見還具有一定的復雜性。
(一)意識形態偏見與“他者化”框架
新聞報道不只是“傳遞信息的工具”,其意義在于對原本的社會事實進行意義化和選擇性重構,借助意義化的過程將事實的敘述條理化,以此構建一個有意義的符號世界。在圍繞2019年涉港問題報道中,中西方媒體報道表現出相當明顯的差異性,而出現這些報道差異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西方媒體都將中國的國家形象矮化,將中國塑造成一個落后、混亂和不尊重人權的國家,在近期的涉港問題報道中,西方媒體構建的針對中國新聞報道的雙重標準存在明顯的“妖魔化”中國的傾向,折射出意識形態的偏見;其二,在全球經濟下行、西方社會矛盾不斷出現的情況下,西方媒體急需構建一個“他者”的形象。在近期涉港問題的報道中,中國大陸與中國香港被西方媒體描述成兩個對立的陣營,報道內容將中國大陸刻意建構為一個與中國香港敵對的“他者化”形象,激化社會矛盾,為實現這一目的,報道的客觀性最終流于形式和表面化。
國際新聞傳播中西方媒體報道構建選擇框架的目的之一即是以宣傳模式促進“輿論同化”,體現出了明顯的意識形態偏見。英國哲學家約翰·湯普森認為,“把一種觀點稱為‘意識形態’,似乎就是已經在含蓄地批評它,因為意識形態的概念似乎帶有一種負面的批評意義”。[11]當前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去意識形態化、淡化意識形態的聲音層出不窮,然而就西方媒體在涉港、涉藏報道上的表現而言,英國廣播公司(BBC)等西方主流媒體的意識形態性顯而易見:一方面,諸多西方媒體在近期涉港問題的報道上對事實進行歪曲,報道偏頗,另一方面,具備強大傳播實力的西方媒體在涉港報道上與中方媒體一度開展爭奪話語權的競爭。從傳播過程看,西方媒體涉港報道的選擇框架具有一致性,其報道基調體現了西方社會遏制中國的意識形態霸權。
西方媒體報道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所進行的“他者化”新聞框架構建可以認為是西方文化霸權的一個典型體現。在傳播學理論中,“霸權”是某個社會群體在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內的領導權,西方媒體在涉港問題報道上的表現正是西方文化霸權的體現,它不僅需要媒體的作用,還需要文化工業與國際輿論對其的認可。在這一背景下,西方媒體借助新聞報道的議程設置與西方社會輿論之間達成了一種價值認同,兩者相互影響,共同建構了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偏見。在跨文化傳播中,權利關系模式與“他者化”表征緊密相連,新聞媒體成為主導權力的鼓噪者,將帶有偏見的報道卷入權力運作,以更為多樣的形式干預政治。因此,在西方媒體的新聞實踐中,圍繞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報道內容更多聚焦于負面問題,新聞信源和內容都呈現失衡狀態,大量體現西方價值觀的象征符號被運用,中國被塑造成為與西方社會相對立的“他者”。在近期涉港問題報道中,西方媒體將香港警察建構成敵對的“他者”,歪曲報道香港警察依法執法、止暴制亂,污蔑警察過度執法,同時對暴徒用易燃液體焚燒無辜市民、企圖搶奪警察佩槍、威脅警察生命安全的罪行進行蓄意包庇和美化。
(二)商業化與新聞客觀性的內在悖謬
在商業化運作模式的驅動下,西方媒體需要以“戲劇性”刺激讀者對媒介文化產品的消費欲望,而這種“戲劇性”與新聞的真實性、客觀性存在矛盾之處,在西方媒體對涉港問題的報道中客觀、平衡地展現各方聲音的報道幾乎沒有,一些報道甚至斷章取義、夸大其詞,為在香港進行暴力、破壞、恐嚇活動的暴徒唱贊歌。另一方面,在近期涉港問題的報道中,西方媒體媒介偏見的體現進一步驗證了西方新聞界客觀性神話的破滅,這些夾雜偏見的新聞內容體現了西方媒體報道的“表面客觀性”或“偽客觀性”。
新聞客觀性借助記者的新聞實踐而得以建立,包含一套新聞采訪與報道的技術標準。客觀報道與新聞內容的傳播效果、受眾的閱讀態度緊密相關,深刻影響著社會輿論的發展趨向。作為一種報道的手法,客觀報道發源于新聞事業發達的西方國家,中國學界長期將新聞客觀性視為資本主義新聞業的理論內容,直到改革開放后才逐漸引入。就新聞客觀性與客觀報道的概念解讀而言,中國和西方新聞界對客觀報道有不同的理解。作為客觀報道的對立面,報道偏見很難被完全消除,記者在選擇事實的過程中不免受到來自國家與民族利益、階級與種族意識、政治、文化與意識形態層面各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構成了記者等新聞工作者反映與理解現實和新聞事件的框架。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徹底擺脫報道偏見,實現完全的客觀性被認為是不可能的,而這一對報道客觀性的懷疑一度使美國的新聞報道走向反面,即完全的主觀性。例如,美國新聞史上20世紀60年代流行的“新新聞主義”就將小說創作的手法運用于新聞寫作,不但包攬了新聞要素,還以“解放媒介”為口號對新聞內容進行大規模改寫,細致地描寫當事人的心理活動,并表達寫作者的評論與意見,然而“新新聞主義”對客觀報道的完全拋棄并沒有得到讀者的認可,記者的職業性質決定了他們必須對新聞報道的客觀性負責。中國新聞界對客觀報道的接納與實踐較早體現在消息與通訊寫作上,胡喬木在其《人人要學會寫新聞》中認為“最有力量的意見,是一種無形的意見——從文字上看去,說話的人只是客觀地樸素地敘述他所見所聞的事實”。[12]在新聞實踐中,中國新聞界認為“客觀報道不等于也不可能沒有傾向性”,客觀報道并不是自然主義,也應有立場,堅持“用事實說話”。[7]
在西方新聞界,客觀報道常被認為是“一個有經驗的職業記者的標志”,是“新聞工作的一項標準”,客觀報道以“平衡”的原則作為新聞客觀的“操作定義”,要求報道內容“務求不偏不倚,盡可能把正反雙方的事實和意見并陳,讓讀者自己評理。”[8]就新聞報道的網絡傳播情況而言,網絡新聞一方面常以社交媒體特有的方式進行新聞信息的交流,帶有鮮明的主觀色彩,另一方面,網絡新聞的客觀性與真實性常彼此糾纏,部分斷章取義、主觀解釋、夸大其詞的報道以“真實性”為幌子,蒙蔽了新聞客觀報道的準則。[9]回顧新聞事業的發展史,報紙由登載船期的廣告紙逐漸演化為政黨黨同伐異的輿論武器,消息發布的系統開始集中化,到了商業化時代,新聞客觀報道原則的衍生與資本主義的商業利益相互結合,平衡、客觀地報道才成為報紙從業者牢固的職業準則。深究新聞事業的發展過程則不難發現,新聞客觀性的產生有著深刻的理論與歷史背景,在新聞實踐中新聞客觀性要求新聞報道反映“普遍利益”。私人資本所掌控的商業化媒體將代表工人階級意識的勞工新聞邊緣化,將資本利益視為社會的“普遍利益”,將資產階級主流價值和統治意識形態轉化為“社會共識”。同時,西方新聞客觀性還與商業化媒體相互依附,政治與經濟動因互為表里,共同構建了客觀性在新聞實踐層面的意義。因此,在西方文化霸權與意識形態偏見的影響下,西方媒體報道呈現出鮮明的“表面客觀性”或“偽客觀性”,客觀報道準則成為粉飾新聞內容的“幌子”,幫助媒介偏見暗度陳倉,制造隔閡與對立。[13]
三、研究意義:意識形態偏見與公共輿論安全的深層關聯
在近期的涉港問題報道中,西方媒體為爭奪話語權,維護西方文化霸權,在報道中采取“雙重標準”,具有明顯的意識形態偏見。這些偏見通過宣傳模式與新聞框架制造共識,促進“輿論同化”,威脅公共輿論安全。按照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札記》對意識形態的分類,媒介偏見也可以被納入“有機的意識形態”與“任意的意識形態”的內涵之中:一部分媒介偏見由社會結構決定,很難避免,另外一部分媒介偏見存在于受眾的頭腦中,受到各種認知過程的影響,集中表現在文化因素中,具有隨意性與非理性的特質。[14]簡而言之,媒介機構受到西方社會的意識形態霸權影響,在新聞報道的框架設置上就具有傾向性,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報以明顯的有機的意識形態偏見,同時西方國家的觀眾與讀者已經在其文化想象中接納了這一偏見,這種偏見有受眾個人因素的影響,也受到特殊的環境因素作用,兩者互為表里、皮毛相依,共同作用于社會心理,對公共輿論安全造成深刻影響。
公共輿論具有鮮明的傾向性、集合性與表層性,公共輿論的形成過程始終處于一種混沌、沖動和非理性狀態,容易受到擺布與控制,通過輿論傳播平臺傳遞信息以作用于受眾。輿論戰是“宣傳戰的一種重要方式,屬于心理戰的宣傳心理戰范圍。即是指以敵集體心理為目標,通過大眾宣傳工具對其心理施加壓力和影響,以期達到改變敵方觀念和意識形態,削弱敵方士氣和瓦解敵軍的作戰方式”。[15]在輿論戰中,“交戰雙方依托新聞媒體展開的全方位的攻心劃謀的特殊作戰樣式,已成為現代戰爭敵我對抗的一個重要內容,并強調要與心理戰、信息戰高度融合,創造性地運用新聞傳播的方法和技巧,使新聞資源的戰場效應得到充分發揮”,“政府和軍隊的宣傳機構控制、操控、策劃、利用各種輿論工具,以網、視、聲、文、圖等為武器,進行旨在壓制對手、贏得公眾的較量”。[16]社會輿論事關意識形態安全,西方國家近年來動用各方力量參與輿論斗爭,媒體機構以輿論為武器,通過利用各種傳播工具和信息資源對重大問題進行導向性宣傳的輿論對抗活動。
夾帶意識形態偏見的新聞報道危害著公共輿論安全,這種報道內容的“失衡”無助于緩解現代化與全球化帶來的社會沖突,反而為全球性問題的解決制造障礙。網絡技術和社交媒體的發展實現了媒體內容的全球化,為西方媒體制度和自由主義媒體理念在全球范圍內推銷文化霸權鋪平道路。因此,受制于以上來自政治經濟文化層面的多重結構性因素的制約,媒介偏見很難消除,作為它的對立面——新聞客觀性對于新聞工作者而言具有相對性與虛偽性。如此而來,客觀報道充當記者壓制主體性的一層表象,不僅為記者爭取了相對于政府與資本的獨立性,還掩蓋了新聞與權力之間的關系。例如,西方媒體認可的所謂“普遍利益”仍舊是西方新聞界與西方占統治地位的政治經濟利益之間關系的反映。[17]
意識形態偏見使得報道具有鮮明的傾向性、導向性,這一點使得新聞報道成為宣傳輿論戰的重要工具。從國際傳播或跨文化傳播的角度看,在近期涉港問題報道中西方媒體偏見的背后隱藏的是更深層次的意識形態偏見,全球化語境下中西方之間的認同壁壘與文化共識的闕如同時也對西方媒體報道的框架設置產生了重要影響。西方主導的媒體如何取舍新聞內容,如何靈活使用客觀性等職業規范,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媒體的政治文化意識形態與新聞價值觀。在近期的香港問題報道中,媒體利用傾向性明顯的報道孤立中國大陸并將其塑造為一個敵對的“他者”,這不僅驗證了新聞客觀性的相對性與虛偽性,也是西方媒體媒介偏見的一個代表案例。近期發生在香港的社會問題不僅僅是中國的主權問題,還藏有更深的文化與意識形態隱憂。西方媒體帶有偏見的報道不僅對公共輿論安全造成顯見的影響,還為中國媒體如何在香港問題的報道中爭取主動權帶來嚴峻挑戰。概言之,簡單的中西方二元對立實際上無助于解決資本主義市場體系中存在的問題,夾帶偏見的報道只能掩蓋問題,探索與尋求全球化視角才能正面由現代化、經濟快速增長與少數族群的多元文化發展帶來的問題。
四、結語
在香港暴力事件升級的情況下,西方媒體涉港問題報道所采取的“雙重標準”體現了明顯的媒介偏見,中國在西方媒體的話語建構中多呈現出一種負面的“他者化”的刻板印象。從新聞事業發展的歷程看,西方新聞界的客觀報道準則所強調的“普遍利益”具有明確的立場,記者、編輯等新聞工作者經由主觀經驗的加工,在新聞報道中移植新聞的選擇框架與媒介偏見。
在近期的涉港問題報道中,西方媒體這種制造對立的“他者化”新聞框架筑起了香港民眾對中國大陸的認同壁壘,激化了社會矛盾。“他者化”新聞框架的設置強化排他性認同,根源于西方社會對中國的意識形態偏見,在新聞報道中出現的媒介偏見與公共輿論互相影響,共同作用于社會心理,危及公共安全。對此,中國媒體一方面應善于設定議題,利用媒介事件引導輿論,與西方媒體爭奪話語權,另一方面中國媒體應避免處于解釋、抗議、聲明等被動狀態,應與外國媒體展開合作,傳達出自己的聲音,避免意識形態偏見所產生的消極影響。
【注釋】
[1]《新聞框架的傾向性研究》,杰拉德·馬修斯、羅伯特·恩特曼著,韋路、王夢迪譯,《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02).
[2]《輿論學》,沃爾特·李普曼著,林珊譯,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51頁.
[3]跨文化傳播在各種思潮和文化沖突的裹挾之下,聚焦“他者的表征”,發展了頗具反思性的“他者化”概念。認同制造了他者化,他者化又制造了“我們”與“他者”的二元對立,進一步強化排他性認同。參見《跨文化傳播視野中的他者化難題》,單波、張騰方,《學術研究》,2016(06).
[4]《西方傳媒“3·14”事件報道的選擇框架與意識形態偏見》,周慶安、盧朵寶,《新聞與傳播研究》,2008(03).
[5]《制造共識:大眾傳媒的政治經濟學》,愛德華·S·赫爾曼,諾姆·喬姆斯基著,邵紅松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6]《維系民主?西方政治與新聞客觀性》,羅伯特·哈克特,趙月枝著,沈薈、周雨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6頁.
[7]《客觀報道與對外報道》,唐潤華著,收錄于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研究室編:《對外宣傳工作論文集》,五洲傳播出版社1998年版,第321-332頁.
[8]《美國新聞道德問題種種》,約翰·赫爾頓著,劉有源譯,中國新聞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頁.
[9]《網絡新聞傳播學》,董天策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頁.
[10]Entman,R.M.Framing:Towardclassificationoffractured paradigm.JournalofCommunication,1993(4):51-58.
[11]《意識形態與現代文化》,約翰·B·湯普森著,高铦等譯,譯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5頁.
[12]《中國報紙的理論與實踐》,李良榮著,復旦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頁.
[13]《簡論新聞報道中的媒介偏見——以西方媒體新聞報道為例》,徐琴媛、楊卓穎,《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2(10).
[14]《獄中札記》,安東尼奧·葛蘭西著,葆煦譯,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頁.
[15]《傳播技術發展與輿論戰的嬗變》,劉燕、陳歡著,軍事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頁.
[16]《伊拉克戰爭中美軍的輿論戰法》,楊堂珍,《軍事記者》,2004(7).
[17]《為什么今天我們對西方新聞客觀性失望?》,趙月枝,《新聞大學》,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