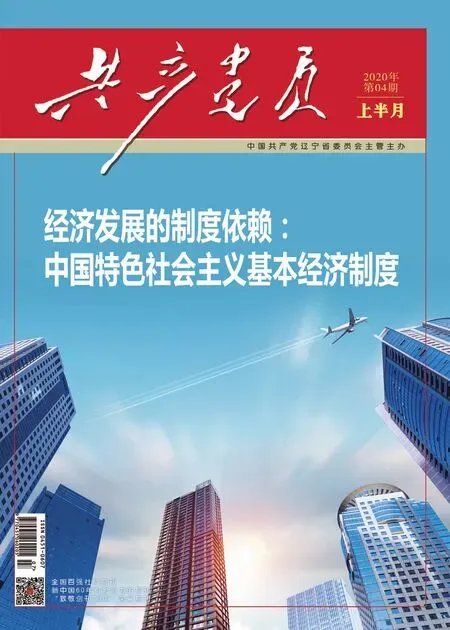傳統社會主義經濟模式的形成與終結
早在19世紀中期,馬克思、恩格斯就在《共產黨宣言》《資本論》 《巴枯寧〈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摘要》 《哥達綱領批判》等經典文獻中,提出了他們對未來社會主義社會一些原則性設想,如生產資料全部由社會占有(公有);生產要素由社會中心統一調配(計劃調節);消費品在共產主義低級階段實行按勞分配,而進入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則實行按需分配。這幾個方面彼此相互依存,是馬克思、恩格斯為未來社會構建的基本制度框架體系。
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把社會主義社會的所有制概括為“社會所有制”,認為在未來理想社會即“自由人聯合體”中,生產者“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并且自覺地把他們許多個人勞動力當作一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一個社會的產品。這個產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一部分依舊是社會的”。后來,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又進一步申明,在社會主義社會這一歷史階段,“以生產資料公有為基礎”,“除了個人的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轉為個人的財產”,而這種生產資料的公有依然是社會所有,而非國家所有,因為這時“政治意義上的國家”已經消亡。由此,馬克思繼續提出,在一個集體的、以生產資料公有為基礎的社會中,生產者不交換自己的產品;用在產品上的勞動,在這里也不表現為這些產品的價值,不表現為這些產品所具有的某種物的屬性,因為這時,同資本主義相反,個人的勞動不再經過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為總勞動的組成部分存在著。于是,生產者“從社會領得一張憑證,證明他提供了多少勞動(扣除他為公共基金而進行的勞動),他根據這張憑證從社會儲存中領得一份耗費同等勞動量的消費資料”。顯然,對照馬克思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構想,現實中的社會主義社會顯然與其有著明顯的區別。
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列寧領導下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進行了初步探索,提出了諸如“新經濟政策”之類的新思想,豐富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由于列寧去世較早,新經濟政策后來沒有得以執行。之后,我們常說的蘇聯經濟模式,實際上是在斯大林領導下逐步形成的。20世紀50年代初,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輯出版了《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該教科書根據蘇聯的經濟建設實踐對社會主義經濟模式作了概括,即“社會主義經濟=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這個概括被理論界稱為“蘇聯模式”。新中國成立后,開始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當時中國共產黨對如何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確實沒有經驗,因而能夠參考借鑒的唯有“蘇聯模式”。
新中國成立不久,便陸續建立了中央財經委員會及負責計劃管理的中央機構,如全國編制委員會、全國倉庫物資清理調配委員會等。人民政府通過這些機構,開始對全國經濟活動實行計劃管理,沒收官僚資本主義工礦企業,調整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代管帝國主義的在華資產,統一財政管理,編制《1950年全國財政收入概算草案》《1950年國民經濟計劃概要》等,建立了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企業,并使之在國民經濟中居于領導地位,初步把私人資本主義企業納入國家計劃的軌道,計劃經濟體制的格局雛形出現。
緊接著,1950年6月召開的黨的七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爭取國家財政狀況基本好轉的中心任務以及完成這一任務的三個條件和應當做好的八項工作。由此開始,新中國掀起了恢復國民經濟的高潮。為在全國范圍內開展有計劃的經濟建設,中財委于同年8月召開第一次全國計劃工作會議,討論編制了1951年計劃和三年奮斗目標。隨后,相繼擬定和頒發了《編制國民經濟計劃的辦法》 《關于國民經濟計劃編制暫行辦法》 《關于加強計劃工作大綱》 《關于編制五年計劃輪廓的方針》,規定國營企業主要以部門系統分配控制,地區要對中央主管部門分配的控制數字和計劃負責,還應編制本地一切國民經濟各部門、一切管理系統、一切經濟成分的計劃并報中央審批,地方企業的計劃由地區財委負責編制,中央人民政府批準中財委及中央各部、各大行政區的計劃,中央各部批準大行政區代管企業及直轄各管理部門的計劃,大行政區財委批準所屬省、市的計劃,并于1952年11月增設國家計劃委員會。與此同時,政務院也相繼作出了《關于1951年度財經收支系統劃分的決定》 《關于劃分中央與地方在財政經濟工作上管理職權的決定》,實行統一領導、分級負責的方針和三級管理制度,把一部分國營企業和財經業務劃撥給地方管理,各地中央直屬企業的政治工作由當地政府領導,并受當地政府的監督、指導和協助。至此,我國不僅設立了比較系統的計劃機構,而且確定了條塊結合的經濟管理形式和一系列方針政策,一種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初步形成。
學習蘇聯模式
1949年初,斯大林派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部長會議副主席米高揚來中國,聽取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關于未來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意見。毛澤東在談到恢復和發展生產問題時表示要向蘇聯學習。在毛澤東看來,國家建設這個課題,對我們來說是生疏的,但是可以學會的。有蘇聯走過的道路可資借鑒。為了進一步了解蘇聯經驗,并爭取蘇聯對新中國的援助,1949年劉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團赴蘇訪問,帶回部分蘇聯專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毛澤東于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出訪蘇聯,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學習蘇聯經驗進入實質性階段。回國后,毛澤東多次強調:蘇聯經濟文化及其他各項重要的建設經驗,將成為新中國建設的榜樣。直到1957年2月,盡管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暴露出了一些缺點和錯誤,毛澤東在講到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時仍然強調向蘇聯學習。他說:為了使我國變為工業國,我們必須認真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已經有四十年了,它的經驗對于我們是十分寶貴的。
隨著國民經濟的恢復,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即將開始,建立更廣泛的集中統一的計劃體制被提上了日程。1953年初,周恩來總理在全國政協一屆四次會議上提出,集中力量,克服困難,為超額完成1953年度計劃而奮斗,是我們貫穿全年的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顯然,黨和中央政府已經將注意力轉移到準備迎接有計劃的大規模的經濟建設上來,這更加強了建立集中統一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追求。以“一化三改”為主要內容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在某種意義上說正反映了這一追求。
從1953年開始,新中國開始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史稱“三大改造”。這是以國家工業化為直接目的的一次大規模運動,也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一次偉大實踐。毛澤東明確提出,中國社會主義改造“所走過的道路就是蘇聯走過的道路,這在我們是一點疑問也沒有的”。他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這篇有名的文章中指出,首先大家知道,我國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的生產水平,現在是很低的,而國家對于這些物資的需要卻是一年一年地增大,這是一個尖銳的矛盾。如何解決這一矛盾?毛澤東認為,只有通過農業合作化,才能使農業由畜力農具的小規模經營,躍進到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經營,從而解決高速發展的工業的原料和糧食問題。而完成國家工業化和農業技術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資金,其中有一個相當大的部分是要從農業方面積累起來的。此后,經過急風暴雨式的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把新民主主義時期的五種經濟成分變成了單一的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即建立了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這也就為計劃經濟體制奠定了經濟基礎。
同時,為推動國家工業化建設,新中國加強對經濟資源的計劃配置和管理。從1953年起,國家先后對糧油棉實行統購統銷,以后又把生豬、蛋品、烤煙等納入統購統銷范圍,商業也對主要輕工業產品實行定購包銷。這樣,直接計劃逐步擴展到整個社會生活。隨著“一五”計劃的執行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展開,中共中央相繼發出《關于建立與充實各級計劃機構的指示》,批準試行國家計委《關于編制經濟年度計劃暫行辦法》,使各級計劃機構和編制工作進一步加強,整個計劃經濟管理體制臻于成熟,并經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憲法確認,其第十五條規定:“國家用經濟計劃指導國民經濟的發展和改造,使生產力不斷提高,以改進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鞏固國家的獨立和安全。”這表明,計劃經濟體制已成為我國法定的經濟體制。
隨著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及統一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建立,集中統一的社會主義所有制結構和計劃管理體制就完全形成了。
新中國成立之初,建立集中統一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有其客觀必然性。在當時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經濟結構比較簡單的條件下,適當地強調集中統一,的確有利于把有限的資金、物力和技術力量集中起來,建立了一批為國家工業化所必需而過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礎工業。從1953年到1956年,全國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19.6%,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4.8%。這也說明,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形成有其內在的合理性。當然,這種傳統經濟模式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
反思蘇聯模式
經過第一個五年計劃,在實施第二個五年計劃的過程中,隨著蘇共二十大暴露出蘇聯模式的缺陷,中國向蘇聯學習社會主義建設的路徑開始發生很大的變化,開始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期間,毛澤東對照搬照抄蘇聯經驗的教條主義做法進行了批判。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澤東在杭州系統研讀了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并結合中國實際與黨內有關同志進行了討論。毛澤東批評說,蘇聯教科書脫離實際,有的觀點背離了馬克思主義。1960年1月,在《十年總結》一文中,毛澤東開宗明義地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國的經驗。但從1956年提出十大關系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這表明,從那時起黨就已經開始了對“蘇聯模式”的反思。遺憾的是,這種反思由于各種原因并未持續下去,更沒有形成新的制度安排。至“文化大革命”結束時,我國國民經濟已瀕臨崩潰邊緣:國有企業普遍缺乏活力,物資供應嚴重短缺;國家計劃高度集中,農、輕、重比例嚴重失衡;收入分配平均主義盛行,勞動者生產積極性嚴重受挫。這實際上標志著傳統經濟體制的終結。
病樹前頭萬木春。1978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由此拉開中國最具時代意義的改革開放大幕。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首次作出中國社會主義處于“初級階段”的科學判斷。1982年,黨的十二大第一次提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992年初,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回答了困擾人們多年的問題——“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鮮明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明確指出“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貧窮”“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這些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經典論述,突破了傳統社會主義理論的禁錮,解放了人們的思想,為中國大刀闊斧的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權威的理論支撐。
過去的4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立足中國實際,不斷推動理論的與時俱進,不斷創新中國的經濟制度范式。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第一次把這些具有偉大創新意義、鮮明中國特色的經濟制度成果,歸納提煉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構成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這不僅是中國式的政治經濟學的重大理論成果,而且也是中國經濟賴以持續穩定發展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