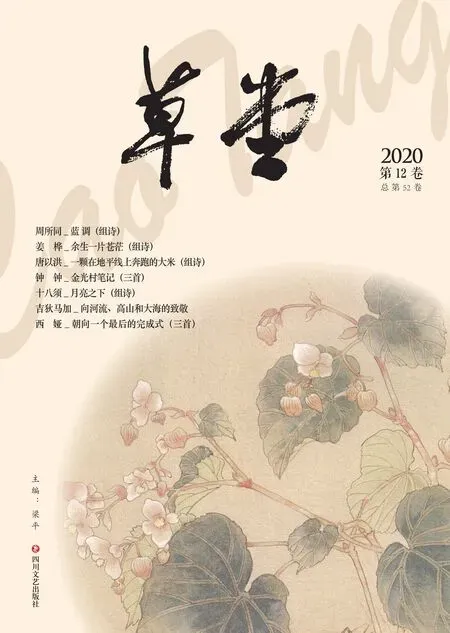大詩的復歸與人類的希望
◎邱華棟
大詩或曰長詩,一直是卓越的詩人追求的寫作巔峰。
我個人更喜歡大詩這個概念。長詩往往只是形容一首詩的長度,但大詩,則在概括一首詩內容的博大豐厚和體量的雄渾龐偉。我們很容易扳著指頭數出一些現代杰出詩人所寫下的大詩:
T.S.艾略特的《荒原》、奧克塔維奧.帕斯的《太陽石》、巴博羅·聶魯達的《大地上的居所》、馬雅可夫斯基的《穿褲子的云》、阿赫瑪托娃的《安魂曲》、龐德的《詩章》、沃爾科特的《奧梅羅斯》、卡贊扎基斯的《新奧德賽》、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 《佩特森》(四卷)、塞弗里斯的《畫眉鳥號》、埃利蒂斯的《理所當然》等,這些大詩,篇幅短的有數百行,長的則有數千行乃至上萬行。這些著名的大詩,在語言的精微性和復雜性上,在詩歌篇幅的長度、內容的厚度和表現的難度上,都有詩學意義上的絕佳呈現,是以語言為生命的詩人在文明層面上的最高表達。
上述這些大詩人所寫下的大詩,有的偏重于敘事,承繼人類史詩的原型故事元素,如卡贊扎基斯的《新奧德賽》,就是對遙遠的史詩《奧德賽》的當代回音;沃爾科特的《奧梅羅斯》也是這樣,它還有一個副題叫作“安德列斯群島:史詩片段”。威廉斯的《佩特森》更是以四卷的篇幅,詩性呈現美國一個小鎮的人類學意義上的史詩景觀,拓展了“史詩”在當代英語詩歌中的形式感和內涵。塞弗里斯的《畫眉鳥號》也是對希臘神話的應答和回聲,埃利蒂斯的《理所當然》更是在古希臘和古羅馬神話元素和史詩傳說中尋找到了現代意識的接口,帶給我們20世紀的最新詩意。
有的大詩長于抒情,如聶魯達《大地上的居所》,激情澎湃,氣勢恢宏,感情的力量如滔滔江河順流而下,將讀者裹挾其中,一覽無余。有的大詩文體十分復雜,如艾略特的《荒原》,它是敘事、抒情、寓言、哲思的結合變體,呈現出英語現代詩概括人類境況的豐富性和可能性。有的大詩,具有高度的形式感,如馬雅可夫斯基的《穿褲子的云》,階梯詩的節奏和造型,將俄語詩歌帶入到一個全新的境界。
有的大詩,有著極其豐厚的文化人類學、神話學的內涵和背景,如帕斯的《太陽石》,是建立在阿茲特克文明和神話傳說之上的當代表達,貫通古今,勾連起西班牙語現代詩古老的文明精神的源流,開啟了一代詩風。有的則深入到當代人的精神處境中,描繪一個時代的精神圖譜,如阿赫瑪托娃的 《安魂曲》,將俄羅斯人沉郁的精神境況和個人悲劇體驗結合在一起,成為一個時代的靈魂畫像。
中國新詩百年史中,也有一些詩人嘗試寫下了長詩或大詩。我們比較熟悉的當代詩人的作品,有海子的《太陽·七部書》,可惜,全稿并未完成,海子就身死了。臺灣詩人洛夫的《石室之死亡》和《漂木》可以說是他的大詩代表作。因此,仔細梳理總結漢語百年新詩史中的大詩或長詩的成敗經驗,也是很迫切的事情。因為大詩的寫作,是一個詩人寫到一定時候的寫作高度的體現,是詩人詩藝的最高水平。可能有的詩人一輩子都寫不出一首大詩,就是由于其氣勢、氣魄不足夠,生命體驗和知識準備不充分的原因。
當代詩人中,吉狄馬加近年來接連寫下多部長詩,如他的《雪豹》《不朽者》《遲到的挽歌》《獻給媽媽的十四行詩》《大河》《致馬雅可夫斯基》《獻給曼德拉》等,有近十部之多,構造出他宏偉的精神世界,呈現出別開生面的大詩氣象。大詩,往往是一個詩人一生凝思,并通過相當大的篇幅,來呈現生命狀態和語言瞬間碰撞出的火山噴發般的巔峰表現,有時候,大詩杰作的出現,甚至是靈感乍現、失不再來的。
《裂開的星球》是吉狄馬加的一首近作,是一首可遇不可求的大詩。它發表在《十月》2020年第4 期上。這首詩有四百多行,主題深廣,切近當下全球新冠疫情或后疫情的世界境遇,這是中國詩人最為難能可貴之處,就是對當代世界境遇問題的回應。在全詩中,他的深切關懷和不斷追問,帶給了我們對人類命運的思索;這首詩氣勢恢宏,意象繁復,宛如長練當空舞,又如滔滔江河一往無前,讀下來,喚起了我當年閱讀奧克塔維奧·帕斯的長詩《太陽石》、聶魯達的長詩《馬楚比楚峰》的新奇感和恢宏博大感。這在我閱讀漢語詩歌的經驗中,是非常少見的。
吉狄馬加這首大詩的出現,顯示了他遠接人類各民族史詩的偉大傳統,近承20世紀以來現代詩歌的大詩傳統,既是史詩的當代變體,也是大詩文體在漢語詩歌中的強勁再生,是中國新詩百年史中出現的令人驚喜的收獲。
閱讀任何一個詩人集合了他大半生生命體驗和文化經驗所寫出來的一首大詩,我們都應該抱著敬畏的心情來對待,凈手、靜心是必須的。大詩或曰長詩的寫作非常耗神。我還記得,我上大學的時候寫過一首二百多行的長詩,當我寫下了最后一句的時候,我已經耗盡了精氣神,幾乎要暈倒了。大詩的寫作過程中,詩人的精神處在高度緊張的狀態里,要消耗巨大的能量和氧氣,是一個人的生命體能的耗散,非常費神。而詩人是語言的煉金術士,是語言的打鐵匠。對于詩人來說,每一行詩、每一個字,都是殫精竭慮的,要反復錘打的,是非常用心用力的。因此,大詩并不好寫。相對于長篇小說的敘述松散度來說,長詩或曰大詩,其寫作的質量就猶如中子星的密度,在極小的篇幅和體積之內有著極大的質量,仿佛一立方厘米的體積,就能洞穿地球的表面。
面對吉狄馬加的大詩《裂開的星球》,首先,我們可以從這首詩的形式和節奏上來感受它、接近它。每一首詩,都有自己的語調和呼吸節奏,詩歌的調性帶有音樂性,這種音樂性是語言形成的。語言構成了音符的功能,幫助我們閱讀和切分整部長詩的內在構成。我讀《裂開的星球》,就找到了閱讀這首詩的呼吸節奏。
按照我對這首詩所自然形成的山脈起伏般的節奏感,我把它分成七個部分,也就是七段。這是我自己閱讀這首大詩的自然分段,也可能是這首詩的潛在結構。需要說明的是,吉狄馬加并未加以分段,我是依照我自己的閱讀體驗,對內容本身形成的節奏感所劃分。這就像是一條大河的不同的河段,共同構成了一整條河流一樣。大河上下,有發端寧靜如小河潺潺的段落,有寬闊平靜的深河河段,有激流跳蕩的險段,也有蜿蜒曲折、回環往復的河段,最后,又收到一點之上,奔流如海。這些河段成為首尾相連的大河結構,成為一首詩九曲回腸的豐富景觀。
那么,在《裂開的星球》這首大詩中,我看到不同語言中詩歌形式的集大成。有漢語律詩、英語十四行詩、阿拉伯懸詩、東歐合組歌、希臘箴言體、日本漢俳、波斯柔巴依、彝族神話史詩等多種語言中的詩歌形式的內化和外化,變形和重新組合,在這首長詩中都有呈現。這是吉狄馬加對世界詩歌的多年學習,將世界詩歌的營養,融化到自己的語言和血液里的結果。
我所分段的這首大詩的第一段,是全詩的前十四行。可以把這第一段看作是一首十四行詩。起首四句是:
是這個星球創造了我們
還是我們改變了這個星球?
哦,老虎!波浪起伏的鎧甲
流淌著數字的光。唯一的意志。
這四行詩也可以是四言絕句,也可以是一首柔巴依,也可以是箴言體,在全詩的結尾再度重復了一遍,完全一樣,成為首尾相連、循環往復的生生不息的結構。這是我們理解這首大詩的關鍵。
在第一段的十四行詩句中,詩人用彝族的古典創始神話史詩《查姆》中對地球的形容,拉開了全詩的序幕。這使得這首詩具有了神話史詩的背景深度。在彝族史詩《查姆》中,人所居住的大地是一個球體,在這個巨大的球體上,四個方位,分別有四只老虎在不斷走動,扯動了地球這個球體并使之轉動,使得地球永不停息地旋轉著,生生滅滅。這是彝族人對老虎的古老崇拜。在他們的創世史詩《查姆》中,太陽是老虎的眼睛,老虎的骨骼化身為大地和群山,老虎身上的毛發化為森林和草地,身上的斑紋演化為海洋,腸子變成了江河,毛發變成了植被。因此,地球是老虎幻化而成的。彝族人如此形容人類所居住的地球,顯示了他們先天就具有和自然相通的理念,尊敬大自然,崇拜大自然。
吉狄馬加對當代世界的真切關懷,在這首大詩的第一段十四行里,鮮明地點出了人類的現實處境。看吧,在不斷旋轉的球體之上,人類此刻的命運,正在被創世時代的老虎的雙眼所注視,人類被善惡纏身,被病毒襲擊,處于緊張的狀態中。由此,這首大詩展開了它波瀾壯闊的呈現,如同金黃的老虎的斑紋那樣變幻多端,耀眼無比,同時,具有語言的高蹈氣勢。這第一段的十四行,宛如智者站在高處審視,并像宣敘調那樣高聲頌唱,引導出全詩的滔滔江河。
我把這首大詩的第二段,劃分為約五十一行。從第十五行開始,一直到“但請相信,我會終其一生去捍衛真正的人權/而個體的權利更是需要保護的最神圣的部分”這兩句為止。在第二段,我們可以看到,詩句明顯變長了,就像是大河起源,從高原奔涌到一片高地海子的寬闊水面,像是從三江源抵達了青海湖一般。這一段,是對人類所處的新冠肺炎所導致的當下境況的描述,是病毒襲擊人類,不斷在一個個人類的居所、空間掠過的全景描述,是人類對病毒來襲的對抗性反映的描述,是對當下疫情后可能迎來的一個分歧和分裂的時代的想象性描述。
在這一段中,彝族古老的創世神話史詩《勒俄特伊》中的觀念出場。在這首史詩中,曾說到人類創世的時候,有六種流血的動物,六種無血的植物,一共是十二種動物和植物,叫作“雪族”,構成了地球世界的基本生物。因此,人類和其他動物、植物都是有血緣關系的親兄弟。從這種古老原始的彝族創世神話中對地球上動物和植物之間兄弟關系的基本描述,到現今全球化緊密聯系的時代,這樣的廣闊的聯系,讓我們看到了古老的神話并未失效,甚至還有著鮮明的當代意義。
當前的世界,人類面臨著核威脅、病毒威脅,全球化經濟、文化發展極度不平衡、安全事務得到挑戰、文化差異需要撫平,人類更需要通力合作,因為人類是一個命運共同體。我們曾看到在聶魯達、帕斯和馬雅可夫斯基當年寫下的大詩中有著這樣的關切,如今,在吉狄馬加的筆下,這樣的高度再度出現了。不同的是,吉狄馬加站在了新的歷史時間的節點上,站在新時代的維度上,對人類的共同境遇和命運進行了全方位的描述。這一段,是起首的宣敘調和十四行詩之后的鋪排段落,是深化全詩主題的領銜段落。
全詩的第三大段,我是從“在此時,人類只有攜手合作/才能跨過這道最黑暗的峽谷”開始算起。這一段起承轉合,進入到人類如何攜手合作,以及為什么需要攜手合作,攜手合作面臨了什么樣的困難,哪些困難,全部做了詩意的呈現。這一節的詩行約有三十八行,有兩行一段的,也有一行一段,四行一段,更有七行一段,呈現了呼吸的節奏,對應人類詩歌史上各種表現形式的韻律、節奏和音節。我們能夠看到吉狄馬加高超的詩藝表現,他能將各種節奏和形式在這一段中融合起來。
我們看到,百年以來,人類在追求現代性過程中的很多面孔,本雅明、茨威格、但丁、塞萬提斯、陶里亞蒂、帕索里尼、葛蘭西、胡安·魯爾福、巴列霍這些文化名人、巨匠紛紛出場,地理學意義上的地球景觀緩緩拉開了幕布,從幼發拉底河、恒河、密西西比河到黃河,從歐洲到亞洲再到拉丁美洲,無數作家、詩人在百年大歷史中,在人類追求現代性的艱難旅程中,對所處境遇的疾呼和承擔,這一段得到了充分展現。吉狄馬加認為,人類必須要攜起手來,必須要互相溝通,必須要面對共同的困難,因為絕望和希望并存,因為“這里沒有訣竅,你的詞根是206 塊發白的骨頭”,也就是人本身,是最大的希望所在。人文主義精神是維系人類命運的絕佳骨骼,我們必須回到對生命價值的肯定,對人自身骨骼的構成——206 塊骨頭這一全人類生命個體基本骨骼結構上,來看待我們現實的處境和未來的走向。
全詩的第大四段,是整部大詩的高潮部分,從“哦!文明與進步。發展或倒退。加法和減法。——這是一個裂開的星球!”開始,以每一小段兩行長句子,一連三十三個“在這里”振聾發聵,氣勢磅礴。三十三行起首一致的詩行,整齊而恢宏,就像是連珠大炮一般,呈現出跌宕起伏、層層遞進的風貌,讓我們目不暇接,讓我們在閱讀的詞語閃光的擊打和喧嘩的聽覺中,體會到了詩歌本身所可能達到的語言風暴。第四段結束,整首長詩或者說這首大詩,在篇幅上接近一半。
隨著詩行的鋪排,我們看到了這首大詩不斷給我們展現出作為命運共同體的人類境況。在這里,就是在這個分裂的星球上,世界并不是平的:
不僅有高山峽谷,高原平原,還有暗礁、島嶼和海溝,國際貨幣體系、巴西亞馬孫熱帶叢林、手機上的殺人游戲、吉卜賽人和貝都因人新的生活方式、幾內亞狒狒、人工智能、英國脫歐、南極冰川融化、海豚自殺、“鷹隼的眼淚就是天空的蛋”、糧食危機、馬爾薩斯人口理論、紐約曼哈頓的紅綠燈、玻利維亞牧羊人的凝視、俄羅斯人的伏特加、阿桑奇與維基解密、阿富汗貧民窟的爆炸、加泰羅尼亞人的公投、愛爾蘭共和軍和巴斯克分離主義活動、摩西十誡、中國的改革開放、瓦格拉和甘地的奮斗、世界銀行與耶穌、社會主義與勞工福利、全球移民、希臘詩人里索斯在監獄里寫詩、9·11 時間、虛擬空間是實在界的面龐……全部紛紛涌現,同時空并置。在這個裂開的星球上,三十三個“在這里”的排比句,滔滔不絕,連綿不斷。這一節一共七十多行詩句,一瀉千里,將我們面對著的、我們身處其中的這個分裂的星球的狀況,做了精微描述,有詩人吉狄馬加對全球局勢的憂慮和關切,更有他對中華文明的價值肯定和贊許,于是:
哦!裂開的星球,你是不是看見了那黃金一般的老虎在轉動你的身體,
看見了它們隱沒于蒼穹的黎明和黃昏,每一次呼吸都吹拂著時間之上那液態的光。
這是救贖自己的時候了,不能再有差錯,因為失誤將意味著最后的毀滅。
我劃分的這首大詩的第五段,是以四大段、一百三十六行的規模,逐漸增加著詩歌在結構上的重量,在語調上的加速度,在質量上的拋射感,在語言密度上的擠壓和情感上的最終釋放,這一段讀起來讓人喘氣,讓人目不暇接,讓人頭暈目眩。比如,以三十九個連續的判斷句“這是——”來對人類境況進行清晰的分析研判,最終,“哦,人類!只有一次機會,抓住馬蹄鐵”。
馬蹄鐵是讓馬蹄不再受損、減少磨損的保護用具。人類也需要保護自己的馬蹄鐵,這就像是某種難得的機會一樣,人類并沒有更多的時間窗口能夠抓住保護自己的馬蹄鐵,只有一次機會,就看你能不能抓住了。
第六大段,是這首大詩的收束部分。在第四段、第五段大量的鋪排、雄鷹高飛般的鋪陳之后,我們盡享這首詩歌本身的語言的絢麗多姿,品賞搖曳無窮的詞語盛宴和無上的思辨之光。我感覺詩人在寫這些句子的時候,一定是瞬間生成的,是他生命經驗和語言的瞬間相遇,是不可重復,失不再來的。這就是詩歌創作的最高秘密,詩人有著天籟般的語言,有著神秘的使命,能夠將全部的生命經驗瞬間和語言相撞產生的火花捕捉,加以定型。
全詩的第六段,以“是這個星球創造了我們/還是我們改變了這個星球?”作為這一節的起首兩句,對全詩的主題進一步深化,這一節中,彝族創世史詩中出現的女神普嫫列依出現了,她有一根縫合受傷的人頭骨的針和白色的羊毛線,詩人要求把它借給他,借以縫合裂開的星球。
第六大段八十多行,分為兩大節,將這個星球的分裂和彌合的可能再度進行了展示,并導向了真正的希望,那是人類更大的希望:
“人類還會活著,善和惡都將隨行,人與自身的斗爭不會停止/時間的入口沒有明顯的提示,人類你要大膽而又加倍地小心。”
《裂開的星球》這首大詩的第七段,是最后的結尾,也是重新的開始,和第一段中的起首四句,是一樣的:
“是這個星球創造了我們/還是我們改變這個星球?/哦,老虎!波浪起伏的鎧甲/流淌著數字的光。唯一的意志。”
于是,經過了峰回路轉、千回百轉和波浪起伏,經過了豹子斑紋般絢麗的語言鋪排和展示,在全詩收尾的這四行詩與起首的四行詩對應起來,形成了首尾相連、四百行的大詩成為一個循環的空間結構,并將主題再度強化,讓我們看到了世界最終依舊在轉動,那虎皮豹皮波浪起伏般的斑紋,流淌著宇宙內在規律的意志。這樣的結構,也就是吉狄馬加在向帕斯的《太陽石》致敬,帕斯以起首和結尾的六句完全相同,形成了拉美文化史詩循環的時間和空間,而吉狄馬加以四句首尾對應,體現出這首大詩的從容和成熟。
《裂開的星球》這首大詩經得起反復閱讀,也需要進行更多的闡釋。這其中,注釋也很必要。其包含的大量文化信息,以語言密碼的方式高強度呈現,是一首可以不斷進行解讀的大詩。這首詩以全景觀呈現、密集豐沛的意象、熱切關切當下人類共同命運的視野,重申生命價值,展現中華文化內核,以黃金凝練般的語言,將心靈火焰和巖漿般的熱情與古老史詩、神話相呼應,并內在地運用了人類多種語言中的詩歌形式,融匯構造成一首充滿了人類呼喚未來希望的大詩,體現出繼承和復活大詩傳統的格局,為我們帶來了漢語詩歌的新景象,可以說是一首罕與匹敵的、可遇不可求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