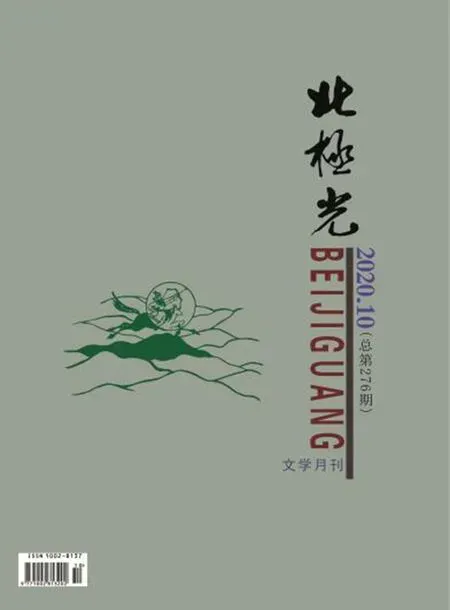它 們
螞 蟻
我不喜歡螞蟻,當然,也說不上厭惡。在村子里,螞蟻實在太普遍了。小,多,不嘈不鬧。因為小,所以不好玩;因為多,所以不稀奇。而且,它們就那樣安安靜靜地走路,安安靜靜地覓食,安安靜靜地過自個的日子。又有誰會去在意、打擾那些弱小而又安靜的物什呢?像落在水面的那些落葉,像村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那些人,像生活中那些偶爾長出來卻又不影響生活的小傷感。
但我相信,在我更小的時候,比如還在地上爬,比如才學會走路,我肯定打擾過螞蟻的生活,甚至吃過不止一只的螞蟻。對弱小者的傷害,更多的來自另一類的弱小。
我后來看過村里那些幼兒們的行為,先在草席上爬,然后就越出了草席的范圍,在骯臟的地上翻滾前行,隨便抓到什么就往嘴里塞。我小的時候,必定和他們一樣。那時,兄弟姐妹們多,而父母已經為生計,為一日三餐忙得焦頭爛額,他們實在無暇在我們的身上投下更多的關注。沙子、石塊、螞蟻、雞屎、樹葉……這些大地上細小的東西,成了我們最好的玩具。我差點就把撿在手上的一小粒雞屎放進嘴里。這是長大后母親告訴我的。我驚詫過后就是平靜,我甚至想,就算當時吃下去,又會有什么壞處呢?我肯定分辯不出香臭和好壞。更重要的,憑著當年旺盛的生命力,一粒小小的雞屎,又怎么能夠阻擋我生長的力量呢?但我肯定吃過螞蟻。就那樣地趴著,螞蟻是唯一可以看到的會動、速度很慢的黑點,它的到來天然地引起我的興趣,伸出手指捏住它,放在眼前細細地端詳,任它在手心爬行,或者就干脆把它塞進嘴里,這也是那個時候村里每個孩子成長的必然經歷。
螞蟻是每個鄉村孩子最早見識的動物,也是每一個鄉村家庭出現最多的動物。實在無法說清它們安放的家究竟在哪里。屋頂、墻縫、床下、柜腳、門后、水缸邊、地板和墻壁交接處,一堆柴火的中間……一小塊地瓜皮掉在地上,很快,就可以看到上面密集的黑黑的螞蟻,還有一隊又一隊的、長長的螞蟻正在趕往目的地的路上。和一塊即使很小的地瓜皮相比,螞蟻微小得可以忽略不計。但一只只微小的螞蟻集結在一起,它們就可以氣昂昂地把那塊地瓜皮搬回家里。千萬不要小看每一個弱小者的力量,當他們團結起來,他們就能夠移山倒海。
螞蟻傾巢而出的場景并不常見,除了災難的降臨,比如,一場暴雨。巷子里的積水還在一點一點順著墻壁往上爬,低處那些人家屋子里的短凳成了小船,這個時候,一枚水中的樹葉成了螞蟻的救生艇,螞蟻們堆砌在葉子上,小山一般。樹葉的四周,還飄浮著成片的螞蟻,密密麻麻的,像撒落在地上的炒熟的黑芝麻。水在緩緩地流,也在緩緩地漲,螞蟻在緩緩地多,拋下的尸體難以計數。雨停了,水退了,太陽出來了,遭受浩劫的螞蟻們,又不緊不慢地出來了。
螞蟻太多,給生活帶來了許多的麻煩,雖然不算大,但讓人無奈地生出煩惱。比如,放在桌上的剩飯,一個晚上就爬滿螞蟻,驅趕干凈它們實在困難,倒掉又太可惜了。那年頭,村子里的人都在為填飽肚子而苦苦掙扎。或者,早上起來,水缸被螞蟻攻陷了。那些螞蟻占據了缸壁、水面,有的還沉到缸底去了。村里本就缺水,全村人就共用一口水井,為了汲滿一缸的水,有時要忙乎大半個晚上。對螞蟻的積怨厚了,就有人想消滅它們。村里一個五保戶,平日家里也懶得打掃,就像垃圾堆一樣,黑乎乎的,還有一股怪味。村里沒有一個人愿意上他家去,他也不喜歡別人去。他家的螞蟻特別多,而且特別大,黑色的。他發現螞蟻在屋檐下有一個窩,就把稻草扎在竹竿上,點燃去燒。螞蟻窩燒掉了,他家的那棟茅草房也著火了,就剩下火燎過后的暗色和一個敞開的屋頂。
村里人就私下里嘀咕他,說怎么樣也不能去燒螞蟻,說他也太狠了。倒是太婆,她去世后村里人還總是念叨她,說她善良,說她心腸好。
我不知道太婆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她多少歲,也說不清我和她之間究竟是什么樣的輩份。反正,村里的人都叫她太婆,她就笑吟吟地、脆脆地回答,后來,就笑著點點頭。她一個人孤單地活著,她的兒子早已去世,孫子也不在了,曾孫好像外出,曾孫的孩子跟著父母到外面去了。她家里的螞蟻也多,地上、米缸、柜子、小圓桌,就是裝水的桶,上面也是一層螞蟻。每次嬸嬸們輪著去幫她打掃衛生,總說她家的螞蟻可以裝一輛板車。老人總是笑咪咪的,臉上滿是溝溝坎坎,但極為潔凈。老人去世時沒人知道,等發現時已過了三天。她穿著干凈的衣服,安靜地躺著,那些螞蟻,在她的身邊圍成了一個又一個的圈,卻沒有一只爬到她的身上。
蝸 牛
那個時候,我并不知道它們叫蝸牛。我以為就是一種螺,像田螺,或者海里的那些螺。因為,它們都有一個硬硬的殼。我們村就在海邊,但村里的人不是漁民。漁民是鎮里的人,他們不用種田,他們的米是從鎮里的糧管所買的。我們村里的人都是農民,天氣熱了才下海捕魚。船是小船,沒帆,就四把槳劃呀劃呀,一張網撒呀撈呀。船小,不敢跑遠,捕撈的范圍都在近海。那些網到的魚,也不像鎮里的漁民那樣,全都賣給水產站,而是挑回村里,按每家每戶勞動力掙的工分進行分配。我也總到海里去,不用上學的時候,或者,整個暑假都泡在海里。礁石上的那些螺真多,還有鮑魚、生蠔、螃蟹什么的,每次,我都能夠扒拉到一桶,提著回家當菜。螺撿得多了,我就把蝸牛也當成了螺。
雨下完了,巷里的水慢慢地退,墻根露出來了,用來裝豬糞豬尿的那些坑也露出來了,一只一只的蝸牛就挪出來了。小的蝸牛像掛在墻壁上的沙粒,大的像裸露出來的石子。
我們村里建房子和別的地方不同,不是用磚或者長條形的石板壘起來,而是用石灰、沙、黃泥和石子夯的。石灰是想建房的人自己去海里撈貝殼,然后自己燒出來。反正離海近,海里的貝殼多,只是把貝殼挑回來實在是苦累活。我家建房子時,跟著父親去,就兩簸箕,我就再也不想去了。那時,覺得從村子到海邊的路真長,怎么也走不完。那些石子怎么也搗不碎,就那樣被黃泥裹著,夯成墻,外面再刷一層石灰,頂上鋪一層稻草,房子就建好了。那些年,除了糾纏不休的饑餓,我倒從未覺得日子的貧窮。村里的孩子們都是一樣的,穿著縫縫補補的衣服,一直吃不飽。村里一年四季會刮七八次臺風。每次臺風來了,就把準備好的木板、石頭壓在屋頂上,再用繩子捆綁好。盡管家家都如臨大敵,臺風大了,那草還是被卷了。天晴了,還得再鋪再補,一年又一年,層上的稻草早就十層了。屋頂這樣,墻也好不了多少。雨淋過,風刮過,日頭曬過,那層石灰一兩年也就開裂了。墻就開始脫皮,那些沙和石子就露出來了。
蝸牛們在那邊安安靜靜地活著,我在不管不顧地和伙伴們玩水仗。每次下雨,我們都會這樣。雨小下來了,我們就跑出家,匯聚到積水多的那條巷子里。如果是刮臺風,風后的那場大雨小了,我們就挎著籃子跑到村里中間的那棵大榕樹下,或者村后的竹林里,或者別人家的番石榴、龍眼樹下面,在這些地方,要不就撿到許多被臺風吹打得只能伏在地上的麻雀,要不就撿到平日我們只能偷的果子。麻雀用尖尖的石塊剖開肚子,掏出內臟,用火烤,油滋滋的香。番石榴香,龍眼甜,柚子澀嘴。
我穿一張后面有個洞的小褲衩,那是我哥哥穿不了給我的。我的身上全是水。頭發濕了,光光的身子濕了,褲衩也濕了。因為還沒停的雨,因為別人潑在我身上的水。水黃黃的,有一股味道。那味道像我們平時用尿拌出來的黃泥巴那樣腥臊。
我習慣了這樣的水,和水的這種味道。在我們村子里,沒有一個孩子會對雨后的這些東西和味道感到稀奇。和我一起玩水的,幾乎每個早上,我都會巷子里和他們相遇。從巷子的這頭或者那邊轉出來,在巷子的中間擦肩而過,每個人的左手是一個簸箕,右手是一把裝了木棍的鏟。我們都在為讓簸箕裝滿豬糞牛糞而穿街過巷。
巷子里的水越來越淺,我已經沒有辦法彎下腰用雙手朝別人撩水了。我用一只腳撐住身子,用另一只腳的腳底踢水。長大以后,我才知道這個姿勢叫金雞獨立。那時,我只想讓自己站穩,我只想能夠朝別人撩起更多的水。腳就那樣不停地踢,向前,向后,向左,向右。每一個人都是敵人,每一個人都是朋友,直至,有人認輸,或者,巷子里的水已經濺不起水花,游戲才會停下來。
我在撩水的時候,腳底碰到了一個硬硬的東西,我以為就是小石子,等到巷子里的地都快露出來,我才留意到,那是一只田螺。這巷子里怎么會有田螺呢?我撿起它,正覺得奇怪,就看到那只螺伸出了兩只角,而且,角上好像長了牙齒。我被嚇到了,這是什么東西?怎么還是活的?怎么還有角?我把它扔在地上,然后,迅速地往后退,靠著墻壁。
它在地上翻了兩個滾,然后停住。殼的那個敞口朝向天。雨不下了,太陽就出來了,晃晃的光落在它的身上。它的角伸出來,短短的,好像抖了抖。我用臟兮兮的手揉了揉眼晴,它的角又往前長了一點,角上還有分叉,然后,慢慢地縮回去,不再動。我走上前,在它的旁邊,用腳趾頭碰了碰它。它不理我。我蹲下去,用兩個手指捏著它,它還是不理我。我舉起手,正想將它摔向墻壁,就聽到有人大聲地說:“快看,蝸牛!”
我的手停在那里,轉頭,說話的人已靠近我。“這是蝸牛,能吃的。”他一邊說一邊把手伸到我面前。我知道他的意思,但我沒有把手中的東西交給他。
能吃的東西,我為什么要給他?
他就站在我的身邊,兩只眼燈籠一樣死死盯著我的手,喉嚨一伸一縮的。我把手指往回曲,那只蝸牛落在我的手心。我迅疾地把掌變成拳,然后,垂下手。他的目光跟著我的手移動,風箏一樣。
為什么叫蝸牛?我問。
給我。他把手伸到我的面前。
像螺,又不像牛,為什么就叫蝸牛?我又問。我已經知道這東西可以填肚子。以前我怎么就不知道呢?村子里究竟還有多少可以吃而我又從來沒聽過的東西?為了填飽肚子,我偷過生產隊準備做肥料的黃豆,那些黃豆沒一粒是黃色的,都被蟲子咬過。我把別人剛埋進地里的花生粒挖出來。村里能吃的東西,那些植物,那些種子,那些爬行的動物,我都吃過。我以為再也找到新的東西,沒想到,還有這種叫蝸牛的“螺”。他把手伸到我的面前,那只手說不清什么顏色。雙眼更大了,上眼皮都快被撐到眉毛上去了。嘴巴張開,口水從嘴角溢出來,順著臉頰往下滴。他把黃黃的舌頭伸出來,貼著上嘴唇,從左到右慢慢地溜。在鼻子下邊,停,舌頭往上伸,碰到涎下來的鼻涕,碰了碰,用力地吸了吸鼻子,舌頭滑過去,縮回嘴里。吸進去的那些鼻涕淌出來,灰色,蟲子一樣。
我看著他,沒有動。給,還是不給?我在心里盤算著,畢竟,這是一塊肉。我不知道吃起來怎么樣,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燒熟它,但它是肉,可以吃的肉。早上,家里沒煮飯,不是父母忙,或者懶,而是沒有什么可煮。生產隊已經好久好久沒有分地瓜了。去年秋收分的稻谷,過了個年就剩下不多了,田里的禾苗在綠著,還沒到抽穗的時候。全家的地瓜就裝在簸箕里,一個簸箕都裝不滿,還是過年前分的。那些地瓜被霜凍過,皮都黑了,煮不爛,吃起來總是脆脆的,好像生的,還有一股氨水的味道。就是這些,也不能敞開肚皮吃,也吃不飽。我個子小,但我飯量大,一頓最多吃到九碗飯,那是親戚家辦喜事,父親帶我去。吃的有些撐,別人都看著我,但我才不理,我不會不好意思。我家人多,但勞動力弱,分到的地瓜和稻谷都不多。開春以后,一日三餐變成了二餐,又變成一餐。就是一餐,我也吃不飽。像中午,那舀到碗里的粥,煮爛了的米粒剛好把碗底鋪平。以前,我們會在田頭地尾、溝畔荒地整一些自留地,種些地瓜什么的。去年,大隊說要“割資本主義的尾巴”,說“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那些自留地不能種了。我的肚子更餓了,餓得連泥巴都能聞到香味。
他舉起手,我緊張地看著他。他朝我咧了咧嘴,用手臂抹了抹鼻子。陽光下,他的手臂亮了。他又把手臂靠近嘴巴,伸出舌頭,舔了舔。黑乎乎的手臂,多了一條潔白。我忍不住,就笑了。
可能因為我的笑,他將手伸到我面前,說,給我,我餓。這話剛說完,他的肚子“咕咕咕”地叫。
我也餓。我看著他,說。我還從來沒吃過蝸牛,肉這么多。
給我!他的聲音又硬起來。
我沒有說話。我在想,我應該怎么辦。我是打不過他的。我和他打過架,以前贏他的,去年開始,每次他都能壓在我身上。我哥哥和我堂哥幫過我,他的兄弟更多。在我們村子里,一個人和另一個人打架,最后都變成一群人對著另一群人。兄弟多的真好,怎么也不會被人欺負。
我的沉默像一堵墻。他撞在墻上,然后,他往向退。我知道,他要動手了。每次和別人打架,包括我,他都這樣,退后幾步,趁別人沒注意的時候像一頭發瘋的牛,伸著頭往前沖。等人反應過來,已經被他頂在地上,他就撲上去。我沒有動,我知道這個時候是跑不掉的。我就看著他。他站在巷子的那一邊,靠著濕漉漉的墻壁,身子微微往下彎,像一把松了弦的弓,右腳邁出半步,腳尖著地。
我們就那樣安靜地相互盯著,大眼對大眼。圍觀的伙伴們零零散散地站在四周,沒有人說話。他們不像過去那樣起哄,當然,他們也不會勸架。平時,遇到兩只公雞打架,他們也會熱鬧老半天。他們也可以追著兩條交配的狗穿過一條又一條的巷子。這一刻,他們的臉上都紅紅的,眼睛亮亮的,比我們激動,興奮。這里沒有我的兄弟,不會有人幫我,也不會有人幫他。巷子里靜靜的,蒼蠅也收斂了翅膀,沒有風,太陽白白地亮著。他的影子貼在墻上,我的頭發印在他癟下去的肚皮上。
我知道他一定會沖向我,他想把我撞倒,壓在我的身上,強行掰開我的手,奪走我緊緊攥在手里的蝸牛。為了這一塊肉,我一定要贏他。
我的左手握著蝸牛,右手攥成拳頭,我的拳頭要擊在他的頭上。我就等著他的沖鋒。
他站直了,右手收回去,和左腳并排,像一個士兵一樣立正。我松了一口氣,松開了拳頭。有人開始吆喝,有人嘻嘻哈哈地笑了。就在這一剎那,他突然向我沖過來了。
我迅速地往一邊躲。多年以后,每每想起這一幕,我總是不明白,像豬那么笨拙的我,怎么能變得猴子一樣敏捷。就那樣,我側過身子,往身后跳。
“嘭”的一聲悶響,他的頭撞在墻上,一些沙子悉悉窣窣地落下來。他頂著墻,沒說話,一動也不動,然后,一個人,慢慢地,歪歪扭扭地倒下去,一屁股坐在濕濕的巷子里。
那些喧嘩的聲音一下子喑啞、消失,像落在水中的石子。我呆了。他們也呆了。所有的目光都落在他的身上。他抬起一只手捂在頭頂上,另一只手伸向我。一只腳曲著,一只腳用力地蹬著地。
我走向他,猶豫著,把手中的蝸牛遞給他。他看著我,嘴角歪了歪,把蝸牛放在泥地上,捂住頭頂的手伸向旁邊,抓起一個石塊,狠狠地砸向蝸牛。蝸牛的肉灰黑灰黑地攤在地上,像搗爛的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