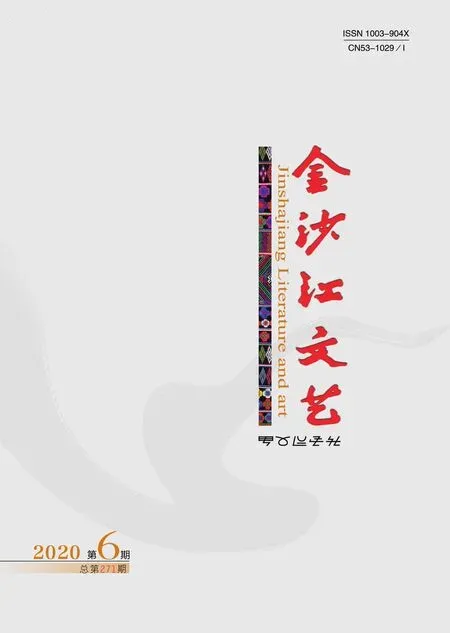小說是一個民族的秘史
——讀李學智《達布的金山》
《達布的金山》是一部洋溢著濃郁的彝族氣息的作品。這無疑是一個有情有義、天性愛美、敬惜人間生活的民族。
姑娘房,是老黑山的古老習俗。“這間姑娘房是樓房,樓上樓下各有十幾張床。樓下供男青年住宿,樓上供女青年住宿。未婚男青年來串姑娘房,夜深了自然按規矩住宿,誰也不會亂來。”農歷六月二十四的火把節,是老黑山最隆重的節日。“人們相約在火把梁子,殺雞宰羊,唱歌跳舞,通宵達旦地圍著篝火狂歡,談情說愛、賽馬斗牛等等。好飲的一醉就抖落了半年的辛勞,喜唱的一吼就趕走了一載的寂寞。”火把節的熱鬧由此可見。在老黑山彝族村寨里,臘月三是開年門,整個正月都在過年。過年不僅僅是人,山神過年祖宗過年。和人一樣辛苦的狗、牛、馬也要過年。人要先給它們吃最好的食物,人才能吃飯。然而此中彝族氣息最濃烈的一筆當屬關于畢摩作畢的書寫。
畢摩是怎樣的一群人?“畢摩在彝族同胞的心目中,是大知識分子,要熟知經文典籍,擅長作畢,也就是做法事,能夠主持祭祀、行醫占卜,掌管神權,把握文化,溝通神鬼,指導人事,在彝族同胞生產生活中發揮好畢摩的重要作用。”他是巫師,又是醫生,還是知識分子。小說看似給畢摩的身份與作用給出概念與定義,但因為身份與作用的多重,又顯得含混。總之,在彝族人的生活中,他是無所不能的,他是不可或缺的。達布就是畢摩,他父親吉達也是畢摩。達布的父親吉達去世時,畢摩在作畢儀式上主祭的誦經、副祭主持的各種儀式,是小說中最先著筆的書寫。作畢是彝族人日常生活中的一景。達布作畢讓商榮死去的家人能夠入土為安,作畢為諾召嬸嬸驅走身上的鬼邪,作畢減少古舒心中的罪惡感,作畢告知神靈惹伙從此與畢摩這個行當無關,作畢為安李云秀送靈歸祖,作畢為盟誓和祭祖讓老黑山煥發新機。畢摩是達布的世俗身份,也是他的精神符號。
達布是一個怎樣的人?年少時,健早爺爺摔傷了,他快速返回家中叫來父親幫忙。電科大伯犯困了,他幫著一起放羊,砍下長著嫩葉的樹枝給羊吃。長大后,面對沙由的無理挑釁,他退讓、隱忍。被沙由用木柴打得頭破血流以至于昏倒之后,面對來道歉的劍沙,達布依然禮貌有加,替對方寬心。日常生活中的細節最能體現一個人的性情與品質。商榮家遭遇泥石流,父親、妻子、女兒均被壓死之后,達布把他視為自己的親侄兒給予無微不至的關心。不是一天關心,而是持續多年關心。布扎的同學來玩,欲上山采菌子,身為父親的他好酒好菜招待,幫年輕人卜卦,穿著畢摩的裝扮和他們合影留念。在年輕人面前,他展示了隨和的一面。
李學智著意為小說設置接二連三的沖突,讓人物性格在沖突中得到進一步的刻畫、豐富、圓滿,并因此引發讀者深深的思索。
圖南的媳婦支景喝農藥死了,支景后家硬說她是圖南逼死的。圖南不承認,雙方又不愿意報警,因此一致要求做端犁鏵口神判。被請去做神判的達布對因取勝而狂喜的圖南表示不解。“這個圖南也是,支景的死,真的跟你沒有半點關系嗎?你出去打工幾年,回來就要鬧離婚,這讓人受得了嗎,現在罪名洗掉了,一切責任就沒有了嗎?”做神判固然有它的合理之處,然而完勝后洗刷“罪名”的圖南真的沒有半點過錯嗎?圖南于夫妻之間情義、家庭的責任兩個層面上的缺乏擔當,難道就可以從此一筆勾銷?這樣的過程且不論科學與否,單是這樣的結果就是既不合情也不合理的。外出打工對傳統家庭與婚姻的沖擊。支景的死只是一個縮影而已。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傳統習俗置放于新的時代情境中,讓舊與新、慢與快、內與外碰撞出火花,情感變遷、思想波動的空間便隨之延展開來。
“在老黑山,沒有了畢摩,活著的人沒了精神,死掉的人只能變成孤魂野鬼。”這是達布對兒子說的話。“你學了畢摩,看事情要像雄鷹一樣長遠,做事情要像老虎一樣得力。” 這是達布對徒弟者都說的話。“唉,現在什么都要從簡,好多事情火候不夠,也難怪最后不成樣子。漢族有句話說,火到豬頭爛。我們現在好多人沒有耐心了。我們作畢為什么不像以前那樣靈了?我們為什么不像那些前輩們有譜氣?學畢不真心,不下苦功,搞些花架子。”這是達布對安教授說過的。不管遇到怎樣的情況,達布的心都是正直的,脊背都是挺直的。正如孟子說過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心中有必須守護的一桿秤,他有心系眾人的擔憂,他守護傳統并不等同于守舊迂腐。
圍繞著達布這個人與“作畢”這件事,李學智塑造了一群活得相當古意的人,生活在時代潮流邊緣的人,達布是處在核心位置的唯一一個。包括達布在內的這些人對生活的方方面面極其慎重,謹慎又鄭重。對待生活,他們絕無半點流于應付之意。他們傳遞出的是既陌生又切近的氣息,這份氣息可謂力透紙背。何為陌生?書中那群有古風、古意之人的生活方式與處世態度。在《姑娘房》這一章的最后,達布心里這么琢磨著:“現在的年輕人們,好多已經不相信他們這一套了。像今天古舒家這樁事,要是在年輕人那里,就不叫事,何必又要殺羊宴請全村人?但是在老一輩那里,他古舒不這樣做,就沒法向村里人交代。”在達布、古舒等人眼中,年輕男女是在姑娘房里發生關系且未婚先孕實屬不潔之事。
氣息為何會令人感到切近?因為人人皆有生命的來路,有了這個前提,便會感同身受于李學智關于彝族人、彝族村落、彝族風俗的書寫。讀小說,想見其為人。“彝族人”是李學智最看重的身份,它是融化于血脈之中的身份。基于此,小說中才能營造出身臨其境之感,在兩千多公里之外讀著小說的我,仿佛站在老黑山那濤村里,俗日子里的煙火氣就在我周遭涌動著澎湃著。現代人多有渴盼遠方的同時把故土拋之腦后的弊病,李學智沒有這樣的缺點。評論家謝有順關于小說寫作的意義有過這樣的說法:“小說的存在其實是為了保存歷史中最生動、最有血肉的那段生活,以及生活中的細節。”我以為,用這句話來評價《達布的金山》是恰如其分的。與生活有關的最生動、最有血肉的細節,是整部小說中最動人的部分,也是最挑戰寫作難度的部分。正是這些細節的縱橫交織編就了小說的生活之網,網出真實的俗氣與鮮活,網住讀者深陷老黑山的心。媒人哈啼和達布妻子沙妮的對唱,一個主動熱忱一個特意躲避,皆通俗、生動、直爽、極富渲染力。布期出嫁前伙伴們唱的《哭嫁調》,唱得達布心中倍感沉重。布期婚事將盡時的《留客調》,含蓄凝練且意味深長。更重要的是小說里提到的一次次作畢儀式,可謂書中彝族生活氣息渲染得最濃烈的一筆。這一筆很長、很重、很精彩。作畢的目的不同,儀式與過程自然不同,講究與忌諱也隨之不同。因而作畢過程的詳細書寫與獨特氣氛的營造,便成了作者必須傾注心血之處。
祖上的有些規矩還是祖上的規矩,祖上的許多規矩早已不是祖上的規矩了。時代的車輪滾滾而來,誰都躲不開避不過,傳統文化于今該何去何從不是一道三言兩語可以打發的簡答題,而是一道意味悠遠的思考題。樂意繼承祖業當畢摩的人越來越少,新時代的思想與風氣正在對古老的彝族文化與彝人村落產生巨大的沖擊。在這個特殊的時期,畢摩與其說是一種身份,不如說是一個象征。象征了彝族的傳統文化的尷尬處境。當然,這樣的沖突與代溝,并不僅在某一獨立章節里出現,而是在整部小說里或多或少、或濃或淡、時隱時現地存在著。布扎不想繼承父親的行當,一心一意在鎮上賣摩托車不正是典型的證據?同樣身為畢摩的惹伙邀請達布做棄畢,達布建議做短棄,惹伙的兒子伙則極力主張做長棄。他說:“達布大伯,我在外邊打工,主要是在車間里開機器,機器爛了,老板會找人來修。我們病了,就上醫院去。我每天在機器上干十幾個小時,沒有什么空閑來背誦經文。那些地方,畢摩沒用處。”一席話,展示的是畢摩在當下的真實處境。
李學智的語言簡潔、精煉,幾無多余的修飾,更無所謂的拖泥帶水。簡、精不等于無,對讀者來講反而意味著更多。此之謂文字表達上的以少勝多。正如中國畫中的留白,留白非空白,是更大的占滿與擁有。亦如武林高手只有簡單的幾招,比起多余的花拳繡腿來,耐看又實用。《達布的金山》雖是一部近二十五萬字的長篇,其中的許多章節卻時時讓人感覺言有盡而意無窮。在我看來,這部小說是一曲寫給過去、寫給傳統的挽歌。新的時代正氣勢洶洶地到來,它們不由分說地搶奪陣地,搶奪并占領老黑山的陣地與人們思想的陣地。這部小說更是一曲頌歌,借達布這個人物形象的刻畫歌頌善良、寬厚、仁義、理智、盡責的彝族人,借老黑山在彝族人腳下的靜默無言與寬廣肅穆表達自己對那一片土地的熱愛。
不顧妻子的勸說,達布執意把十三部經書和《老黑山藥譜》獻給政府。他說:“我們家這本藥譜,好多方子都可以做成藥丸,這樣也就讓好多人都可以治好病。”達布是心懷大愛的畢摩,是坦蕩無私的彝族人。在常人眼中堪稱巨款的二十萬,他無所謂,無所謂獎勵不獎勵,獎勵多與少。達布身上固然有許多優點,但是在老黑山與彝族文化何去何從的緊要關口,他的不存私心、一心裝著老黑山才是最重要的品質。達布說:“把老黑山砍光、賣光、吃光,富了一兩年,坑了幾代人,這種事情做不得啊!”這情真意切、高瞻遠矚的大白話不正是保護性開發、可持續發展等理念的詮釋嗎?
在眾人都支持修建水廠的時候,持堅決反對意見的只有達布一人。他對自多說:“其實,你只要認真想一想,要是你是那依河下游的人,你會怎么想呢?斷了老黑山的水,就是損了老黑山的筋脈;斷了村莊的水,就是抽了田地的血。這些事情,說起來遲早會有大報應的,這事啊,整不得的。”此番肺腑之言說得語重心長。第一句話是懂得換位思考的將心比心,有古仁人之風。不被利欲熏心,沒有自私自利。第二句話是敬畏那依河、敬畏自然,有明確的自我定位,有自知之明。至《圣水》一章,達布的形象陡然高大起來,與旁的村民相比高下立現。兼具傳統做派與時代氣息的達布豐富、生動,有走出紙頁的立體感。
何為達布的金山?這部小說寫的不是達布如何創業致富擁有一座金山的故事,而是寫他在時代的大潮面前,如何擁抱真善美、懷抱正義、守護老黑山的故事。老黑山就是達布的金山。金山就是有“金子”可以開采的山。不是真的數得清的金子,是比真的金子更金貴的“金子”。小說標題雖為“達布的金山”,但是達布卻從未想過將金山占為己有,而是想方設法讓這座金山讓惠及更多的同代人以及子孫后代。只有出現越來越多如達布這樣的彝族人,老黑山才會是世世代代彝族人的金山。
巴爾扎克曾說過:“小說是一個民族的秘史。”誠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