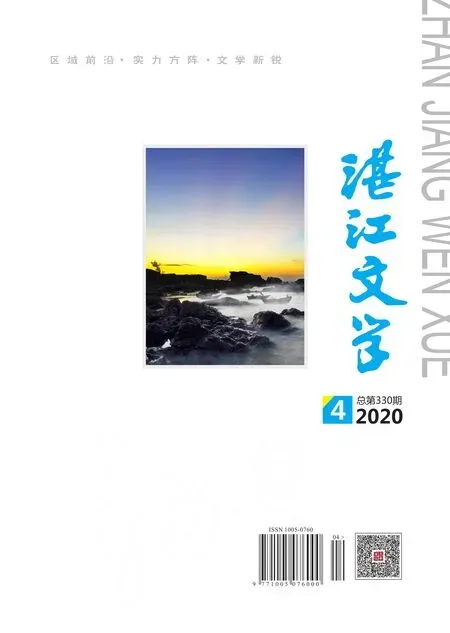清明煙雨走紅安
陳鴻波
水流千溝經萬壑,人間最愛是紅安。
身為紅安人,故鄉始終是我心中最驕傲的圣土。總喜歡漫閱著她的歷史,總喜歡沉浸于她的滄桑。那承受了數十年革命戰爭的斷垣殘壁還在,那耄耋老人穿越槍林彈雨的累累傷痕還在。沃土田園,山川處處,至今還傳唱著振奮人心的紅歌——我就知道紅安是永遠紅的!
每年天臺山上的映山紅開了,赤霞烈焰,就像天上滾滾不滅的彤云。倒水河的水也隨著變得更清靈了,清冽冽的河水倒映著蔚藍色的天空,澄澈得如同一面鏡子,照著我面前即將奔赴的遠途。
老君山上的蘭草花芬芳撲鼻,黃色的花瓣結著褐紅色的穗子,連根莖也透著絲絲的殷紅,誰會懷疑那不是英雄的血色。而此時此刻,天臺山上的云霧茶也正在迷蒙細雨中綻吐著新葉嫩芽。山是青山,茶是好茶,青山處處埋忠骨,這美麗的茶園,靈秀的茶葉,也無不感受著先烈們碧血丹心的潤澤,炒制的茶葉也是好過龍井,泡出來的茶水也要賽過玉液龍涎。
離別家鄉歲月多,無數個在他鄉寂寥寄居的夜晚,我沒有一次不是夢里回到紅安。聽那鐵馬冰河,看那旌旗獵獵,追憶那烽火歲月,接唱那軍號壯歌。穿越過歷史彌漫的硝煙,走過那連綿不斷的霧障叢林,就迎來了今天的旭日,而這每一幅都是動人心魄的畫圖壯錦。這不僅僅是我一個人的情懷,每每問及在外面工作的紅安人,似乎他們也是一樣的心情,我要問他們的問題,也正是他們要問我的。紅安就是紅安,美不美,家鄉水,親不親,故鄉人。只要你是這塊土地上走出來的人兒,哪怕僑居國外,或者在上海北京,不管你地位多高,無論你多么富足,你也會幾回回夢里歸來,眷戀故鄉的田園山水,纏綿故鄉的風俗民情。
樹高千尺不忘根,是的,故鄉不可不回。即使你是這塊神圣土地以外的人,我也可以鄭重地對你說,歷史不能忘懷,精神還得繼承,而紅色的紅安不可不去。
到紅安沒有不去陵園的。這里說的陵園,就是黃麻起義和鄂豫皖蘇區革命烈士陵園。園以地顯,地以園輝,旎旖的風光,悲壯的歷史,燦爛的人文,久而久之,竟成了紅色土地上的一大勝景。
紅安的陵園,在本地是婦孺皆知的。過去人們都叫她烈士祠,直到如今還有不少人這樣叫她,有的老人甚至習慣著叫了一輩子,可見這種對英雄烈士的感情,在他們心底植根的深度。陵園的規模是很大的,占地足有幾個多平方公里。這里是全國最大的十座陵園之一,一年四季蒼松掩映,翠柏長青,時刻都體現著她的巍然與厚重。稍稍了解一些歷史的人都知道,以紅安為中心的大別山革命根據地,在紅軍時期就是除中央蘇區井岡山外的第二大蘇區。黃麻起義在這里驚雷一響,接著八方涌動,萬眾一心,紅四方面軍在這里誕生,紅二十五軍、紅二十八軍在這里成立。那血雨腥風的歲月,從這里一路路刀光劍影,一路路熱血灑拋,一茬茬人連著倒下去,一茬茬人又在投身革命中站起來,水深火熱的勞苦大眾終于當家作主。
清明時節雨紛紛,我就習慣在這樣的日子回去。風輕輕地拂著面龐,柔和而舒爽。蒙蒙的微雨下著,浥濕著通往陵園的路,也浥濕我的心情,去掉我內心的激動與浮躁,讓我懷著崇敬的心去由衷的緬懷,拜讀每一位將軍,感恩每一位烈士。當走過每一處場館,掀開每一幅畫面,可以自己去靜靜地感悟,也可以跟隨著講解員清脆的聲音去瞻仰。在紅安,在陵園,你能夠不為之動容,你能夠不肅然起敬,你澎湃的心潮又如何能夠不波瀾起伏?
今年暮春里的一天,我是悄悄地從工作的武漢回去的,剛好是清明節的前日。我沒有挑在清明節的當天,我知道那天陵園里人不會少,車也不會少。或者個人的祭掃,或者公家的祭奠,熙熙攘攘地,想求一隅靜處,想獨自在歷史的風云中穿梭寄懷,那是很難的。
到那里去,我不想打傘,淋著絲絲的細雨就好,可以安撫我隨時起伏的心。最好從紅安縣城的南門越過,看看那迎面聳立的銅鑼。一聲鑼響,就可以凝聚紅安人的士氣;一聲鑼響,也可以歡迎和包融八方的來客。銅鑼面對著省城武漢,客從南方來,這里是進入縣城的口子,要去瞻仰陵園祭奠先烈,就先見識一下銅鑼的風采。說是銅鑼,其實是花崗石的雕像,觀其形,感其大,卻是曠古未有的。一丈多高的鑼架,方圓八尺的銅鑼,僅一柄鑼棰就有手臂那么粗實,你見過嗎?
“小小黃安,人人好漢。銅鑼一響,四十八萬。男將打仗,女將送飯。”一首傳唱了幾輩子的《黃安謠》,就是這面銅鑼的見證。你不曾經歷過,但你可以想象到那個火熱的年代,那是男女老少斗志昂揚的崢嶸歲月,那是仁人志士舍生取義的熱血高潮,一桿桿紅纓槍劃向黑暗的蒼穹,一面面革命旗撲向萬惡的霸主。銅鑼聲聲,喚醒了一個時代,讓愚昧了的不再愚昧,讓該反抗的起來反抗。銅鑼聲聲,“打土豪,分田地”,四鄉八里,一群群光著腳背的農民站起來了。沒有槍,鋤頭扁擔就是他們砸向黑暗的武器。他們咆哮著,像黎明曙光里沖出的醒獅。就是在這面銅鑼下,他們眾志成城地說——誰愿意做土地的佃戶,誰不愿意做自己的主人!
自從修建了陵園,這條通往縣城過南門河的路,就叫作陵園大道。任它熱鬧喧嘩時車水馬龍也好,任它罷市打烊后冷冷清清也罷,街面上總是格外干凈。政府沒有刻意地要求,老百姓卻保持著高度的自覺,讓這條往陵園去的大路一塵不染。我就漫步在這條熟識的路上,讓蒙蒙絲雨滋潤著我的心田。來時特意到花店買了一束鮮花,如今的紅安也是處處春色,人民的日子在浩蕩春風中日漸紅火,烈士和將軍們生前也出自這青山綠水的土地,我想他們都是愛花的人。
天街小雨潤如酥,盡管細雨一直下著,可越近陵園,我的心潮越是澎湃。原以為挑下雨的天氣來,我可以少一些激動,即使要感動也會控制一下情緒的,但今天似乎做不到,鼻尖已經在隱隱地痛楚而發酸。
曾幾何時,在臨近陵園大門三百多米的地方,沿街兩邊的綠化樹旁已經豎立了一塊塊的將軍牌。未見陵園,先識將軍,這儼然又為浩氣長存的陵園增添了一道新的風景。再仔細看時,這些將軍牌都是按上將、中將、少將的順序依次排列著,上面有將軍們的畫像和簡介,包括他們的出生地、生卒時間和生前任職。將軍牌一律用不銹鋼來制作,統一的格式,中間還刻著某某單位負責管理的字樣。一個個赫赫有名的將軍,一個個威武岸然的將軍,假如你未曾見過他們,在這里,在紅安,你都可以很容易地見到他們的風采。
早在唐代,詩人曹松就曾在一首《己亥歲》的詩中寫過:“澤國江山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樵蘇。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活下來的將軍經九死一生,當然是幸運的,而無數成為烈士的英靈也終將不朽。盡管有的登記在冊,有的無姓無名,但人們會說,你是英雄,真正的英雄常常犧牲在人民的腳下。幸存下來的紅安將軍,他們在世的生活是儉樸的,對子女的要求是嚴格的,對家鄉的親友是無私的。曾記得有一位應該授銜上將而實評中將的紅安籍將軍對戰友們說,我能夠戰斗到全國解放已經很不容易了,還在乎什么授銜!想想和我們一起拋頭顱灑熱血的戰友,為革命而早早犧牲了寶貴的生命,他們才是真正的英雄,功勞永遠是他們的。
雨還在下,我沸騰的心情卻沒有隨之解潮,人已經在不知不覺中到了陵園門口。古典靜穆的牌坊式大門敞開著,寬闊的中門左右還有兩個側門,牌柱并排聳立著,像靈霄寶殿上巍然屹立的金剛。歇山式的頂面重檐結構,蓋著綠色的琉璃瓦,青翠欲滴,象征著革命先烈的萬古長青。金色的陵園題名還是徐向前元帥寫的,就是這個出生在北方山西的大個子,紅軍時期在紅安一待就是近十年。他不僅是紅四方面軍的總指揮,還是紅安的女婿,與紅安結了緣,也結了親。那一年,這個靦腆老成的男人,與美麗的紅安姑娘程訓宣相愛了,在艱苦的歲月里,簡單的一桌飯席就算成了親。從此一個在前方指揮打仗,一個在后方負責宣傳。本該是天造地設的有情人,誰料天有不測風云,紅四方面軍的肅反派為了捏造徐向前的材料,竟然對程訓宣嚴刑拷打,妄想從她口里探出一些什么。程訓宣身在流血,心也在流血,但她相信自己的丈夫,堅貞不屈的她,最終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之下,臨死也沒有說出一個不該說的字。程訓宣的死,讓徐帥心痛了一生,后來南征北戰,每每想起也是傷心不已。他對紅安是有感情的。解放后,他在樸素的家中無數次接見紅安的鄉親,甚至還將程訓宣的母親接到北京贍養,直到老人臨終前含笑而去。山水有痕,真情無限,這方圓不大的紅安,曾經磨破他多少雙跋涉的草鞋,曾經多少次在戰斗的槍聲中揚鞭策馬。黃安城、七里坪、倒水河、檀樹崗,到處留下了他矯健的身影,是他讓兇殘的敵人聞風喪膽,是他讓革命的隊伍星火燎原。 80年代初的某一天,一位白發蒼蒼的老人在他北京小四合院的家中靜靜地追憶,意往神馳,默立良久。他看著窗外的南方,那是血染的紅安的方向,最后欣然命筆——“兩百個將軍同一個故鄉”!那些長眠地下的戰友,那些為國捐軀的英魂,還有那忠貞不屈的妻子,此刻,你們又在哪里?如果你想知道這位老人是誰,他就是當年的徐向前!
到陵園的人比我想象的要多,進進出出地,三五成群,也有像我一樣捧著鮮花獨自去的。售票口人頭攢動,有幾個人好像在那里登記什么。我也趕緊跟過去,正準備從口袋里掏錢買票。陵園的工作人員連忙一擺手,沒等我會意過來,旁邊的游客已經搶著說:“從去年春天起,到紅安烈士陵園來參觀,全部免票啦!”我愣怔了一下,工作人員微笑著說:“原來一百二十元的門票,現在都不用買了,只要拿取身份證登記一下就行!”聽到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我是又驚又喜,不管地方是出于什么樣的想法,這樣的舉措絕對是受歡迎的。古人云: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讓世界了解紅安,讓紅安走向世界,不拒細流,方匯百川。當年的黃麻槍聲如同霹靂,當年的黃麻烽煙如同圣火,拯救了一個民族,抒寫了一段歷史,也締造了一個神話。有人說,紅安是一個奇跡,是一個世界之最。仔細想來,這話也是不過分的。
穿過雄偉巍峨的陵園大門,我徑直往里邊走。雨還在清爽地下著,風也在靜靜地吹,風是吹面不寒,雨是沾衣欲濕,讓人徜徉在陽春三月最柔和的風景里。兩邊的迎春花綻露出金黃的火焰,一條又一條,簇簇擁擁地,隨同柳色一齊在微雨中舒展青春。高大的雪松黑壓壓地,像天王擎傘,像力士舉鼎,饒有氣勢地向遠處鋪開,也或直插云霄,也或虬枝旁逸,撐起了陵園的不凡與大氣。
接著走上去,就可以看到路旁的花叢里,矗立著董老題寫的“樸誠勇毅“四個大字,這就是不屈不撓的紅安精神。其實,火熱的紅安精神從大革命時期起,就已經初見雛形,到新中國的建立和人民群眾獲得解放,在幾十年的革命斗爭中,這種以黨性和人民性為價值取向的認知、情感、意志的總和終于形成。“要革命,不要家,不要錢,不要命,一要三不要;圖貢獻,不圖名,不圖利,一圖兩不圖”,敢為人先的紅安人,也敢冒當時天下之大不韙,光著赤膊甩開大步踩出了一個清新的世界。翻開壯麗的史詩,我們可以看到,當年黃安縣國民黨黨部在“清鄉委員會”的布告中說:“十齡幼女,口喊自由。三尺之童,目無長上。黃安素稱禮儀之邦,一變而為禽獸之所。”可見當年紅安的革命是遮天蓋日的,火種一撒立時就達到了高潮,足見其“赤化”到了深入人心的地步。而這個鼓動思想之功的啟蒙人,就是紅安籍的導師董必武。難怪原國家主席李先念在一次視察座談會中說:“董老是湖北革命的一面旗幟,我們都是他的徒子徒孫。”
迎面而來的紀念碑就在整座陵園的中軸線上,當我走近她時,那里已經聚集了一些人,還有許多堆積的花籃花環。地上濕漉漉地,鮮花上滴灑著甘霖雨露,在這里綻開笑顏,也綻放春天。能夠守護著為革命犧牲的十四萬英雄兒女,紅花綠葉也是幸運的,花是丹心的輝映,葉是碧血的潤澤。這巍然聳立的黃麻起義和鄂豫皖蘇區革命烈士紀念碑,凈高有二十五點七米,在蔚藍的天幕下直矗蒼穹。前面和左右兩邊鐫刻著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葉劍英、徐向前、李先念的題詞,碑座的正面塑有五星的碑徽,臺座正中為漢白玉雕成的花環,雄偉的氣勢與不屈的英靈將同于不朽。從正面轉過來,左右分嵌著黃麻起義、蘇區軍民武裝戰斗、保衛蘇維埃政權的浮雕,碑身的前面還刻有中共湖北省委和省政府撰寫的碑文。紀念碑兩旁的雕像群形象逼真,氣勢磅礴,左邊是一位武裝的農民身背大刀,高舉銅鑼,象征著黃麻起義,右邊是一位紅軍戰士高擎鋼槍,奮勇向前,象征著不屈的戰斗。在他們面前,我只有一顆熾熱而感恩的心,以及奔騰的熱血和激動的情懷。獻上一把鮮花,捧上一把泥土,虔心默默,佇立,鞠躬,以往的堅強都化歸脆弱。我流淚了,是盈眶的熱淚,淚水流到紀念碑旁邊的泥土里,不管以后身在何處,心卻永遠印在了紅安。
舍不得擦拭眼角的淚痕,我在無聲的細雨中朝里走。男兒有淚不輕彈,人一生流淚的機會總是有限的,要么為了親人,要么為了故鄉。于親人或許為其難過,或許哀其不幸。而面對我自己的故鄉,只要站在這一片深情的土地上,只要腳步踏入紅安的地界,我的心就會顫抖,滿腹豪情在心海里激揚,一浪趕一浪,為這里的人而喜,為這里的土而歌。
幾年沒有來,還真是變化了不少。在山明水秀的陵園,最宏偉博大的建筑就是黃麻起義和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紀念館。經中共中央批準之后,頭年夏天奠的基,到翌年冬天就正式對外開放了。占地近四千平方米,光展覽面積就有五千多平方米的紀念館,記載的,鐫刻的,抒寫的,展示的,無一不是血染的黃麻。從遠處看,紀念館就像一個規正的“品”字,五個寬敞的出口,東西各有兩道門與陵園的其他四座紀念館相通。仿古紫銅門穿透歷史,與立面墻、弧形板、蘑菇石構成精美的組合,猛然看就像一座古老的城堡。大小不等的長條窗戶,像經歷過戰爭殘留的槍炮彈孔。這里每一處都充滿革命的激情,既有古典園林的神韻,又兼現代建筑的風格,于是就成了陵園一碑五館中的最亮點。
有人說,這歷史紀念館是紅安革命的剪影,要載入史冊的全在里面存著,沒有載入史冊的也被羅致其中。每一個展廳都是一幕光輝的歷史,每一場戰斗都是熱血澆鑄的凱歌。我已經完全融入其中了,忘記了當下的時間,也忘記了戶外的細雨。歷史在《大別雄風》中開篇,在《將軍搖籃》中結束,十年紅旗不倒鑄就了輝煌,人民前赴后繼抒寫了壯烈,于是在不斷的起伏聲中涌向了高潮。說黃麻驚雷是一曲壯歌,說商南烽火是一筆神話,說皖西烈焰是一首鴻詞,說赤區新貌是一篇巨制,說鏖兵大別是一幅畫圖,說浴血孤旅是一抹重彩,都是名副其實,恰如其分的。山不老,水常流,大別山的人民在譜寫精神的同時,也在用生命的代價創造了驚人的業績。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走出歷史紀念館,我知道該去哪里了,雨從來就沒有停過,任它飄灑任它淅瀝吧!映入眼簾的長墻,青色的花崗巖在云幕下熠熠生輝,你以為那是墻嗎?十四萬紅安兒女,不用說,都是英雄,用生命構筑,用熱血凝結,用信仰澆鑄。黃麻起義的英靈,長征途中的烈士,以及西路軍在河西走廊的悲壯與喋血,一齊讓這鐫刻十四萬紅安人名字的墻體閃光。沒有鮮花,我隨手折幾枝路邊的花草,扎成一個美麗的花環,放在烈士墻前的紅星碑上。在這里,我連聲音也差一點哽咽,注視長墻,仰望蒼穹,久久也不忍離去。先輩啊,今天終于可以在這里安息,當年你們流血拼殺的時候,你是否想到有一天會終歸于不朽,故鄉和人民都會記住你們。
十四萬啊,人站成一排該有多遠,名字刻起來該要幾多年,我情不自禁地考慮起這些問題。自古將軍百戰死,何須馬革裹尸還。我仔細地讀著這些名字,其中有許多并不陌生。紅軍時期,僅僅在我們七里就制造了幾個無人區,一村村炊煙無火,一戶戶雞犬無家,而心中的火是撲不滅的,那就是革命。
就在這凝重的長墻上,有一個我親屬的名字,我看到了。雖然為國捐軀的他找不到回家的路,我卻在這里找到了他,政府和人民也找到了他,如今也在這光輝的石墻上。那是一幅怎樣的場面,我的腦海里今天依然可以翻起。一個母子倆相依為命的家庭,兒子看到革命隊伍來了,一定要去參軍,娘死活不依,就這樣兒子平生第一次哄騙了瞎子娘。兒子說,娘,我背你去看戲。之后就將白發親娘馱上了板樓,接著下來抽走了樓梯。兒子走時對著娘哭了,娘啊,我當兵去,你好好在家吧!娘也哭了,她不知道這次是永別,一個可以由人攀越的樓梯,從此將他們隔成兩個不同的世界。兒子后來在戰爭中犧牲了,娘活到了解放后,成了五保戶。她做夢都想再見一次兒子,可歷史往往就是這樣的無情。
如今的紅安沒有機場,在這里,你卻可以看到一架小小的戰斗機。這就是30年代肆虐盤旋在紅色革命根據地上空的敵機,也是有史以來第一架被紅軍繳獲的飛機,后來改名叫“列寧號”。那年月,紅軍有什么,野菜飯,南瓜湯,青山是我的房,野地是我的床。一個只有大刀長矛的隊伍,居然在反“圍剿”中有了一架自己的飛機。戰爭的硝煙早已散去,撥開歷史的云層,在這里它就是最直接的見證。它可以告訴如今的孩子們,當年那是一個怎樣的年代,怎樣鬧革命,怎樣是殘酷,如今和平了,該珍惜的要珍惜,該記住的不能忘。
“列寧號”的上面就是董必武紀念館。中國古典庭院式的結構,白墻碧瓦,飛檐翹角,依著山體而建,更是顯得古樸莊重。人從數十級臺階拾級而上,也隨著紀念館掩映在蒼松翠柏之間。登上臺階,抬頭便可以看見徐向前元帥題寫的“董必武紀念館”六個鎦金的大字,字跡工整有力,似乎就是董老一生為國為民的凜然正氣。從正門進去,院子中央安放著董必武的半身銅像,基座上由鄧小平題寫的“董必武紀念像”六個大字飄逸灑然。基座后面就是董必武與夫人何蓮芝的骨灰合葬墓,這是二〇〇六年經中央批準,其親屬從北京八寶山送回來的。生從紅安出去,死從外面回來。曾記得那辛亥豪情,曾記得那求學東渡,曾記得那南湖船上,曾記得那長征途中,一個經歷了大風大雨的人,一個嘗遍了人間坎坷的人。在三年嚴重困難時期時期,他心中最惦記的也是故鄉——那歷經劫難和滄桑的紅色家鄉啊,鄉親們,你們都有飯吃有衣穿嗎?
“九十光陰瞬息過,吾生多難感蹉跎。五朝弊政皆親歷,一代新規要漸磨。徹底革新兼革面,隨人治嶺與治河。遵從馬列無不勝,深信前途會伐柯。”在1975年董必武九十歲生日時,病魔纏身的董老寫下了人生最后一首詩詞,這不僅僅是他一生的光輝寫照,也是一代偉人的絕筆。一棵大樹溘然倒下了,一個世紀老人從容去了,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紅安的驕子沒有遺憾,他胸懷的是祖國,是人民,魂歸的是家鄉,是故土。
從董必武紀念館出來,我一順向西邊走去。水泥地面像被洗刷一新,濕透了卻沒有溢出水來,我的心卻在這清明的季節翻卷著潮水。那西邊也是一座館藏,依山傍勢的雄姿,氣勢恢宏的面貌,讓我懷著崇敬的心情走近她。那里也是一位偉人,也是一位巨子,一個鄉間走家串戶的木匠,竟然成了泱泱大國黨和國家的領導人,是偶然么,是奇跡嗎?不,你自己去看看吧,盡量看得清楚些,歷史會對你詮釋,給你一個完整的答案。李先念,一個大家并不陌生的名字,甚至于在今天還有著不凡的影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說起來多么容易,就連許多大學問家一輩子皓首窮經都未見做得到的事情,他居然在磨礪和劫難中淌河涉水地做到了。
我想到了李先念在紅安高橋鎮長豐村那李家大屋的老房子,熟悉的土坯墻,青色的溝檐瓦,石門檻兒也記錄了他離家的歲月。那古老的織布機、紡車、搖籃,還有那雕花大床、水缸垛子,這些都是李先念少年時做的木活,如今還在思念著它的主人。就是那個山村少年,從他家鄉的紅馬寨上、九龍沖里走出,組建了游擊隊,攻下了黃安城,成為大別山紅四方面軍的驍將。在長征路上,他三過雪山草地,在河西走廊突出重圍,將部隊的火種帶到了新疆,走出了星星峽。中原突圍有他,千里躍進大別山有他,首鎮湖北有他,為國理財有他,粉碎“四人幫”有他,改革開放有他,這本是平常人家的兒子,從紅安走出去,漫長的一生就變得很不平常。
此時此刻,風還在吹,雨還在下,我的耳邊仿佛又聽到了這位智慧老人的聲音。那是三年嚴重困難時期時期,時任湖北省省長的張體學從紅安視察回來,連夜打電話給北京的李先念:“李副總理,你就是砍我腦殼,也要給我兩億斤糧食!百姓們沒法活了!”李先念緊咬嘴唇,半晌才開口:“你就是砍了我腦殼,我也拿不出兩億斤糧食——”我還聽說過一件事情,某一年,紅安老家的人到北京,請求李主席幫忙解決一下家鄉的困難。就是在北京,就是在他中南海的辦公室里,李主席雙手一攤,板著臉說:“我是國家的主席,不是你們紅安的主席,你們有困難,哪里又沒有困難!”一代偉人去了,什么也沒有帶走,只留下一卷史詩,兩行足跡,幾篇佳話,還有珍藏在故鄉人民心中永遠的音容!
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十四萬英魂啊,你們可曾都回到故土,兩三萬登記在冊的烈士啊,你們夢里是否也相聚在故鄉。浴血大別,瞑目長征,魂斷草地,陣亡河西,不管路程多么遙遠,不管曾經多么艱辛,犧牲了,就都魂兮歸來,葉落歸根,這里有你們的鄉音,這里有你們的鄉情,故土和田園都在召喚。在陵園的西南側,有幾重幾進的古式大院,長廊環繞,映碧流丹,那就是著名的烈士館。館名仍然是徐向前元帥題寫的,《大別山母親》和《碧血黃安》的背景浮雕融為一體,伴隨著氣勢磅礴的音樂,寓意著祖國母親將永遠銘記著烈士的英名。革命先導、起義英雄、大別忠魂、天臺鐵骨、西征壯士、民族脊梁,一幕幕悲壯如歌,一面面紅旗如血,震撼著我不平靜的心。想哭,哭不盡,任憑多少淚水,也不夠激昂,不夠蒼涼。燕然未勒歸無計,不破樓蘭終不還,那年月,那豪情,與這里比起來,實在不算什么。
雨在風中迷失,我的眼線也在迷失,睫毛和眼角上盡是淚花,這是必然要流的眼淚,不流才是不正常。順著一米多寬的石階往稞子山上走,綠樹濃蔭,蒼松翠柏,山花竹徑,古木參天。那石碑高聳的地方,是一座座將軍的墳塋。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那一個個打著赤腳,穿著草鞋,光著膀子的孩子,如今都回來了,魂歸故鄉,與紅安的山水擁抱。看吧,鄭位三回來了,韓先楚回來了,秦基偉回來了,還有王建安將軍、張天云將軍、劉昌毅將軍——雖然說,做官不打家鄉過,活著的時候他們沒有刻意關照過家鄉,死了卻仍然要想到回來。故鄉的綠豆粑、紅苕片、臭皮子、小麻油、珍珠花、煨葫蘆,那是頂好頂好的啊,山珍不及它豐美,海味不夠它滋長。還有那漫山遍野的映山紅,每年的清明節前后,就會如火如荼地開著,一如烈士們殷紅殷紅的鮮血。
一路仔細地往前看,耳邊的樹葉在沙沙作響,似是悠悠的羌笛,似是低鳴的號角。我緩緩地走近每一個英雄,沈澤民、曾中生、蔡申熙,一個個當年如雷貫耳的名字,如今也魂歸這里。他們戰斗在紅安,犧牲在天臺,青山處處埋忠骨,人間無處不青山。看不到紅旗映日,看不到烈焰如詩,那就作天臺山上的一棵青松,就作紅色土地上的一株小草。
稞子山的最東邊,那是紅軍墓園,平時是不開的,今天竟然也開放了。涂著綠色油漆的鐵門開著,好像在等待什么人來臨。雨絲如同無色的米線,讓人放松,讓人久違。我摘了幾把路邊的山花,迎春開了,玉蘭開了,還有野杜鵑和丁香。一枝一葉總關情,他們把一切獻給了黨和人民,呵呵,又在乎我什么呢?挪動著沉重的腳步,我走近每一塊墓碑,這一個個年輕的生命,曾經是那樣鮮活,那樣奮勇,如今就長眠在游人的腳下。不,他們是一座山,我永遠也逾越不了的山。分開一枝枝鮮花,插在每一塊碑前的泥土里。我在心底默默地祝福著,你們靜靜地開吧,要開得燦爛些,要開得絢麗些,活著是不屈的英雄,死了是不朽的烈士。
天在細雨中一會兒明晰,一會兒灰暗,來陵園的人似乎多起來。走下紅軍墓園,穿過靜穆的骨灰堂,沿著那遍栽塔柏桂花樹的山路,一直向西邊走去。紅色的碑林,像一枚枚平地升起的火炬,排列在背山的兩旁,那火焰就像要升騰,那紅球就像要跳出。偉人的題詞,將軍的題字,還有那土地革命的史詩,那紅軍時期的紅歌,都是為紅安而書,為紅安而作,如今也一篇不漏地聚集在這里。毛澤東在接見紅安代表時說:要保持紅安永遠紅啊!以及那“八月桂花遍地開,鮮艷旗幟豎啊豎起來——”的歌謠,也是從這里唱起。還有那“痛恨綠林軍,假稱青天白日,黑暗沉沉埋赤子;克復黃安縣,試看碧云紫氣,蒼生濟濟擁紅軍”的對聯,從那黃安一役起,革命的隊伍就有了新的名字——紅軍。看吧,碑林如血,都記錄著呢!這里是稞子山的頂峰,是稞子山的東面,每天一早就能夠看到太陽,看到旭日,看到朝陽如血。
臨近中午,人越來越多,車也越來越多,都趁著這清明時節趕著趟兒。雨還在下,有撐著傘的,也有沒打傘的,有抱著花籃的,也有拿著鮮花的,從紅安,從武漢,從外省,帶著虔誠和景仰的心來。在轉回去的路上,在那雄偉的紀念碑旁,我碰到了一個熟人。那就是被紅安人民譽為“紅色宣傳員”、“紅色爺爺”的胡耿老師,他正在給一群戴著紅領巾的小學生津津有味地講解。胡耿老師是武漢人,年輕時是一位空軍部隊的團政委,出于一種對魅力紅安的不解情結,一種對英雄紅安的敬仰情懷,轉業后他放棄了大都市的生活,堅決要到貧窮落后的老區紅安。在他平凡的宣傳工作崗位上,他曾經無數次在國內外大中小學演講,用心中的歌去贊頌紅安,用手中的筆去描畫紅安,用紅安的真實歷史去演繹紅安。讓世界了解紅安,讓紅安走向世界,一位年近八旬老人的一生,就做了這一件大事。沉甸甸的責任,他還背著,即使是老驥伏櫪,還是志在千里。他曾經說,他會繼續挑下去的。孩子們正認真地聽著,紅領巾飄在胸前,風吹著,拂紅那一張張小臉,雨絲灑在他們蘋果般的臉上,漾出微紅的光亮。我向先生點頭示敬,不敢去招呼和打擾他,生怕因為我而影響了先生的講解。那是一群可愛的孩子啊,是祖國的花朵,是紅安的未來,正需要施著肥料,澆著雨水,傳授花粉,讓他們茁壯成長,去繼續紅安先輩們未完的事業。
出了陵園的大門,旁邊就是紅安一中,那是前總理李鵬題名的學校。此刻,里面正是書聲瑯瑯,一片片春花滋養在雨露里,蓬蓬勃勃地綻放著妍麗。大門兩側掛著激勵人心的橫幅,又是一年高考臨近了,又到了一個沖刺的季節。這是我的母校,我曾經是這里的學生。那時候,陵園是要門票的,但對我們學生從來沒有收過,不知為什么,可能是一種特殊的禮遇吧。這是一顆顆未來的太陽,將有一顆顆明星從這里升起,近水樓臺先得月,相信吧,每次進入陵園,孩子們都不會白來的。
走在陵園大道上,路是濕的,心也是濕的。雨兒稍稍下得大了一些,雨絲變成了雨點。我不由得看看天,還是一陣陣忽明忽暗地,總有人三五成群地向這邊走來。
“巍巍大別山,滿山紅杜鵑。花兒這樣紅,烈士鮮血染。為國把軀捐,為民何懼難。兒女盡英雄,紅安將軍縣,將軍縣。清清倒水河,兩岸盡歡歌。春風送時雨,景色滿山坡。紅譜添新彩,老區更祥和。兒女競風流,英雄故事多,英雄故事多——”一陣陣歌聲由遠及近地響起來了。我抬眼看時,原來又是一群學生,打著少先隊的紅旗朝這邊走來。領頭的老師打著節拍,吹著哨子,孩子們整齊有序地跟著,一張張可愛的帶著石榴紅的臉,在微微風雨中泛著晶瑩剔透的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