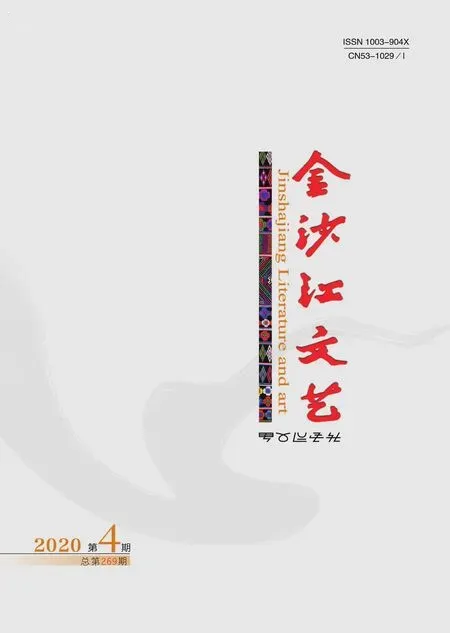春 風(外一篇)
李成生
小區的杜鵑花開了,白、粉、絳紅三色,旁邊有一株玉蘭,花瓣如玉雕一樣剔透晶瑩。這種物相就是春天了,所謂“三春”,指春季的三個月,這已經是今春農歷的第二個月了,這個春天實際上是如期而至的,只是我們的感覺錯位,一直以為春天還很遙遠。被漠視的嫵媚,依然婀娜多姿,并不在乎你的視而不見。朋友從遙遠的滇西無量山傳來一組圖片,那里的馬纓花開得漫山遍野,錦緞一般鋪在山崗上,讓人陶醉。春天回來的時候,我們甚至渾然不知。對于暮年的我來說,惋惜又錯過這個春天的花事。
人是社會動物,對一個人最大的懲罰不是讓他貧窮、仕途無望,而是讓他孤獨。《魯濱孫漂流記》的主人公被困孤島28年,歷盡人世間所有的孤獨,迫使這個孤獨者想出無數活下去的奇招,使他長期處于瘋癲狀態,這是何等的殘酷。宅居其實亦具殘酷的一面,雖然有了大把的時間,卻在一年最美好的時光里不得出門,連仰望藍天都成為奢望。抖音里無數小視頻呈現人們無聊至極的種種狀態:學蛆爬、學驢叫、挑擔賣饃、翻跟斗、瘋舞、語無倫次、罵街、學狗狂吠……封閉宅居家中的有些人瘋了一樣,僅僅幾十天時間,人性脆弱的一面原形畢露。讓人與大自然隔絕,大自然安然無恙,人卻從心靈到肉體都垮了。這種前所未遇的境況,怕是要催生一個學科:疫情中人類怎樣消遣孤獨。它的必要在于:這不可能是人類遇到的最后一次疫情,歷史上的瘟疫也不止一次,死神與我們如影隨形。
住高樓的好處就是春風刮得比地面上起勁,兩株高大挺拔的柳樹枝條亂舞,幾乎要抽到窗子的玻璃上,把今年的春天塑造得驚心動魄。幾乎每一次災難中,人類都要付出沉重的代價,經濟損失自不待言,許多鮮活生命的離去,使這個春天淚流滿面。過度的渲染使人們以為:門外游蕩著無數的病毒,到處尋找活人的肺寄宿,它們比閻王殿里的黑白無常更厲害,不管你陽壽是否到期,遇到你就帶你走。今年的地球在宇宙中是一只驚弓之鳥,生靈惶惶不可終日:韓國、日本、伊朗、意大利、美國……新冠病毒所到之處,一片哀鴻。地球今年像一頭發飆的瘋牛,把最殘忍的一面撕開給人看——流行感冒、火災、洪水、蝗災一股腦地在各地爆發,似乎神話中的末日即將來臨。春風勁吹,宣誓季節的不可逆轉,人們才猛然醒悟:地球并沒有感冒,地球依然自轉和公轉,地球依然把溫暖的春天送回人間。倒是人,擁有的確實是最后的反省機會:無論個體和族群,怎樣做才能安然地活著。
地球溫度的上升很大程度是人類的過錯,二氧化碳的過量排放致使局部地區乃至全球性的氣候異常,人類的家園危機四伏。千百年來,人類唯我獨尊的丑陋思維使伴生動植物不斷滅絕,不但威脅現存物種的延續,也給自己掘出了萬劫不復的巨大陷阱。許多病毒在人類遠遠沒有出現之前就生存在地球上,不少病毒比恐龍的歲數還要大。人類來到這個地球上只能以百萬年計算,而這些病毒的年齡已經超過億年。他們躺在潘多拉魔盒中沉睡,貪婪的人類如果非要打開這個魔盒,必自食其果。野生動物就是這些病毒的宿主,比如蝙蝠、果子貍、竹鼠等等,它們與病毒能和諧相處,人類一旦動了別人的晚餐,大自然立即瘋狂報復。每一種動物來到地球上都有理由,都有生存的權力,人類用自己的生存權去抹殺異類的生存權,冥冥蒼天必給人類貪婪無度的嘴巴以巨大的回饋:只要你敢吃,就讓你付出血的代價。中國是一個早已解決溫飽的國家,最近三十年來,食物的富足使十幾億人口擺脫了饑餓,靠狩獵野生動物果腹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可是少數富豪和獵奇者依然把食用野生動物作為口服化境,標榜自己有錢能顯擺,往往少數人的無知與愚昧野蠻,使國家和民族陷入危險之中。食用野生動物不但是一個道德概念,還是一個危害人類生命安全的法律概念,是長在國家肌體上的惡性腫瘤,不摘除它,人類恐難有祥和的日子。
病毒是人類的災星,歷史上已使數以億計的生命化為枯骨,己亥末庚子初的新冠肺炎標新了災難史記錄,流行速度之快、感染地域之廣,前所未有。這種病毒給人類社會帶來的苦難是觸目驚心的,它使武漢人經歷一次煉獄般的生活:感染者深陷呼吸的艱難,逝者帶來的撕心裂肺的呼喚,生者禁錮在家里焦躁地等待門外的陽光……武漢的經歷是21世紀開始20年來中國人最悲傷的歷史,它迫使一個國家啟動龐大的社會動員機制,將一切可以應用的手段和物資找出來與這該死的病毒決戰,目的只有一個——救人。生命無法以任何形式的價格計算,這是人類文明的最高標志。也正是這個原因,災難考驗了局內和局外的所有靈魂。
年幼的女兒在母親的遺體前聲嘶力竭地呼喊:“媽媽不要拋下我!”這位媽媽很年輕,是一位醫生,她肯定不想死,她的孩子還小,她必須陪伴女兒長大成人。看到這個畫面不流淚的人,不能言善。每個人的生命都如此寶貴,對于一個家庭來說,個人的生命其實并不僅僅屬于自己。可是這位年輕的醫生、母親卻在救人的路上倒下了,所有贊美都無法挽回這個生命的離去,無法彌合這個家庭的殘缺,我想到的是:她走了,女兒的人生之路怎么走?直面死亡不計后果,是這些犧牲者最值得歷史記住的精神和文化內涵,中華民族之所以數千年延續至今,正是由這種精神鑄造的結果。喊幾聲口號不會改變歷史發展的方向,空洞的口號喊得多了,除了引起民眾的憤慨,還會割出帶血的文化新傷。面對這位逝去的年輕母親,社會必須立即想到的是:讓這位沒娘的女兒接受良好的教育,撫平她的心靈創傷,讓她像母親一樣成為一個善良、對社會有用的人。如果當時就公布一個救助和撫養方案,比你喊一萬句口號更具公信力,更能激發民眾的斗志。
不要小窺這些柔弱的肩膀,這個春天,她們是民族的脊梁。在昆明長水機場,出征湖北咸寧的云南醫療隊中半數以上醫護人員是女性,他們中不乏90后、00后,她們擁有姣好的容顏,甜蜜的愛情,幸福的家庭。擁抱、吻別、揮手、回眸,然后遠去。此后,這種場面在這個地點出現過7次。今天是三八婦女節,與醫療隊一同出征的同事昨夜在一個不到50米的清潔通道中為109位醫護人員拍了肖像,平日她們戴著口罩,穿著防護服,只露出一雙眼睛,“長得都一樣”。當摘下口罩拍照,這位年輕的攝影記者眼里一直噙著淚花:那些如花的面龐傷痕累累,長時間佩戴口罩、穿防護服,她們的臉上布滿道道血痕。一個多月沒有化妝,一個多月倦怠的勞碌奔忙,帶傷的面龐依然透露出堅貞、剛毅的神色。這些肖像當夜在云南網、云南日報客戶端發表,成為今天網民們追捧的對象:“她們是這個三八節最美的女神!”她們不是希臘神話中的阿爾忒彌斯、雅典娜、赫斯提亞,她們不是中國神話中的女媧、洛神、九天玄女,他們沒有觀世音普度眾生的法力,她們就是一群平凡的女子。她們之所以被人們尊為神,正是她們平凡身軀上發出的人性光芒。
不要忘記那些在大難面前敢講真話的人,這個春天,講真話能夠拯救更多的生命,講真話人命關天。曹操在《對酒歌》中表達了他的治國目標:“耄耋皆得以壽終,恩澤廣及草木昆蟲。”這里的“耄耋”指的就是80至90歲的老人。84歲的鐘南山年列耄耋,卻依然像當年抗擊非典一樣,最早奔赴武漢,他成為年齡最大的逆行者。作為臨危受命的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鐘南山實地了解疫情、研究防控方案、上發布會、連線媒體、解讀最新疫情。在接受央視采訪時他沒有絲毫隱瞞:肯定存在人傳人。他是院士,社會地位比李文亮醫生高,沒有人去訓誡他。但講真話被訓誡的李文亮感染新冠肺炎后,沒有實現他“拯救地球”的心愿,過早離世,年僅34歲,生命定格在庚子年寒氣逼人的初春。年步古稀的李蘭娟院士在抗疫中與那些一線醫護人員生死與共,她看到了民族精神的本質,提出青年人要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國家要將良好的待遇提供給對社會做出重要貢獻的人,而不是向有高報酬演藝明星看齊。這個災難,讓人們悟懂了一個國家真正的核心價值觀,只是讓一個普通的老太太說出來,沒有足夠的力度。我們知道病毒會傳染,但我們不知道它什么時候來。人類的智慧無與倫比,但擅于變幻的病毒每次都讓我們措手不及。這就要求我們的社會必須有一批不人云我云的明白人。
春風拍打著窗欞,從晨至暮,未有停歇。我們經歷的磨難只是歷史的一幕,沒有哪場災難能持續地肆虐下去,如這春風,當它停止勁吹的時候,大地便百花盛開,生機盎然。其實記錄災難并不需要宏大的敘事,天馬行空的夸張比喻,充滿媚俗和脂粉氣的華麗辭藻。記錄真實發生的事,輯錄充滿思想靈光的語言,給勇敢善良的逆行者一個真誠地點贊,向遭受災難的骨肉同胞投去悲憫的目光,給逝者獻一束緬懷的心花,給疫區同胞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比如捐款捐物),我們便干凈地見證和參與了這段歷史。在波及全球的災難面前,一個普通百姓能做的也只有這些。
“洞庭洞庭,我是滇池”
我們和中原人最大的不同,在于非常慣于攀登,包括我們的代步工具汽車。這個春節,最早離開昆明的“專縣上的”人,一直到二月底還困在山里。有一個同事的老家就在梅里雪山附近,春初山里還堆著厚厚的積雪。他們燃燒一種植物消毒,據說這種植物可以清潔宅院,當地人一直使用這種方法。那同事說,從昆明到老家,只帶了四只口罩,反復使用了20幾天,便拿到雪地上凍著,算是消毒。他在微信圈里說:“我要回昆明,需要一只口罩,但是買不到。”我回答:“你們整個地區都沒有確診病例,無須戴口罩。”他說:“路上不戴口罩要被查!”是的,我回昆明時,到處都是測體溫檢查是否戴口罩的人。
云南的神奇,其實就是大山制造的。我體驗過八百里秦川、燕京平原的平坦,哪怕在河套地區,都找不到云南這樣崔嵬的山脈。據說云南修筑一公里高速公路,所需費用是平原地區的三倍甚至更多。年輕時到成都讀書,坐成昆線綠皮火車,一千多公里路,估計三分之一是在隧道里穿行,尤其從大涼山到昆明一段,總覺黑洞洞的看不到原野和天空。大山將生活在這里的人們鍛造成鐵腳板,我在楚雄彝族山區做社會調查,看到過這樣的景象:一個背柴的老表吹著笛子跋涉在崎嶇的山路上,與他相遇,看到他滿臉都是汗水。這是我第一次體會堅韌這個詞的深刻含意,生活中的苦難,有許多化解的方法,比如煩惱時跳鍋莊舞、左腳舞、彈月琴等等,哪怕在負重的時候。這就是大山的性格。春初的這場疫情,其實對云南的極大部分地區影響不大,原因還是山。
數得出的幾個旅游勝地都被山包圍著:麗江、大理、西雙版納、德宏,要么在山麓的緩坡上筑城,要么被四面群山包裹得嚴嚴實實,就是省會昆明,也在群山的屏障之中,孫髯翁大觀樓長聯說得很清楚:“東驤神駿,西翥靈儀,北走蜿蜒,南翔縞素。”其實就是四座山脈:金馬山、碧雞山、蛇山(長蟲山)、白鶴山。與山為伍是云南人的日常,許多縣城修筑在半山腰,清早出門就爬山,更不要說生活在真正山區的各民族百姓:對面山路上的行人叫得答應,但是你要和他會合得走半天,爬山是云南人從小到大的一門功課。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怒江沿岸的三個縣找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平地,高黎貢山、碧羅雪山,乃至綿延至緬甸的擔當力卡山,將這塊土地切割成溝壑縱橫的巨型雕塑,江面到山巔的高差超過千米,谷底熱浪滾滾,山巔夏日猶寒,造訪山間的那些村寨,除了攀爬與流汗,別無他法。疫情期間,怒江的文友常發一些在扶貧村消毒的圖片、視頻,我就覺得這有些過度防范了:怒江至今沒有疫情,大山里的寨子大多與世隔絕,只要沒有外來人員,根本用不著戴口罩用藥水消毒。
昆明、大理、麗江、西雙版納四地的確診病例來源有二:外地游客的涌入(尤其是武漢游客);在湖北(尤其是武漢)務工的人員回鄉。1月22日得到的信息,從武漢入滇的人員已達3萬余人,滯留昆明、大理、麗江、西雙版納等地。但人們沒有想到的是,昭通市的確診病例緊跟昆明之后,昆明53例,昭通25例,10到15例的地區是西雙版納、玉溪、曲靖、大理,其余都在9例以下,迪慶和怒江兩州一直為零,全省累計確診174例,死亡2例,確診病例目前已全部出院清零。應該說,云南與疫情較重的地區相比,情況還好。省會昆明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比如公共交通停運,餐飲、娛樂、商場系統停止營業,小區出入實行嚴格的管理,機關單位在網絡上開會等等,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的漫延,云南基本守住了凈土。但我同意方方的說法:沒有勝利,只有結束。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我們失去了生命,170多人曾經經歷呼吸艱難等等折磨,我們投入抗疫的人力、物力是一個天文數字,真正的勝利,是這一切都沒有發生,而且不會發生。
與發達地區相比,云南整體上還是一個貧困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無法跟人家比。我看過江蘇“十三太保”的微信,人家的醫療隊中竟然有村級的醫院,此次出征援助湖北,裝備精良,恐怕云南的許多縣級、地級醫療單位也無法與人家相比,真是財大氣粗啊。但是云南有大山啊:大山錘煉了云南人勇敢頑強的精神,鍛造了云南人樸實擔當的涵養,云南以有限的力量馳援湖北,在這次抗疫中問心無愧。我們錢不多,但我們物產豐富,昭通的蘋果、紅河的芒果、麗江的土豆、元謀熱壩的蔬菜,甚至昆明的鮮花,都成為援助湖北同胞的物資,而且頗受疫區群眾的歡迎(原生態的)。再者,我們有人:截至2月24日,云南省共向湖北派出由重癥醫學、呼吸、感染性疾病、醫院感染控制、心理衛生、心內、護理、中醫、疾控等人員組成的10批工作隊1156人。其中:女性804人,博士29人,碩士97人,本科825人、大專及以下205人。我們奉獻了所能做到的一切,和其他省市一樣,云南人這次也表現出了以命相搏的英雄氣概。
湖北與云南有久遠的文化淵源關系。楚宣王、楚威王時期,楚國的疆土西起大巴山、巫山、武陵山,東至大海,南起南嶺,北至今河南中部、安徽和江蘇北部、陜西東南部、山東西南部,幅員廣闊,核心區域就是今日之湖北、湖南省,說得再小一點,就是以洞庭湖為中心區。公元前279年,楚頃襄王派將領莊蹻率軍通過黔中郡向西南進攻,經過沅水,向西南攻克且蘭,征服夜郎國,一直攻打到滇池一帶。黔中郡原曾為楚地,后被秦一度攻占,前277年,秦派蜀郡守張若再度攻取黔中郡和巫郡。翌年,楚不甘心失敗,又調集東部兵力收復黔中郡部分地區,重新立郡以對付秦國。因黔中郡的反復爭奪,莊蹻歸路不暢,便“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史記?西南夷列傳》),融入了當地民族中。關于莊蹻入滇的時間,史載有異說,《史記》和《漢書》的《西南夷列傳》列為楚威王時事,《后漢書?西南夷傳》則說是楚頃襄王時事。不管是哪種說法,莊蹻入滇的意義對于中國歷史,尤其是西南地區的歷史是巨大的,它不僅促進了西南地區的發展,同時也是中國多民族融合的象征。
據《世本》《古今姓氏書辯證》及《元和姓纂》等載,楚族出自顓頊之后,是指族源而言,楚族之直系祖先則應是季連。楚先民對自然的崇拜,主要表現對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雷電、風雨、祖先等的崇拜。戰國楚帛書提到的雹戲,就是對雷電化生萬物的偉大自然力量的崇拜,“帝俊生日月”,就是對日、月的崇拜,火正之為祝融,就是對火神、太陽的崇拜。當先民思維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對各種自然現象,加以概括和歸納,于是萌發出天地的觀念。戰國楚帛書說的“奠三天,辨四極”,說明祝融時代,楚之先祖已有天地觀念了,并予以祭祀。楚之先民祭天祀地,長盛不衰,故《漢書?地理志》稱“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楚人之如此“重淫祀”,楚地之如此多神話,恰是楚之先祖創造和發展了豐富多彩的原始文化的結果。這些風俗與文化,在云南的彝語支民族中幾乎被完整地保存下來,是稱“巫風楚俗”,這些文化風俗,就是莊蹻所率楚人帶來的,滇文化與楚文化水乳交融,創造出有別于其他地域的文化體系。今研究楚文化者,若到云南調查文化風習,應該有驚喜的收獲。
從歷史的角度看,湖北與云南還有“親戚”關系,鄂地大疫,滇人且能袖手旁觀?盡管自己也是受傷者,卻還拉衣裳墊屁股地捐錢捐物,盡自己的綿薄之力。有些舉動是本能的,不要說親戚關系,就是從同胞這個角度出發,也義不容辭。
楚國大夫屈原《離騷》曰:“路修遠以多艱兮,騰眾車使徑待。”“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轪而并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云旗之委蛇。”路途多么遙遠又多艱險,我傳令眾車在路旁等待;我再把成千輛車子聚集,把玉輪對齊了并駕齊驅;駕車的八龍蜿蜒地前進,載著云霓旗幟隨風卷曲。哦,這多像今日八方馳援湖北的景象。當云南的第一支馳援隊伍出發時,給湖北的電文就應該這樣寫:“洞庭洞庭,我是滇池,我來了!”滇池與洞庭湖,已經有2300年的交情,大疫面前,舍我其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