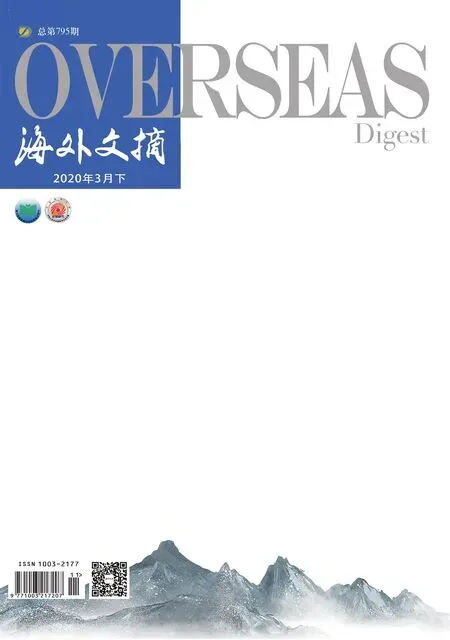清代傳教士《詩篇》中譯與文體變遷
韓沁妍
(南京大學(xué),江蘇南京 210023)
《圣經(jīng)》中的《詩篇》部分原是希伯來語詩歌,生動而夸張,最主要的修辭方式是押輔音的頭韻和雙關(guān)語,但這些只有在希伯來原文中才能體現(xiàn)。一旦被翻譯成各式的譯文后,效果便大不相同。19 世紀(jì)初,基督教傳教士才開始圣經(jīng)漢譯的工作,其中最有名的是馬殊曼與馬禮遜,俗稱“二馬譯本”,這兩者誰先誰后一直存在著爭議。
1“二馬譯本”與“中間文體”
以著名的《詩篇》第二十三篇為例,馬殊曼和馬禮遜二人都未脫離原文本。但比較而言,馬殊曼運用了許多看上去典雅的生僻字,而馬禮遜因為主張的是雅俗共賞,折中了文言和白話,因而用字更多,行文也更加流暢。并且由于是翻譯《圣經(jīng)》的早期,很多術(shù)語只能自創(chuàng),當(dāng)今通行的“天國”“福音”“使徒”[1]等等一系列詞匯其實都來源于馬禮遜譯本。也因此,馬禮遜譯本的影響相對而言更大,他的《神天圣書》(1823)被認(rèn)為是中國境內(nèi)出版最早的《圣經(jīng)》漢語全譯本。
不過馬禮遜譯本同樣存在不少問題。他的忠實原文是雙面的,有時是思想的客觀正確反映,體現(xiàn)在他不多加補(bǔ)充,比如將復(fù)合詞翻譯為完完整整的“饕者醉者”[2],沒有進(jìn)行道德批判。同樣也不省略刪節(jié),比如用“爾父之裸體,爾母之裸體,爾不可露之”字面直譯,而委辦譯本、施約瑟譯本和和合本這三個版本都省略了原文中關(guān)于父親的內(nèi)容。[3]這恐怕是由于儒家的倫理綱常影響,為使《圣經(jīng)》適應(yīng)19 世紀(jì)中國文人所推崇的儒家倫理。可見,彼時的馬禮遜譯本并不刻意適應(yīng)中國傳統(tǒng)文化。
另一方面,他追求的是通俗的白話文,采取一種中庸之道,用《三國演義》這樣的“中級”與“中間”文體來翻譯圣經(jīng),想要實現(xiàn)一種莊而不諧卻又通俗易懂的平衡。但是他通篇充斥著“也”“焉”等等,語句不簡練又太長,仍然深受西方長句子的影響。巧的是,馬禮遜這種雅俗共賞的“中間文體”恰恰位于中間位置,由此開始,清代《圣經(jīng)》的翻譯改寫越來越融入了刪節(jié)、補(bǔ)充等各種各樣的新方式。
2 新奇又傳統(tǒng)的漢譯形式
2.1英國傳教士湛約翰所翻譯的楚辭形式
在《中文韻律詩篇選輯》(1890)中,湛約翰翻譯了詩篇一至十九篇和第二十三篇,模仿了九歌體和西晉潘岳的《射雉賦》,是首部完全用中國傳統(tǒng)文學(xué)形式翻譯的圣經(jīng)。仍然以《詩篇》第二十三篇為例,他的翻譯為“耶和華為我牧兮/吾必?zé)o荒/使我甫青草苑兮/引靜水旁/蘇吾魂之困憊兮/我得安康/俾我行于義路兮/其名遂彰/雖過四蔭之谷兮/亦不畏傷/蓋牧與我同在兮/慰以杖鞭/爾為我設(shè)筵席兮/在吾敵前/曾以膏膏吾首兮/杯滿涓涓/我畢生得恩寵兮/慈祥綿綿/將居耶和華室兮/永遠(yuǎn)長年”[4]他以傳統(tǒng)楚辭體翻譯舊約詩篇,為清初《圣經(jīng)》中譯風(fēng)潮注入新鮮血液,關(guān)注到了中國的傳統(tǒng),獨具開創(chuàng)性。
然而,湛約翰的翻譯比較靈活,也比較模糊。其一,詩句的組合基本是按照詩篇的結(jié)構(gòu),并非機(jī)械地模仿騷體句式,而是靈活變化,比如《詩篇》第二篇。其二,在用典中,出現(xiàn)了《詩經(jīng)》《淮南子》等等,但《詩經(jīng)》本是儒家經(jīng)典,在此過程中又經(jīng)常出現(xiàn)“耶和”等圣經(jīng)用語,出現(xiàn)了以儒釋耶的矛盾現(xiàn)象。其三,用語的選擇方面,他用“郇”這個字來代替錫安山這一特定的猶太民族象征。還經(jīng)常用多個意思的詞語,比如“士師”就有兩種解釋,一個是建立王國期間的領(lǐng)袖稱謂,另一個是在王國時期之后,士師的功能只限于作審判官,裁決爭議的事。與其他翻譯版本相比,有的中文版直接是審判官的意思。可見這里湛約翰楚辭形式用語的選擇造成了模糊性,擴(kuò)大了不同解釋的可能性。
2.2鮑康寧所翻譯的古詩形式
鮑康寧曾經(jīng)在六朝古都南京學(xué)習(xí)過中文,他也有所突破,用中國傳統(tǒng)詩歌的樣式來翻譯詩篇。《詩篇精意》(1908)通達(dá)淺白,詩句多六七八字,接近官話口語。他在序中自評文章讓人一目了然看得明白。由此,他調(diào)整原文的節(jié)數(shù),由每四六或八句組成一段,來適應(yīng)中國的傳統(tǒng)。不過,他并非完全按照中國詩句的平仄來安排各個韻部的分配,只關(guān)注字?jǐn)?shù)規(guī)范而已。
仍然以《詩篇》第二十三篇為例,鮑康寧將之命名為“主為善牧”,并寫道:“全能上主是我牧人,千福萬安無不備;引到水旁青草安身,保養(yǎng)安慰免受累。行走義路他作先鋒,指示引導(dǎo)免走岔;主帶竿杖沿途護(hù)送,卽經(jīng)填墳也不怕。敵人面前主擺酒筵,再用恩膏抹我首;福杯慢溢流成泉源,慈悲恩寵更加厚。生前日日恩愛并隨,前后左右到長壽;救主親自一生相陪,樂住明宮到永久。[4]”
可見,與湛約翰的楚辭形式相比,鮑康寧的古詩形式意思高度概括,刪減更多,很多地方和原意相差甚遠(yuǎn)。但與此同時,在用詞方面,兩者相似點頗多。鮑康寧的翻譯里也偶爾會加上新約的解讀,或者把耶穌的名字“耶和”等等加在其中,一些“主”“受膏君”等等代表耶穌的固定詞還是未變。除了引用新約的詞語比如“圣靈”之外,為讓中國讀者感到熟悉,亦使用了中國民間宗教的神靈用語,甚至《詩經(jīng)》《尚書》等等。比如第一百四十八篇《萬物讃主》中的“云漢”便語出《詩經(jīng)·大雅·蕩之什·云漢》,指的是天河,甚至還有第一百五十篇“讃主到底”這樣任性的篇名,其中“八音克諧”出自《尚書·堯典》,可見文化融合的矛盾感。總之,鮑康寧的譯文并不固守舊約詩篇原詩的節(jié)數(shù)、結(jié)構(gòu)或用語,而只是簡化成中國傳統(tǒng)詩的結(jié)構(gòu)而已,并且出現(xiàn)了多重雜糅的矛盾感。
3 結(jié)語
對比湛約翰和鮑康寧的翻譯,可見湛約翰用楚辭形式,相對而言比較靈活,依據(jù)了原意,而鮑康寧古詩形式更加拘泥于形式套語,改變了節(jié)數(shù)甚至內(nèi)容,導(dǎo)致和原意相差更大,由此可見不同文體以及不同形式的靈活程度,對《圣經(jīng)》中譯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
清代漢譯《圣經(jīng)》出現(xiàn)楚辭和古詩的形式,不禁讓人疑惑,清代已經(jīng)是小說為主體,又為何還要復(fù)古到古詩乃至楚辭,出現(xiàn)一種既新奇又詭異的融會矛盾感。筆者認(rèn)為《圣經(jīng)》中的《詩篇》部分由于是“詩”這一獨特的形式,而中國當(dāng)?shù)匚幕械摹霸姟眲t是楚辭、古詩等等,因此“中譯”這一過程除了內(nèi)容的搬運外,“詩”這一形式也需要有所轉(zhuǎn)換,需要由西方的“詩”轉(zhuǎn)化為東方的“詩”。
不過,這一轉(zhuǎn)換的過程卻忽略了東方和西方“詩”的差異。想來詩經(jīng)、楚辭以及中國古典詩詞往往都是古人真情實感的抒發(fā),而《圣經(jīng)》里雖說圣詩本身是充滿美感的,但一旦拘泥于以固定形式固定套語的改寫轉(zhuǎn)換,則充滿著說教意味和念經(jīng)感,導(dǎo)致一種奇怪的不通感。湛約翰和鮑康寧的《中文韻律詩篇選輯》、《詩篇精意》只是重于形式,一味地進(jìn)行勸信和布道,并非真正的肺腑之言,并未從真情這一中國古典詩詞的真正出發(fā)點出發(fā),也就不能引起共鳴,從而造成巨大影響。
但是反過來,《圣經(jīng)》中很多屬于智慧文學(xué),最重要的特點就是說教性,直接傳達(dá)的是處世哲學(xué)與三觀。或許中國詩一向與宗教相離甚遠(yuǎn),總是若有若無地體現(xiàn)出宗教思想,而西方詩形象夸張卻又思想深廣,這二者其實各有千秋,不同文體碰撞所造成的融會矛盾感又何嘗不是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