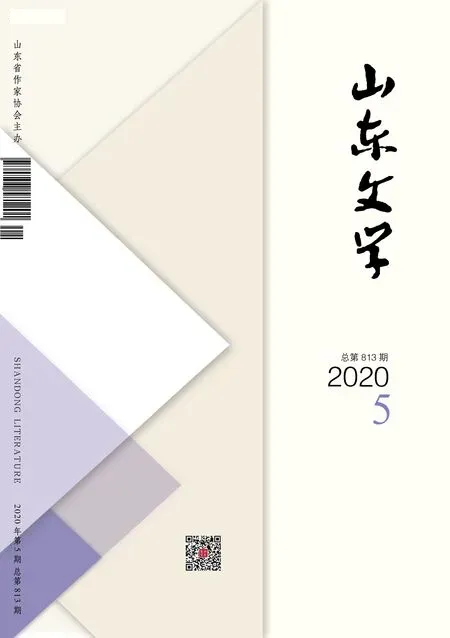家園意識(shí)的詩學(xué)空間解析
——王二冬城鄉(xiāng)主題詩歌的解讀與思考
康建軍
一般認(rèn)為,家園意識(shí)是地理空間遷移的心理學(xué)產(chǎn)物,故鄉(xiāng)與異鄉(xiāng)就是距離和空間差異的產(chǎn)物,從一個(gè)熟知的地方到另外一個(gè)有風(fēng)景的異國或他鄉(xiāng),會(huì)極大激發(fā)空間感覺上的巨大差異,并將這種差異恰如其分地表達(dá)出來,就是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原動(dòng)力之一。
90后詩人王二冬憑借對(duì)文學(xué)的熱忱和高質(zhì)量的創(chuàng)作,活躍于當(dāng)今詩壇。其作品重點(diǎn)關(guān)切當(dāng)下中國城市新職業(yè)者(快遞從業(yè)者、外來務(wù)工人員)、鄉(xiāng)村現(xiàn)狀(留守老人、鄉(xiāng)村就醫(yī)、耕地毀壞)等現(xiàn)實(shí)問題。筆者試圖通過其對(duì)于城鄉(xiāng)的二元化空間認(rèn)知,以及目前其致力于寫作的城市方位,具體分析詩人感受城鄉(xiāng)斷裂的切身之痛、體味詩歌創(chuàng)作的追問之思考,解讀其詩歌如何以飽蘸感情之筆,書寫真實(shí)的城市快節(jié)奏與非虛構(gòu)的田園。
城市或鄉(xiāng)村:撕裂視野里的精神家園
文化地理學(xué)者克朗認(rèn)為,家園是一個(gè)非常重要的地理單元和文學(xué)單元,家園在描述技法上可以寫實(shí)也可以虛寫,在空間表達(dá)上可以擴(kuò)大也可以縮小,因?yàn)樵谖膶W(xué)家那里,更多的是需要進(jìn)一步強(qiáng)調(diào)和表達(dá)這種空間結(jié)構(gòu)模式對(duì)于書寫的左右,也即在創(chuàng)造“家”的過程中,文學(xué)思想、文藝思維的重要性。
王二冬生長的村莊叫東河西營,據(jù)縣志中趙氏譜書記載,始于明永樂二年(1404年),由山西洪洞縣遷徙海豐城東立家園,也是一個(gè)有掌故的老村落。所以舊時(shí)有楊延昭設(shè)立營帳的傳說,也有相傳“明永樂二年,始祖攜銅佛五尊,自汴梁遷徙海豐城東二十里立村”之說。他的一首題為《小年》的詩即把空間場景置于東河西營這一有著特殊意蘊(yùn)的地理場所,“從今夜啟程返鄉(xiāng)的人,會(huì)不會(huì)/在別家的炊煙中,聞到祭灶的味道/在東河西營,我的祖母也一定拖著/發(fā)木的腰身,一遍遍清掃塵埃和往事/祖父不用下坑了,他應(yīng)該站在某個(gè)角落/等待被擺上供桌的邀請(qǐng)函/他的一生都是小年”。詩行中對(duì)于時(shí)光電掣而去的飛逝與追悔、對(duì)于祖父輩這一具有鮮活農(nóng)村意象的表述,都顯示了詩人回望的空洞與無底的絕望,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農(nóng)村的空心與悵惘:“如今,大年將至,小年仍緊追不舍/像一只困獸,困在彼此的命中”。
就具體的詩歌文本所創(chuàng)造的詩學(xué)空間而言,空間詩學(xué)在這里兼具地理空間與文學(xué)的交叉和融合,地理學(xué)(所營造的)空間無疑是真實(shí)的地理環(huán)境,而文學(xué)(所營造的)空間無疑是作家筆下描述出來的地理環(huán)境,同時(shí)地理詩學(xué)又是詩學(xué)理論中關(guān)于空間(而非時(shí)間)的一條橫軸。正如米歇爾·柯羅所言:“地理詩學(xué)的術(shù)語似乎一方面可以用來指一種詩學(xué)——一種關(guān)于文學(xué)形式的研究,打造地點(diǎn)的意象;另一方面也可以用來指一種詩學(xué)理論(poietique)——關(guān)于把文學(xué)創(chuàng)作與空間聯(lián)系在一起的關(guān)系的思考”。
所以在王二冬的很多詩里面都會(huì)出現(xiàn)“東河西營”四個(gè)字,甚至有《東河西營往事》。東河西營可以說是王二冬在發(fā)力時(shí)候的文學(xué)原點(diǎn),能夠幫助其矯正方位。王二冬自己也說,無數(shù)故事發(fā)生在文學(xué)意義上的東河西營,但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這些事情屬于別的村莊還是東河西營,已經(jīng)不再重要。只要你認(rèn)可這個(gè)文學(xué)方位,整個(gè)中國、整個(gè)世界、整個(gè)宇宙的故事就都可以在東河西營發(fā)生,找不到或回不去故鄉(xiāng)的人,也可以把東河西營當(dāng)作自己的村莊,直至當(dāng)作心靈的精神家園。
人總是會(huì)被故園拋棄的,所以現(xiàn)在的一切根本無法回到過去的樣子。因此作家們通過這種書寫結(jié)構(gòu),創(chuàng)建了意念中的“家”的概念,而這個(gè)新創(chuàng)造出來的家園,實(shí)際上只是充滿了對(duì)過去的回憶和追想,并不能是真實(shí)的家園,甚至都感受不到原始的真正味道。但不管如何,這種“家園感”的書寫原動(dòng)力,一直以來受到不同國度、不同時(shí)代文學(xué)家的密切關(guān)注,從而成為一種“原型空間”的寫作模式。
《如果大海還未平息》書寫了詩人在異鄉(xiāng)的思念,想起了村莊、莊稼、麻雀和妻子,詩里面寫麻雀是連接天地的音符,這種只有在寧靜的鄉(xiāng)村才會(huì)出現(xiàn)的場景,是詩人靈動(dòng)的比喻,把麻雀在電線上的躍動(dòng)與撥動(dòng)寫得惟妙惟肖。“那不是為我送行的隊(duì)伍/嗩吶也不要先于麻雀的翅膀響起/我太愛這些小東西啦,連接天地的音符/總在我沉默的時(shí)候一驚一乍/又在我不安的時(shí)候端坐如佛/還是笑好了,不要破壞了異鄉(xiāng)人的心情/他們還有很遠(yuǎn)的夜路要走”。人生的路很長,故園又太遠(yuǎn)。空間的凝練,時(shí)間的壓縮,把詩人內(nèi)心的大海一樣起伏的波瀾,落在紙上,如同沉郁的家譜。
王二冬在大學(xué)期間自印了詩集《沒有回家的馬車》,于2012年進(jìn)行了幾場不小規(guī)模的作品研討和座談。劉廣濤教授特別鐘愛其《與野草的斗爭》,與臧克家的《三代人》進(jìn)行了比對(duì),“孩子,在土里洗澡;爸爸,在土里流汗;爺爺,在土里埋葬”,認(rèn)為全詩是對(duì)農(nóng)民生活狀態(tài)的關(guān)注,是一首沉甸甸的詩,從曾祖父到父親都表現(xiàn)了民族文化中的愚公精神,既有歷史的厚重感,又充滿了現(xiàn)實(shí)的氣息;體現(xiàn)了詩人責(zé)任意識(shí)的《我的村莊正在消失》寫的是家鄉(xiāng)要變成經(jīng)濟(jì)開發(fā)區(qū),童年時(shí)的老樹、老房子將被夷為平地,還有那片墓地也要一起被遷移。詩人對(duì)故鄉(xiāng)的愛從整本詩集里都能體會(huì)得到,而家鄉(xiāng)被消失的痛楚和無奈也讓詩人情感噴涌而出卻又無可奈何地坍塌倒地。
透明或隱密:地理坐標(biāo)中的心理原點(diǎn)
熟悉的地方?jīng)]有風(fēng)景,一地總有一地的局限。對(duì)于身邊事物的鈍感,會(huì)導(dǎo)致作家創(chuàng)作源泉的枯竭。任何作品毫無疑問地會(huì)有這樣或者那樣的局限,就是在空間和時(shí)間上進(jìn)行創(chuàng)作的乏力感,在故鄉(xiāng)與異鄉(xiāng)抉擇上的沖突感,會(huì)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作品的文學(xué)性。
其實(shí)在2010年讀大學(xué)之后,王二冬的寫作就呈現(xiàn)了一種自覺創(chuàng)作的高產(chǎn)狀態(tài),聊城大學(xué)附近的小飯館和小酒館,在菜市口的美食街上,在王氏羊湯、老漁夫石鍋魚、金濤小海鮮、蓮香閣……這些美食的熏陶下,高度亢奮狀態(tài)下的詩人,寫出來一首又一首佳作,不時(shí)地進(jìn)行心靈的叩問。
《大夢》是王二冬的一首只有四行的短詩,“夢見一些人,夢見一些/逝去的人,夢見一些終將逝去的人/悲傷襲來。淚水若鳥的翅膀/一不留神就飛出靈魂”,只是簡單地把夢陳述出來,卻把夢里的淚水都寫了出來。那些逝去的人和終將逝去的人,是時(shí)間的兩個(gè)維度。詩人在這里巧妙地把前后的時(shí)光壓縮到這一個(gè)夢里面,作為承前啟后的夢境,淚水會(huì)飛,那也是在夢里,因?yàn)槌赡耆说氖澜缋铮M會(huì)有輕彈之白日淚水?除了借夢和托夢,哪里會(huì)有痛哭的理由和可能?
地處山東省最北、渤海西岸;無棣水為禹疏之導(dǎo)河溝盤河,亦名老黃河,三代以前是禹貢九河之一。經(jīng)過黃河的多次漫溢,王二冬能看到的縣城的溝盤河,其實(shí)是現(xiàn)在在無棣縣黃柏嶺以下流入渤海的馬頰河的一個(gè)支津,現(xiàn)在的馬頰河在無棣縣城西,追溯到上游,是河南省濮陽縣金堤閘,這條河,恰恰經(jīng)過王二冬所在的大學(xué)——聊城大學(xué),在跨越聊城大學(xué)東校區(qū)和西校區(qū)的校內(nèi)彩虹橋上,王二冬可以俯視這條河,是如何不舍晝夜,從他的母校聊城大學(xué),奔騰不息地流向他的故鄉(xiāng);或者如果時(shí)光可以倒轉(zhuǎn),他也可以懷想那個(gè)童萌的孩子,目光所及之處,時(shí)光和河流都倒流,流到上中游的聊城大學(xué)。
社會(huì)科技與交通的飛速發(fā)展,現(xiàn)代人的“家園”日漸失落,那種由“居家”帶來的穩(wěn)定感、確定感和溫暖感愈益消失,因此,現(xiàn)代人的心理有著回歸家園的渴求。家園不僅是物理家園,更是一種文化歸屬感,而這種歸屬感正可以由地域文化所提供。《壩上篝火》是詩人寫空間外景的一個(gè)習(xí)作,承德的北方草原綠草如茵,火苗一樣晃動(dòng)的草原,是大風(fēng)的產(chǎn)物。沒有什么不會(huì)被生命的利刃收割:“壩上的火焰是綠色的,野草/不需要木頭,從大雪降落時(shí)燃燒/云朵是上蒼懸在人類頭頂?shù)膽n傷/黃昏是短暫的鋪墊/像利刃出鞘時(shí),那瞬間的溫暖/只有跳躍的心和上升的靈魂才是火焰”,肉體和靈魂是分開的,是燃燒過后的灰燼。
維拉·凱瑟發(fā)表于1925年的《教授的房子》,通過在古老高原與現(xiàn)代校園、鄉(xiāng)村與城市等場景的不斷轉(zhuǎn)換,解構(gòu)隔絕于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之外的烏托邦,想象和建構(gòu)“雜糅”流動(dòng)的第三空間,并通過圣彼特教授的歐美雜糅身份,探索文化交流、文化互動(dòng)的第三空間。《B13D區(qū)》是詩人寫自己在辦公大樓的場景以及內(nèi)心感受。對(duì)于所有的公司職員而言,每天絕大部分的時(shí)間都與辦公室、會(huì)議室、格子間為伴,而所有的信函、包裹的地址也無一例外地書寫著:“請(qǐng)記住我的位置:京東大廈/B12D區(qū),旁邊是休息室和飲水機(jī)/胸悶時(shí),就使勁敲打鍵盤/想象是馬蹄聲從草原傳來/那也是我的憂傷,請(qǐng)記下來/無法回到地面撒野,也無法掙脫/這透明的囚籠,去飛翔”。可以想見,身體被囿于幾個(gè)平方米之內(nèi),但是詩人的情思卻無法束縛,精騖八極、神游萬仞。其有節(jié)奏的鍵盤敲擊聲與無法脫韁之馬的馬蹄聲,都被解讀為對(duì)于自由不能獲取的憂傷,無法撒野,也無法掙脫:“連寫給天空的信也尋不到地址/沒有一朵云在風(fēng)中把遐想簽收/當(dāng)我絕望,我的重量就是這建筑/砸進(jìn)大地的重量,哦,悲傷/原來你也可以用深度去衡量”。悲傷是有重量的撞擊,所以才會(huì)有心疼的感覺。
對(duì)于城市空間的延展上,巴什拉自問自答了一個(gè)問題:“我們能夠用什么方式把外在空間的宇宙無垠感,賦予在這個(gè)城市空間上?”外在空間的無限延伸,與城市空間的日漸逼仄,形成了鮮明的對(duì)比。巴拉什把大城市當(dāng)成了一片擾攘不休的海洋,如果車水馬龍的城市成為一種噪音時(shí),“我會(huì)盡力從中間聽出雷鳴的聲音”,讓心靈回歸大自然,就如同年輕詩人伊馮·卡護(hù)形容城市的詩句:“空洞海貝里面/傳來的喃喃私語”。
創(chuàng)意或還原:詩歌技巧論的辯證分析
人和空間存在著流動(dòng)性的關(guān)系,這種流動(dòng)性也造成了文學(xué)創(chuàng)造的萌動(dòng)。此處與彼處的景觀差異,以及人群的外在差異,都造成了文學(xué)創(chuàng)造的出口。因而不同的文學(xué)作品里,都賦予空間關(guān)系不同的意義。如對(duì)哈代《德伯家的苔絲》中的“鄉(xiāng)野景觀”,荷馬《奧德賽》、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等的解讀,都會(huì)發(fā)現(xiàn)其中初始的原生心態(tài)——“家園感”(sense of home)。這種家園感是一種介于逃離與回望、摒棄與追思的復(fù)雜情愫。
當(dāng)人生的軌跡轉(zhuǎn)圜到首都北京時(shí),王二冬的詩意與詩藝又得到了進(jìn)一步的提升,這反映在其詩歌《母親,北京下雪了》中,他以傾訴的方式,把在帝都的見聞,條分縷析地念叨給母親聽。那些陽剛的冰涼的建筑,那些渺小的溫暖的人們。北京的文化符號(hào)與文化意蘊(yùn),作為一個(gè)新的地理空間和情感空間出現(xiàn)在詩人筆下,“北京下雪了。紙團(tuán)般揉在一起的城市/有了舒展的氣象,老街巷是長長的粉筆/給天空的問候?qū)懼匦?聽到骨頭和磚頭碰撞的聲響/你知道嗎母親,北京的雪/跟東河西營的不一樣,它們一落地/就被城市吞噬的一干二凈”。在詩人的囈語里面,藐小如同廢紙團(tuán)一樣的人,無處不在,但是跟歷史時(shí)期詩人與知識(shí)分子的被揉搓乃至被蹂躪和踐踏不一樣的是,更多的是個(gè)人志愿在宏大的歷史空間下的手足無措。這種拋棄感和被忽略感,使得詩人想要的文化追求實(shí)現(xiàn)不了。當(dāng)然這些也是柴米油鹽醬醋茶七件事的羈絆,讓詩情畫意如同鏡花雪月,可望而不可及。在人生里面,想要實(shí)現(xiàn)的夢想太多,但卻無暇照應(yīng)每一個(gè)少年時(shí)的豪言壯志。這里面當(dāng)然有城鄉(xiāng)二元的對(duì)立、對(duì)抗,以及最終對(duì)話、和解和妥協(xié)的問題:“這不是我的北京,村里/那條大樹參天的老路才是我的長安街/它會(huì)擁抱每一場雪,每一個(gè)人/都可以在上面打滾。你還記得嗎母親/有一次雪花將你的頭發(fā)染白/仿佛年老的你從時(shí)間深處走來/這一切并不遙遠(yuǎn),我們每一個(gè)人/都逃不出歲月,曾經(jīng)向我們妥協(xié)的/都會(huì)一一反抗”。每個(gè)人都有自己的精神王國和內(nèi)心圖騰,在詩人的文藝性創(chuàng)意和寫作實(shí)踐里,時(shí)空的轉(zhuǎn)圜,如同大雪的飄忽,令人不可捉摸但是又感同身受。詩行里面充滿著生命的奮爭與不甘,同時(shí)又充滿著生命的妥協(xié)與掙扎。在北京的大雪里面,山河染得皆潔白,在內(nèi)心結(jié)成花朵形狀的霜凍與冰涼,這種輕巧,也讓人在冬天里看到希望的詩句。
但是在文學(xué)作品中出現(xiàn)的故鄉(xiāng),一定不是王二冬所生活過的那個(gè)有著煙火氣息的東河西營了,詩人如何努力,也無法回到那個(gè)喜怒哀樂具有鮮明色彩的東河西營,回到那個(gè)人與人與自然與萬物和諧共生的東河西營,詩歌存在的最大意義在于,構(gòu)筑了一個(gè)可以棲息的心靈樂土、精神家園。正如王二冬所說,“人的一生中始終有兩種力量在激蕩,一種催著我們?nèi)ミh(yuǎn)方,一種帶著我們回原鄉(xiāng)”。這與莫言先生筆下的高密東北鄉(xiāng),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又如雨果的《悲慘世界》中對(duì)巴黎窮人窄街小巷與城市通衢大道進(jìn)行了辛辣的對(duì)比,而波德萊爾和福樓拜作品中的“浪蕩子”(flaneur)形象與現(xiàn)代城市景觀的格格不入但卻真實(shí)存在,諸如此類對(duì)于家園感這一素材的把握和重構(gòu)等,都讓文學(xué)作品對(duì)于生活的二次演繹,顯得文字精彩而富有新意,由此形成了別具一格的家園感系列文學(xué)作品創(chuàng)作。
這種思維在《我的大雪》里也有所體現(xiàn),說明詩人開始自覺地運(yùn)用了諸多的寫作技巧。黑洞一樣吸引人的空間,“沒有雪的北京,像一個(gè)巨大的窟窿/風(fēng)分別來自地下和天上/在人間形成寒流,冷冷地吹著”。這種地點(diǎn)與空間的置換或者叫做偷換,在詩人個(gè)體的感受那里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詩歌中很多巧妙的比喻,以及通感似的延伸,都反映了詩人的自覺寫作與意識(shí)覺醒。“烤紅薯的大叔,睫毛上落滿冰霜/仿佛遙遠(yuǎn)的枝椏為春天儲(chǔ)備雨水/清潔工老王的手指凍得發(fā)紫/是每一個(gè)早晨最先燃燒的火焰/開出租的小山東喜歡汪峰/還未醒來的歌聲像極了村莊的雞鳴”,這種對(duì)“小人物”的刻畫,是自覺為之的、貼近最基層人們的生活的句子,其感受非常接地氣,運(yùn)用排比、比喻與通感的手法也非常成熟和科學(xué),反映了詩人感同身受地去體驗(yàn),也是身體對(duì)物極必反的寒意的抵抗,非常有生活氣息,寫的是在京城里底層勞動(dòng)者的眾生相,而對(duì)于一個(gè)不特定故鄉(xiāng)女孩的描寫,用工筆白描的手法,寫社會(huì)的公平與正義之思,讀來讓人振聾發(fā)聵:“其實(shí),我的生命中一直有一場大雪/不停飄著、飛著、旋轉(zhuǎn)著/我的大雪是一個(gè)來自東河西營的女孩/她的身體在月光下白如雪/被無數(shù)雙手摸著摸著就化了/只有風(fēng),只有被風(fēng)開過刃的陽光/照著我也照著沒有大雪的人間”。在詩歌中,時(shí)間和空間的凝練與壓縮,體現(xiàn)了詩人運(yùn)用詩藝技巧的嫻熟。而對(duì)于生活的體驗(yàn),是對(duì)那個(gè)鄉(xiāng)村女孩生命困境的一個(gè)總結(jié)與解剖。陽光的利刃,當(dāng)然會(huì)割傷每一個(gè)人;在詩歌里面,也不缺乏跌宕的生命。
米歇爾·福柯說“空間是一種通過權(quán)力建構(gòu)的人為空間,是權(quán)力機(jī)構(gòu)控制民眾的一種方式”,這也點(diǎn)明了空間不是僅僅具有單純的物理屬性和物質(zhì)屬性,同時(shí)兼具人文屬性和社會(huì)屬性,并且后者可能更多地影響了人文空間。
王二冬在接受采訪的時(shí)候說,我們的一生都走在還鄉(xiāng)的路上,鄉(xiāng)愁是一個(gè)詩人不可或缺的氣質(zhì)。摩爾(G.E.Moore)也說過,在這個(gè)世界上,最有價(jià)值的東西是人與人之間交往的樂趣和物質(zhì)的生活……這兩者是社會(huì)進(jìn)步的最終目的,也是合理的目的。在詩人的字里行間,充斥著冰凌一樣堅(jiān)硬而又柔軟的孤獨(dú),那些突如其來的孤獨(dú)、暗涌,莫名其妙的死亡的恐懼都如同“風(fēng)中的馬匹”;那些漫天飄零的雪花、那些乍暖還寒的春天都如“風(fēng)中的馬匹”;那些狂歡過后的虛妄、漂泊的孤單、人世的炎涼都如“風(fēng)中的馬匹”……在詩行里面,讀者和作者,把彼此困于生命的長途跋涉中,難以出逃又難以遠(yuǎn)離。這個(gè)就是家園的魔咒,這個(gè)無法破除和無法消解的空間,是諸多優(yōu)秀文學(xué)作品的母體,也是文學(xué)回歸所必然依賴的空間建構(gò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