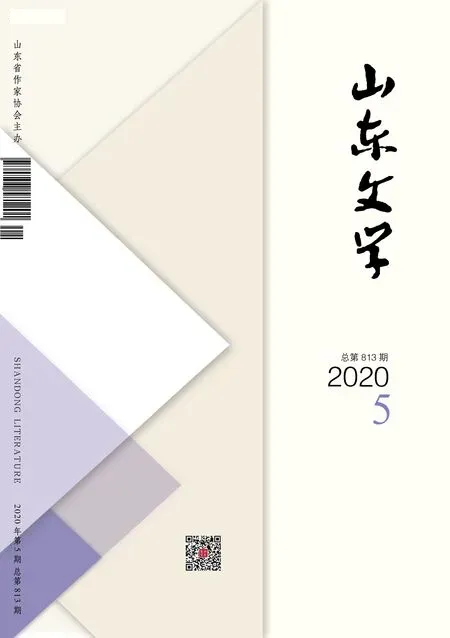不老的詩性表達
許 平
中國的漢字,已走過幾千年的漫長歲月,承載著我國悠久的文化內涵。漢字在幾千年的歷史雕琢中,歷經了甲骨文、大篆、小篆、隸書、楷書諸多字體的變化。詩詞就是用漢字碼成的文本中審美價值最高的一類作品,它簡潔、優美,把漢字所蘊含的審美潛能充分地發揮出來了。
這些年來,詩詞的圣潔,一直鮮活在我這個詩詞愛好者的心目中。故,我始終認為,寫詩作詞,是極不容易的,讀書,應該多讀讀詩詞。不知是我疏遠了詩詞,還是詩詞疏遠了我,總之,我看詩詞的時間是越來越少了。近年來,偶爾翻閱一下新潮的詩詞書刊,總有些難以言語的酸甜苦辣咸的味覺復合體。光怪陸離的新詩短句,奇裝異服的新生代詩人,令人目眩神韻,深而思之。
最近,“詩詞綜藝熱”的出現,再次把我拉回到詩歌的世界里。《圓桌派》《朗讀者》《中國詩詞大會》等文化類綜藝節目的出現也為綜藝界注入了新鮮的血液。這些綜藝節目創新了文化的呈現形式,應用互聯網思維,打破與年輕群體之間隔閡,增強節目的傳播效果。其原因不僅在于它新穎的節目形式和深厚的文化內涵,更在于它們喚醒了觀眾們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溫情與敬意。
正如語文教育專家所說,這一熱點與當代國人強烈呼喚傳統文化回歸的時代背景緊密相連,是國人文化自信的體現。其實,遠遠不止是《中國詩詞大會》等節目,這些年來還曾流行過漢字聽寫大賽、成語大賽……其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公眾并非一味喜歡流行,依然有著高層次的文化需求。當然并不是所有的傳統文化都會受到歡迎,這里還涉及到手段創新。但只要傳統文化找到好的表現方式,肯定受到歡迎,卻是毋庸置疑的。
綜藝作為影視節目,在視覺上本來就有著先天的優勢。而從詩歌吟誦、月下舞蹈再到五弦琵琶,視覺聽覺加之想象力的創作,讓節目形成了一種氣場。詩歌作為一種至純至美的作品,理應找到一種平臺:簡潔、純粹,不喧嘩。它在選擇它的受眾,也在選擇它的平臺,三位一體,互相聯系。
而這也是中國文化能繼承下來的根本原因:一個人或者一首詩歌、一個名字,都不是最重要的。從大眾的口耳相傳中,提煉文化的精髓,使它變得更為純粹,才是中華民族潛移默化的文化意識。
著名語言學家羅常培說過:語言文字是一個民族文化的結晶。這個民族過去的文化靠著它來流傳,未來的文化也仗著它來推進。從殷墟甲骨文到今天的漢字,祖先幾千年前創造的文字沿用至今。而《中國詩詞大會》比拼的絕不是記憶力,而是對審美、對感知、對體用的回歸,閱讀詩詞典范作品,可以在審美享受中不知不覺受到感染。這個過程就像社甫所描寫的成都郊外的那場春雨一樣,“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所以詩詞雖然距離我們有千百年的距離,但實際上它始終是活在現代讀者心頭的活的文本,這是它最大的現代意義。
不過,我還是懷念以前讀詩詞的情景,一個人安靜地翻開一本詩詞舊集,就如同微風拂過面頰,留下一絲淡淡的風痕。而心卻醉在長短句中,被它柔軟的美所陶醉。
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活著的是他的靈魂,是詩詞為他的靈魂支起了骨架。如劉屯田之《八聲甘州》,蘇東坡之《水調歌頭》,晶瑩剔透,格高千古,極得神韻。蘇軾《念奴嬌》,風格之豪放,酣暢淋漓,千古絕唱。辛棄疾《永遇樂》,豪壯之中略見悲涼,叫人拍案叫絕。
透明的詞句的誕生要求有透明的心境,無天真之心的人是絕不可能寫出天真之作的。故李煜的詞可稱得上“神秀”,韋莊的詞可稱得上“骨秀”,而溫庭筠的詞只能算是“句秀”了。尼采曾說過,“凡一切已經寫下的,我只愛其人用血寫下的書。用血寫書,然后你將會體會到,血便就是精義。”王國維則評價李煜的詞說:“后主之詞,真可謂以血書者也。”“故后主之詞,天真之詞也;他人,人工之詞也。”比較李后主之“人生長恨水長東”,韋端己之“洛陽才子他鄉老”,溫飛卿之“畫屏金鷓鴣”,境界高低自不言而喻矣。
我熱衷于重構現代詩詞理論批評框架時,向著詩詞藝術的境界,去探索,去追求,去逼近。那些優美的詩詞,那些淡淡的憂愁,總是在不經意間,悄悄叩開我心靈的一扇窗,讓我有幸聆聽到那穿空而來的天籟之聲。
詩是語言的藝術,詩人豐富的內心情感在詩中不是直接流露的,優秀的詩人總善于把一些看似平常的意象組合成一幅或絢麗或凝重的圖畫,從而傳達出一種動人心魄的感情。如戴望舒的《我底記憶》一詩,將承載著詩人記憶的一個個具體場景定格——燃燒的卷煙、筆桿、破舊的粉盒、頹垣的木莓、喝了一半的酒瓶,這些意象組合起來,便成了一幅色彩斑斕的圖畫。
當然,相比于《我底記憶》是一首純現代詩而言,《雨巷》取法晚唐詩歌。詩人以卓越的藝術想象力塑造了“雨巷”與“丁香姑娘”兩個核心意象,并通過情節的渲染與音節的復沓吟唱著對心愛之人可望不可即的企慕,使全詩感染上朦朧的浪漫色彩與悲情氣氛,可謂現代版的《蒹葭》。
無論是古體詩還是現代詩,它們都是一門語言的藝術,鑒賞詩歌是思想的思維的藝術,抓住“意”中之“象”去品味“意”中之“境”,揣摩“意”中之“蘊”,就走進了詩,走進了詩人的內心。
我想,每一個人詩人應承受寂寞,并且要甘于寂寞,能從沉寂中汲取養分。他雖然外在給人的感受是孤寂,但內心卻豐富充實。也許這樣更能產生詩的凝聚力。古語云“耐住寂寞大學問”。當然,詩歌不一定要有什么高深的道理,不講道理一樣可以是很好的詩。但詩還是需要一種境界,這種詩歌境界也是人的境界,要一生努力為之。
總覺得,有一天,當你經過人世的紛亂,顛沛,痛苦,失落,當你感覺生活欺騙了你,你就應該像一個詩人一樣用詩意看待生命,看待一切歲月無常。不管是“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豪放,還是“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州”的失意。有一種詩詞的境界是存在的,那便是從心靈滋生出來的,這種感覺,如魚飲水,冷暖自知。
詩詞,便是我飛臨古今的翅膀,那句句語詞,像片片美麗的羽毛。無論我們身居陋室,還是奢華的高樓大廈,閱讀詩詞,就會讓自己置身于靜謐的蒼穹之中,俯瞰世間萬物。
在詩詞中,我們會了解到祖先在生活中時時刻刻都注意與自然環境的和諧處,他們熱愛自然,而現在的人往往與自然漸行漸遠。讀詩其實也是讀人。讀古代詩詞的最高境界,就是最后透過文字來讀人。所以詩詞中境界最高的名家名作對現代人具有人格熏陶和境界提升的作用。
遠離了詩,就遠離了自省,弱化了趣味,鈍化了對美最初的向往,麻木了心靈中最本真的部分。真心實意親近古詩詞,用詩意抵消生活的粗糲,用壯闊開掘思維的閉塞,用精致磨洗庸常的瑣屑,知恥、知禮、知不可為,這就是詩,讓個人形端表正,擴大到社會,再潛移默化到人的內心,人人都能讀懂詩,也會被真正的好詩折服。北宋初期的汴京,人人醉迷于李后主的詞,并不在乎他的亡國之君的身份。《紅樓夢》中被人買來賣去的香菱同樣可以感知“渡頭余落日,墟里上煙”的韻味。
詩歌是每個中國人的內心記憶,能喚起國人共同的記憶和文化自信,學習古典詩詞,追溯漢字的歷史記憶,欣賞文字之美。詩詞發展跨越古今,詩詞精神燭照中華文明的各個時期。學詩是披沙揀金、去粗取精的過程。好的詩文總是人生最美好的部分、最真誠的感情、最真切的心志的反映。經過漫長時間的化學作用,去腐朽,凝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