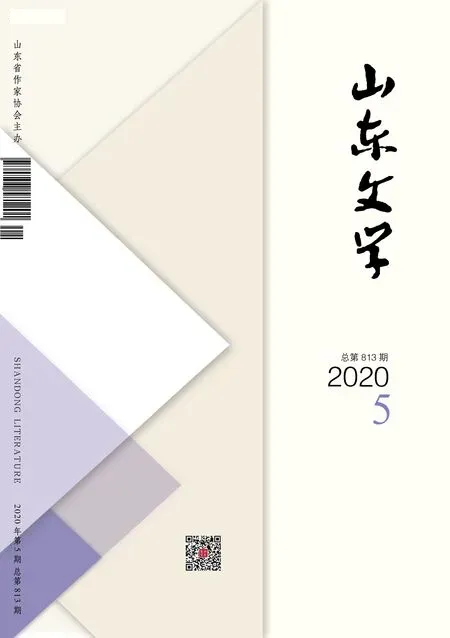兄 弟
留 待
大年三十晚上,劉曉芒從省城趕回了老家。他駕車剛駛上高速時心里窩著一股火,路上的空闊和冷清使他的火氣漸漸轉化成了焦慮。車里的暖風過于充足,他用手指摁壓鼓脹的太陽穴時發現額頭上滲出一層汗水。拐上青銀高速之后,他將轎車緩緩地停在路旁,下車脫掉了笨重的羽絨服。空氣里彌漫著清冷的氣味,眼前是遼闊平原,暗藍色的天空下,依稀看到茂盛的青色麥苗正在凜冽的寒風中瑟瑟顫抖。一股冷風順著領口刺到皮膚上,劉曉芒打了個寒戰,冥冥中有了種不祥的預感。他本來跟父母說好不回老家過年了,剛才陪著岳父岳母正準備吃晚飯,突然接到母親的電話。岳母還不到五點鐘便張羅著吃晚飯,為的是半夜十二點再吃一次。岳父拿出一瓶珍藏多年的“茅臺”。劉曉芒的妻子蘇楠不在家,他特想使家里的氣氛歡快一些。剛端起酒杯,手機響了。
母親哽咽著說,曉菖失蹤了。
曉菖是劉曉芒的弟弟。劉曉芒愈來愈感覺這個比他小十歲的弟弟純粹是降生到他家來要帳的。曉菖小時候經常生病,要死要活,父母半夜三更抱著他去醫院。時間一長,跟縣、鄉兩級醫院的兒科大夫們都混成了熟人。原以為曉菖是個養不大的孩子,沒想到上了初中之后身體反倒比同齡人更加強壯。他一強壯,父母的花銷更大了,因為新添了跟同學打架的毛病。打了人當然不能白打,隔三岔五便會有被打傷的同學的家長氣勢洶洶找上門來。曉芒的父母過日子非常節儉,家里不光種著自己的地,還租種了別人十畝地,父親常年跟著一個村里的小建筑隊打工。曉菖用那雙不安分的手在父母節儉的生活里扒開一道口子。劉曉芒大學剛畢業那幾年幾乎不敢回家,母親一見面便抱怨日子艱難。母親才五十二歲,頭發已經全白了。她不以為家里的捉襟見肘是因為曉菖惹是生非,話里話外讓劉曉芒覺得是在抱怨他給家里交的錢太少。當時劉曉芒還在跟蘇楠談戀愛,正是咬緊牙關冒充豪爽的時候,母親的話讓他的心像是被鉗子揪住了。
他安慰母親說,曉菖長大點就好了。
母親嘆了口氣,盼著吧。
曉菖成長的速度遠遠超出全家人的預想,初中一畢業便開始到處找工作。劉曉芒知道他退學并不是為了分擔父母的艱難。曉菖屬于天生不適合讀書的人,課本上的文字和學校里的規章都被他視為要命的羈絆。他懷揣著不切實際的發財夢想專門往大城市跑,一會兒在北京,一會兒又去了上海。母親見不著曉菖的影子,常常半夜被噩夢驚醒,醒了之后便哭。母親過了一陣子以淚洗面的日子,忽然又有種欣慰感,曉菖自從出外闖蕩,再也沒跟家里要過錢。
母親高興地給劉曉芒打電話說,曉菖真是長大了。
劉曉芒聽了只能苦笑著附和。他不敢把自己的擔心傳達給母親。他覺得曉菖長大了還不如沒長大,曉菖現在名義上是在外打工,實際上是像無頭蒼蠅一樣到處亂撞,誰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更不知道他結交了一些什么人。
今天春天,曉菖在劉曉芒家住了一個星期,說是要跟著朋友去深圳做生意,在省城倒車,順便看望一下大哥。劉曉芒對他的不期而至有點意外,又有點高興。他想趁機把弟弟留在身邊。劉曉芒在一家中外合資企業里當部門主管,給曉菖找份出力氣的工作還是能做到的。曉菖聽劉曉芒說到找工作時正仰著脖子喝可樂,劉曉芒的話還沒說完,曉菖將一大口可樂噴到了墻壁上,好像聽了個笑話。
曉菖用手背揩著嘴巴,笑道,你真會開玩笑,那么多機會等著我,我怎么會到你手下打工?
曉菖這兩年個頭躥得挺猛,人高馬大,打眼一看像健身教練。劉曉芒住的是七十平米的兩居室,猛不丁添了一口人,再加上曉菖走路時帶著橫沖直撞的勁頭,屋子顯得特別逼仄。蘇楠回到家連睡衣都不敢穿,去廚房做飯也是滿身正裝,像是隨時準備去上班。蘇楠是個愛清靜的女人,曉菖看電視上的足球頻道時卻將音量調到最大,還隨著電視里的球迷一起吶喊。蘇楠只能皺著眉頭躲進臥室。曉菖并不關心嫂子怎么看他,拿劉曉芒家當了賓館,居然用床單擦皮鞋,煙頭和果皮隨手亂扔,劉曉芒每天下班回到家總感覺像走錯了門。蘇楠身為大夫,有輕微的潔癖,面對曉菖制造的狼籍倒也沒當面抱怨,晚上臨睡覺時,她故作漫不經心地問,你弟弟什么時候走?
劉曉芒像蘇楠一樣盼著曉菖盡早離去,曉菖自己不說走,他又不好意思趕他。其實他也想讓曉菖多待幾天,以便找機會再勸他留在省城,結束無頭蒼蠅般的日子。曉菖本人似乎也不知道要在哥哥家待多久,每天睡到中午才起床,半夜里卻要坐在電腦前跟某個人視頻通話,如果對方是男的,曉菖的嗓門還算正常,對方若是女的,曉菖的聲音會異常興奮,嘹亮的說笑聲順著主臥室的門縫鉆進來,蘇楠只好用被子蒙住頭。更可氣的是,曉菖在電腦上看淫穢圖片,竟然將一張圖片設置成了電腦桌面。
蘇楠實在忍無可忍,對劉曉芒說,你該跟他談一談。
劉曉芒覺得確實應該跟他好好談一談。不光因為電腦上的淫穢圖片,更重要的是劉曉芒發現床頭柜的錢夾里少了一千七百塊錢,蘇楠的首飾盒里少了一枚戒指。一想到弟弟踏上盜竊之途,劉曉芒的脊梁骨嗖嗖冒涼風。趁著蘇楠上夜班,劉曉芒把正躺在床上玩手機游戲的曉菖拽到了客廳。曉菖可能是心虛,也可能是怪哥哥打斷了他的游戲,眼睛根本不看劉曉芒,斜躺在沙發上,只顧撅著嘴唇吐煙圈。在曉菖制造的烏煙瘴氣中,劉曉芒猶豫了好一會兒,不知該怎么說。他對曉菖一直很遷就,好像一旦惹得曉菖不高興,也就是惹怒了母親。劉曉芒知道應該疼愛這個被母親視若掌上明珠的弟弟,曉菖的舉止卻讓他有點煩。曉菖翹著二郎腿,左腳用大腳趾頂著拖鞋晃來晃去,就像電影里正在抽鴉片的二流子。
看到曉菖又點上了一根煙,劉曉芒有點生氣,你少抽點。
曉菖手中的香煙愣在嘴邊,冷笑道,你要是不愿讓我在你家待,就明說,不用拿抽煙的事擠兌我。
劉曉芒被他一嗆,更不知怎樣將話題落在戒指和錢上。
劉曉芒干笑了兩聲,你知道我沒有擠兌你的意思。
曉菖說,你明明就是這意思。
倆人圍繞著抽煙所衍生的“擠兌”糾纏了好一陣,看到曉菖打起了哈欠,劉曉芒急中生智,拿一個正在蹲監獄的同學舉了例子。那個同學本來挺聰明,可沒把聰明用對地方,從小手腳不干凈,先是偷同學的文具盒,后來偷同學的自行車,再后來偷父母的摩托車,甚至還帶著一伙人去他舅舅的廠子里去偷。偷盜是一條不歸路,只有手銬才能讓他停下來。劉曉芒說話時,曉菖的眼睛緊盯著他的臉,認真的樣子就像幼兒園的孩子望著老師,手里的香煙燃盡了都不知道。他以為劉曉芒會重點講述那個同學做下的大案以及在監獄里的生活,劉曉芒卻停住了。曉菖有點失落。
劉曉芒感慨道,小時候偷針,長大就會偷金。
曉菖愣了一下,忽然回過神來,像是被開水燙著似的跳起身,將煙頭狠狠地猛摔在地上,嚷道,你懷疑我偷了你家的東西?
劉曉芒一時很尷尬,急忙說,沒有。
曉菖臉上涌上一副蒙冤受辱的表情,口氣卻愈發粗壯,就像嚴厲的父親訓斥兒子。
曉菖說,你也不想一想,如果真偷了你家東西,我還會坐在這里聽你說話?你要攆我走,犯不著用這種夾槍帶棒的下三爛招數。
曉菖氣哼哼回了臥室,重重地摔上了房門。
劉曉芒有點蒙,弟弟如此理直氣壯,他忽然懷疑自己可能把錢夾里的錢數錯了,蘇楠的戒指也許丟在了娘家。
劉曉芒下高速時看到路口設了疫情檢查站,路旁鐵欄桿上懸掛的橫幅在銀色燈光里顯得愈發醒目。橫幅在寒風中撲簌簌抖動,白色字跡像是振翅欲飛的蝴蝶。劉曉芒停了車,搖下車窗,一個穿防護服的人站在車邊,拿著紅外線體溫計探到他的額頭上。那人問,這么晚才回來?劉曉芒聽著他的聲音有點耳熟,由于他的頭部被防護帽包裹住,一時認不出是誰。劉曉芒笑著說,有事,耽誤了。那人又說,請替我向二老拜年吧。劉曉芒本來也想回敬兩句拜年的話,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不知道人家是誰,更不知道人家的父母是否健全,說了還不如不說。劉曉芒略顯尷尬地說,謝謝。
劉曉芒重新上路時還在努力想著那人的名字,離開檢查站不到一百米,他的腦子又被曉菖的身影占滿了。自從上次不歡而散,劉曉芒沒再見過他。他說要去深圳做生意,也不知是否真的在深圳。劉曉芒打過幾次電話,曉菖沒接。劉曉芒心里忽然涌滿了自責,那次跟曉菖談話的態度太軟弱,應該拿出大哥的威嚴,強硬地把曉菖留在身邊。如果那樣,母親會少了許多擔心,也不會有今天的麻煩。劉曉芒想著,又有點納悶,曉菖從外地回到家已經半個月,明明是回來過年,怎么偏偏在大年三十又失蹤?
劉曉芒的家在城南二十里的劉家莊。他開著車從縣城穿過時,又接受了一次體溫檢測。這次檢測的人提醒他戴好口罩。他戴上口罩之后感到有點憋悶,急忙把車里的暖風關了。從105國道拐下來,劉曉芒遠遠看到了自己的村莊,往年的此刻,村莊上空彌漫著五彩斑瀾的煙火,震耳欲聾的鞭炮聲此起彼伏。村里那些在外闖蕩的人,都喜歡用燃放煙花的數量來證明自己這一年的成績。今年的春節異常寂靜,疫情使所有人都不約而同地陷入了傷感和沉默。劉曉芒猛然想到蘇楠,她三天前隨著援鄂醫療隊去了武漢。自從她走后,劉曉芒極力克制著不去想她。不光因為她向醫院遞交請愿書時沒跟他商量,更因為她臨走的前一天晚上說的那些話。當時蘇楠流著眼淚,淚水卻是為另一個男人而流。劉曉芒像當頭挨了悶棍,愣愣地看著她,突然發現自己對這個同床共枕的女人并不了解,繼而又覺得他們的婚姻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劉曉芒不敢再想下去,抬手在額頭上猛拍了一掌,惡狠狠地摁了一下車喇叭,笛聲在遼闊的夜空里顯得特別凄厲,驚得路邊樹枝上棲息的麻雀到處亂飛。
在車燈的照耀下,劉曉芒看到村口橫著一條繩子,掛在繩子上的紅色標語被風卷成一團,繩子變成一根粗壯的棍子。隨著轎車駛近,劉曉芒看到有四個戴口罩的男人站在路中間沖他打手勢,讓他停下來。劉曉芒知道老家已經封了村,原以為散漫的村人不會把所謂的“封村”當回事,沒想到大年三十的夜晚依然這么嚴。他停車后搖下車窗,看到是劉剛、二征、三悶,還有一個戴眼鏡的瘦子。二征手里的紅外線體溫計就像一把手槍。劉曉芒的車剛停穩,體溫計便沖著他的腦門上戳了過來,就在“槍口”即將戳到額頭的剎那間,二征又將手縮了回去,興奮地嚷道,芒哥,是你呀。二征去年曾經帶著母親到省城讓劉曉芒領著去找蘇楠看病。二征扭頭對那個戴眼鏡的瘦子說,馬主任,芒哥是我們村的,不用測,反正他這一路已被測了好幾回。馬主任沒言語。劉曉芒急忙從車上下來,笑著說,你為什么不給我測?測過之后,二征大聲說,三十六度七,我說不用測吧。三悶笑著解開了攔路的繩子。二征又朝車里看了一眼,問,嫂子怎么沒回來?劉曉芒剛要說話,劉剛將劉曉芒朝旁邊輕輕一拉,壓低著聲音問,你為曉菖的事回來的吧?
劉曉芒跟劉剛有一種特殊的親近感。劉曉芒的母親和劉剛的母親是同一天嫁到劉家莊的,倆人關系挺好。劉曉芒和劉剛出生之后,分別認了對方的母親當干娘。劉剛小時候念書挺笨,讀了一年初中便跟著表哥去北京學習修電機。在北京混了十來年,去年回村競選上了村主任。
劉剛說,有了他的消息你及時告訴我,我找他多半天了。
劉曉芒撓了撓頭,像是問劉剛,又像自言自語,這小子能去哪兒呢?
劉曉芒的父母住在村東頭第二個胡同里,去年新蓋的五間大瓦房。劉曉芒將車停在胡同口,下車時看到東村口也攔著一條粗壯的繩子,兩個穿軍大衣的男人正戴口罩守在繩子旁邊。劉曉芒進了胡同,各家的墻外都堆著剩余的建筑材料,把本來挺空闊的胡同擠得特別窄。新房子是劉曉芒出錢蓋的,蓋好之后他總共回來過四次,每次回來都像是誤入了別人的村莊。他在村中央的老宅子里長大,記憶中的老家就是那三間殘破的土坯房,在夢中經常睡在老宅的窄床上。劉曉芒進大門時被一根棍子絆了一下。他彎腰想把棍子撿起來立在墻上,手剛摸到棍子,又停住了。每到春節,家家戶戶都會把祖先的靈魂請回家過年,門口橫上一根木棍,為的是讓祖先的靈魂安靜地待在家里,避免到處亂串。院子里燈火通明,劉曉芒看到正屋的門東邊放了張方桌,桌上擺著一個碩大的白色豬頭。母親每年春節都要給老天爺上大供,擺好豬頭之后還要雙手合十念誦一番。劉曉芒小時候對母親念誦的內容特別好奇,總是站在她身后偷聽。他聽到母親是在讓老天保佑他將來考上大學。等到有了弟弟,母親念誦的內容改成了保佑曉菖的身體強壯起來。院子里的寂靜讓劉曉芒有點不安。他急步走進屋里,看到母親正蓋著被子躺在床上。他以為母親病了。母親是個敏感而要強的人,三歲時失去了父母,隨著姨媽長大。她原來盼著劉曉芒能回到縣里或鄉里當干部,只有給家族帶來看得見的榮耀,大學才算沒白念。劉曉芒留在了省城,母親覺得他像一粒砂子掉進了海里。
母親一聽有人進門,麻利地從床上坐了起來,懵懂地問,是曉菖回來了嗎?劉曉芒發現母親的頭發變得烏黑,穿著鮮艷的紅色毛衣,顯得年輕了許多。她只在劉曉芒跟蘇楠結婚的那一年染過一回頭發。染了頭之后怕村里人笑話她裝模作樣,跟人說再也不染了,如果再染,只能是在曉菖結婚的時候。她看清進門的人是劉曉芒,哭了,用手指著門,匆忙下達著命令,曉芒,快去把你兄弟找回來呀。劉曉芒心里一酸,母親這輩子為曉菖流的眼淚太多了。看著她不停地流淚,劉曉芒默默坐在床邊的沙發上。他知道母親的眼淚是勸不住的,只有等她哭完,情緒才會稍微穩定一些。母親拿著手絹輕輕擦眼睛,話頭落在曉菖身上。昨天上午,曉菖非要讓母親穿上他給她買的新毛衣,隨后又催著她染頭。母親不想染,曉菖將染發劑和梳子摔在地上。曉菖一著急,母親反倒笑了。她說,我原打算等你娶媳婦時再染。曉菖說,你就當我明天娶媳婦吧。曉菖幫母親染頭時,那雙粗笨的大手小心翼翼,像女孩兒的手一樣溫柔。
母親對劉曉芒說,當時我心里七上八下,有點慌。
果然,曉菖下午出了家門就沒再回來。昨天晚上吃飯時,父親給曉菖打電話,曉菖說晚點回家。父親以為他跟著李齊去打牌了。今天早晨父親想叫著曉菖去祖墳上請祖先,發現他一夜沒回,再打他的電話,關機了。
母親絮絮叨叨,聯想著曉菖可能遭遇的種種不測,又哭起來。劉曉芒覺得屋子里和院子里一樣冷,有一股寒風順著門縫不停地往屋里鉆。他起身將門關得更嚴一些,看了看屋角的煤爐,快滅了。劉曉芒添了幾塊煤,拿起鐵條捅了捅,幾縷淡藍色的火苗從爐口緩緩冒了上來。他給母親倒了杯熱水,端起來遞給她。
劉曉芒說,您不要亂想,曉菖肯定不會有事,我先去找李齊問一下。
他剛拉開房門,母親問,蘇楠沒跟你一塊回來?
劉曉芒不愿把蘇楠去武漢的事告訴她,囁嚅了一下,說,她今天值班。
母親說,當個大夫真不容易,大年三十還要給人看病。
劉曉芒出大門時聽到手機來了條短信。是蘇楠發來的:聽爸爸說你回老家了,有急事?劉曉芒拿著手機愣了一下,回道:沒事。回完之后,劉曉芒覺得自己的口氣有點生硬,正想再說點什么,蘇楠的短信又來了:那就好,你代我向爸媽拜年吧。劉曉芒想問一下她在武漢的醫院里過得怎么樣,提醒她注意安全。他不止一次從手機推送的信息上看到有醫務人員被感染了。他發現蘇楠的信息也像是在應付,又感到沒什么可說的了。他將手機揣進兜里,心里突然一空。自從見過蘇楠為另一個男人流下的眼淚,劉曉芒覺得倆人之間出現了一道鴻溝。
當時劉曉芒正盤算著要給岳父送的禮物,蘇楠說要跟他談一談。她的表情過于嚴肅,劉曉芒有點蒙。
他問,談什么?
蘇楠說,我明天要隨著醫療隊去武漢了。
劉曉芒感到胸口一悶,像是被人猛搗了一拳。
他問,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說?
蘇楠沒有看他,目光投在窗戶上。窗外的夜色像是給窗玻璃刷了一層濃重的黑漆,映出她蒼白的臉。
她自言自語般地說,我寫了三次請愿書才被批準。
劉曉芒問,你以為提前說了我不讓你去?
蘇楠沒有回答,牙齒緊咬著嘴唇,像是極力控制著嘴里的話冒出來。她的臉在漸漸扭曲,肩頭不停地聳動,雙手突然捂在了臉上。
她哽咽著說,我又夢見他了。
蘇楠夢到的那個人叫陳布朗,比她大一歲。蘇楠的父親調到省城之前在魯南一個縣城工作,蘇楠家跟陳布朗家住鄰居。蘇楠小時候是陳布朗的跟屁蟲。學校在馬路對面,每天上學放學陳布朗都會牽著她的手。他們住的家屬院有些低洼,下大雨時院門口會積下一片水,蘇楠雖然也穿著雨靴,陳布朗每次都會把她背過去。同學們以為她是陳布朗的妹妹。陳布朗喜歡吹笛子,經常吹《揚鞭催馬運糧忙》和《小放牛》。每當笛聲在隔壁院里響起,蘇楠便站在凳子上俯著墻頭看他。兩家葡萄樹的枝葉在墻頭上纏在一起,陳布朗看到她時,笛聲一停,招手叫她去他家院子坐到他對面的馬扎上。蘇楠不去,她覺得趴在墻頭上笛子更好聽。陳布朗上了初中之后就不在院里吹笛子了,蘇楠心里空落落的。她依稀感覺陳布朗在疏遠她。她有點生氣,想當面問一問。雖然是鄰居,當一個人刻意躲避時竟然也很難見到。蘇楠堵了他好幾回才把他堵住。他騎在自行車的大梁上,單腳撐地,像被逮住的小偷似的神情有些慌亂。
蘇楠問,你還吹笛子嗎?
陳布朗臉有點紅,吹。
蘇楠納悶,我怎么聽不到了?
陳布朗說他現在去護城河邊的柳林里吹。
蘇楠問,你怎么不帶著我?
陳布朗說,下次帶你去。
說完,像逃跑一樣騎著自行車走遠了。
他一直沒有叫她去柳林。蘇楠上了初中之后才切身感受到男女同學之間那種莫名其妙的隔閡,互相之間都不說話。蘇楠在學校里偶爾看到陳布朗,主動叫住了他。陳布朗面對她時就像做了虧心事,眼睛只看著自己的腳尖,要么就彎腰系鞋帶。蘇楠心里偷偷地笑,臉上卻是一副興師問罪的表情。
她問,你怎么不守信用?
陳布朗說,下次吧,一定帶你去。
他最終也沒帶她去柳林聽笛子。那是2003年夏天,他染上了“非典”。
劉曉芒聽著蘇楠的講述,仿佛看到十四歲的蘇楠穿著白色連衣裙正站在醫院大門外,手里拿著準備送給陳布朗的新笛子。隔離區守衛森嚴,蘇楠只能仰臉望著那幢被封閉的住院樓。夏日的夕陽依然熾熱,密集的窗戶在夕陽映照下像一面面耀眼的鏡子。蘇楠不知道陳布朗住在哪間病房里。她看著一個又一個緊閉的窗口,眼睛都酸了,也沒看到他的身影。她舉起手中的笛子,沖著住院樓的窗戶晃了又晃,希望他能看到她。
蘇楠是從陳布朗母親口中得知了他去世的消息,陳布朗的母親交給她一封信。信封得很牢,顯然沒被打開過。蘇楠拿著信躲在臥室里遲遲不敢把信打開,他的去世對她猶如晴天霹靂,她在極度震驚中連眼淚都忘了流。她將信放在書桌上,緊挨著那根沒有送出去的笛子。當天夜里,她被笛聲驚醒。剛開始以為是做夢,隨即感覺笛聲離她這么近。她沒有害怕,以為是陳布朗又在院里吹笛子了。她循著笛聲找去,恍惚中覺得他的死亡才是一個夢。月光如水,她站在院子里,看到墻根放著她原來站過的那個凳子,凳子上蹲著一盆花。她重新回到屋里時,看到那支新笛子正壓在信封上,原來粘貼很牢的封口敞開了。
陳布朗的信寫了滿滿兩頁稿紙。前半部分顯得挺啰嗦,他一再解釋為什么遲遲沒帶她去柳林聽笛子,他的理由在蘇楠覺來不能算真正的理由,她只看到了一個少年內心深處那份難以抑制的羞澀。信的最后寫道,那天傍晚我看見你了,你搖晃著的笛子,我站在病房的窗口不停地沖你招手,你沒有看見。我病好之后要去省藝術學院讀附中了,媽媽說已經幫我聯系好轉學的事,將來我要考中央音樂學院。我這次出了院,第一件事便是帶你去柳林,把你介紹給我那些愛音樂的朋友們。
蘇楠說到這里時已經泣不成聲,頭俯在沙發扶手上,身子不停地聳動著。劉曉芒傻愣著坐在旁邊,一時不知是否應該安慰她。他心里的某個角落忽然一動,終于明白她為什么遲遲不肯要孩子。他催過幾次,蘇楠總是說她的心里還沒準備好。他有點莫名其妙,曾專門找人咨詢,心理醫生說,不想生孩子的女人一般是因為少年時期心理上留下了某種陰影,也就是俗話說的有道坎。他建議劉曉芒帶著妻子去當面咨詢,心理醫生會幫著蘇楠跨過心里那道坎。劉曉芒沒把咨詢的事跟蘇楠說。他覺得自己總比心理醫生更了解她。如今才知道,自己對她并不了解,她心里竟然還裝著另一個男人。
蘇楠的淚水止住時,臉上帶著一絲陌生的凜然。
她說,正因為他,我后來才學了醫。
劉曉芒緊咬著嘴唇,沒有說話。他很清楚對一個已經去世的十五歲少年不該吃醋。蘇楠的眼淚卻讓他心里有種說不出的別扭。他覺得蘇楠是在故意將他推離她的生活,或者,他從來就沒真正走進她心里。劉曉芒手中正握著一只不銹鋼杯子。他沖動地想將它砸向某個地方。他的手愈握愈緊,幾乎聽到了杯子變形的聲音。
劉曉芒去找李齊時走得很急,脊背上的汗水浸濕了襯衣。街道非常寂靜,昏黃的路燈將他的身影不時地縮短了又拉長。劉曉芒不希望曉菖跟李齊混在一起。李齊比曉菖小一歲,竟然讓一個女孩子懷了孕。今年五月份的一天中午,李齊帶著那個瘦弱的女孩找到劉曉芒,想讓他領著去找蘇楠給女孩做流產。劉曉芒苦笑,蘇楠是呼吸科的大夫,要流產應該找婦科,再說,流產在哪兒都能做,沒必要專門跑到省城來。李齊悄聲對劉曉芒說,之所以來省城,一是為了保險,更重要的是讓那女孩知道他在省里有熟人。劉曉芒本來不愿管這事,后來又覺得李齊在省城無依無靠,還是給蘇楠打了電話。
李齊沒在家。劉曉芒從他家出來之后,站在街上左顧右看,不知再去哪兒找他。這時,他看到劉剛騎著電瓶車走了過來。劉剛剎住車,納悶地問,我正要去找你,怎么在這兒?他的話音未落,村莊的大喇叭里響起了他提醒村民不要聚會的聲音。喇叭里劉剛口氣異常嚴厲,跟眼前的劉剛簡直是兩個人。劉曉芒感到一絲詭異。
劉剛一笑,喇叭里放的是錄音,每個小時放一次。他用手順著鼻梁往上推了一下口罩,問,見到曉菖了嗎?
劉曉芒說,聽說曉菖失蹤前跟李齊在一起。
劉剛一聽,聲音突然激動起來,他娘的,這個李齊,我也正要找他。
劉剛用電瓶車帶著劉曉芒順著大街朝西走了半里路,在一家小超市門前停了下來。超市關著門,門口卻亮著燈。劉剛用力拍門,好一會兒,一個俏麗的小媳婦開了門,她身上散發著淡淡的煙草味。她一見劉剛,驚得張大了嘴巴,像是要大喊,嘴巴卻遲遲難以合上。劉剛沒理她,氣呼呼地徑直穿過超市朝后院走去。劉曉芒聽到北屋里傳來桌子被掀翻的聲音,隨即是劉剛的罵聲。劉曉芒進了屋,看到有三個男人正瑟縮著身子垂首站在墻根,眼睛盯著散落在地的麻將。劉剛指著鼻子訓斥他們的聚會,我喊了一遍又一遍,你們不想活了?劉曉芒站在門口有些尷尬,本想跟著劉剛來找李齊,無意中卻成了隨著他抓賭。劉曉芒沒看到李齊,不愿摻和進老家人的是非里,想退出去。這時,劉剛走到大衣柜前,拉開柜門,伸手將李齊一把揪了出來。李齊比劉剛矮一輩,嬉皮笑臉叫了一聲叔,劉剛抬腿踢了他一腳。李齊像只靈巧的猴子似的一蹦,想奪門而出,卻撞在劉曉芒的懷里。
李齊笑了,曉芒叔,你啥時候回來的?
劉曉芒把李齊叫到院子里一棵石榴樹旁,李齊很高興被及時救出來,跟劉曉芒說著話,眼睛卻不時朝屋門溜一眼,生怕劉剛再來踢他。
劉曉芒問,曉菖失蹤前跟你說了什么?
李齊有點蒙,失蹤?他怎么會失蹤?
劉曉芒心中一闊,以為他知道曉菖的去向。
李齊說,昨天下午我想帶他來打牌,他非要回家幫你媽染頭發。
劉曉芒心里一緊,原來曉菖的失蹤是有預謀的,他幫母親染頭發是在上午。
劉曉芒說,你再想想,他可能去哪里?自從昨天下午一直沒回來。
李齊很認真地想了想,眼睛一亮,他別再是回武漢了吧?
劉曉芒心里一揪,他去武漢干什么?
李齊有點納悶,你不知道?他前些日子一直在武漢,還在那兒交了個女朋友。
劉曉芒腦子里立時亂成了一鍋漿糊。
這時,劉剛從屋里走了出來,劉曉芒夢囈般地對他說,曉菖去了武漢。
劉剛嚇一跳,隨即又笑了,開什么玩笑?武漢已經封了城,他怎么去?連車票都買不到。
李齊說,買不到票就去不了?曉菖的辦法多著呢。
劉剛抬腿踢到李齊的屁股上,快滾,回頭再收拾你。
劉曉芒看著李齊又蹦又跳地跑出了院子,忽然感到一陣天旋地轉,急忙伸手扶在石榴樹上。
他失神地看著劉剛,曉菖不會真的去武漢吧?
劉剛緊摟了一下他的肩頭,說,別亂想,曉菖又不傻,那兒疫情最嚴重,他怎么會往那里跑。
劉曉芒一聽心里反而更加緊張。曉菖的性子太野,逆反心理特強,愈是不希望他去的地方,他偏偏要嘗試一下危險的樂趣。
劉剛抬腕看了看手表,說,咱們回家看看吧,沒準他已經回來了。
劉剛推著電瓶車和劉曉芒并肩朝家走。
劉剛說,鎮派出所要給所有從武漢回來的人備案,我已經匯報過了,曉菖回來已經超過十四天,沒什么癥狀,不過,我還是要盡早帶他去一趟派出所。
劉曉芒沒聽清劉剛說了什么。他的腦子里像風扇一樣呼呼轉,又像跑了針的破唱片,腦海中只有一句話在不停地盤旋:他不是在深圳?怎么又去了武漢?
劉曉芒家的老宅在村中央一條又窄又深的胡同里。劉曉芒記得小時候最怕夜晚在胡同里走,因為總聽到身后尾隨著輕輕的腳步聲。母親對他說,晚上害怕時可以大聲唱歌。劉曉芒試了幾次,反而更加害怕。胡同兩側的墻太高,唱歌時會有淡淡的回聲,就好像有幾個看不見的人正隨著他一塊唱。最終是父親徹底打消了他面對漆黑夜色時的恐懼。父親說,害怕時可以在心中默默地喊爸爸。打那之后,劉曉芒再也不懼怕黑暗了。他心里只要叫一聲爸爸,便仿佛聞到父親身上的煙草味,又感覺像是正被父親那雙長滿繭的雙手舉起來。那時的父親在劉曉芒眼中非常強壯。如今父親的腰佝僂著,全身的所有器官好像都陷入了未老先衰的狀態。走起路來身子朝前一探一探,像是在水中奮力地往前游。劉曉芒隨著父親走進通往老宅的胡同,看著他的背影,眼睛忽然有點發澀。
劉曉芒是在家門口時與父親相遇的。當時劉曉芒正在跟劉剛商量著怎樣找曉菖。他們怕當著母親的面說起曉菖再勾出她的眼淚,倆人只好站在大門外。劉曉芒說曉菖出走是有預謀的。劉剛有點不解,如果他昨天下午準備出走,昨天晚上為什么還會接父親的電話?劉曉芒覺得曉菖是在延緩時間。劉剛笑道,他還是個孩子,又不是特工,肚子里哪有這么多彎彎繞,再說,有什么事情會促使他年根底下出走?劉曉芒想到曉菖在他家偷了錢和戒指之后依然義正詞嚴的樣子,心里一哆嗦。劉剛掏出手機看了看,說,曉芒,咱們報案吧。劉曉芒不愿報案,他覺得曉菖失蹤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這時,父親匆匆走了過來。他一見劉曉芒和劉剛,激動地猛拍了一下大腿,說,找到曉菖了。
曉菖一個人正待在老宅的三間土坯房里。父親這一天到處找他,終于找到了,他卻不肯出來。曉菖從屋里閂緊了房門。父親生氣地拿起鐵锨想把門砸開,曉菖卻拿起一把生銹的瓦刀。曉菖說如果有人進門,他就把自己劈死。
父親對劉曉芒說,我回來叫你媽,讓她去把曉菖叫出來。
老宅的三間土坯房還是父母結婚時蓋的。如今外墻上的白灰大都脫落,裸露出土坯間寬大的縫隙。沒有人住的院落破敗得非常快,大門雖然上著鎖,大門旁邊的土墻卻被夏季的暴雨沖開一道豁口。劉曉芒看到父親從豁口跳了進去。父親走路時氣喘吁吁,跳墻時身手竟然如此敏捷。劉曉芒沒有讓父親叫母親來,母親來了只能哭得人心煩意亂。劉剛本想跟著一塊來,走到半路被支部書記打電話叫走了,說是又發現有人聚會。劉曉芒緊隨著父親跨過那道豁口時突然有點擔心,深怕曉菖轉移了地方。幸好,一進院子便透過窗玻璃看到了曉菖的身影。
曉菖穿著單薄的皮衣,正瑟縮著身子烤火。火堆不大,可能是怕火太大引燃了房子。他蹲在火堆前,雙手湊近了火苗反復揉搓著,頭發又長又亂,看上去就像個正在烤獵物的原始人。他被煙嗆了一下,捂著嘴不停地咳嗽起來。父親走上前敲了敲門,曉菖一驚,眼睛望著窗外的夜色,右手麻利地抄起放在身邊的瓦刀。
父親說,曉菖,你哥回來了。
曉菖手里的瓦刀垂下了,站起身走到門前,用手抹了兩下玻璃,往外看了看,忽然將頭抵在玻璃上,哭了。
曉菖說,哥,以后咱爸媽就靠你了,我是完了。
劉曉芒一驚,你怎么就完了?
曉菖說,我感染了新冠病毒。
后來,劉曉芒每當想起與曉菖的隔門對話,心里都會涌過一絲強烈的震撼。劉曉芒沒有想到,這個自幼嬌生慣養、讓他恨鐵不成鋼的弟弟,這個整天東游西逛、極有可能變成盜竊犯的弟弟,在面對生死時,突然變成了有擔當的男人。
曉菖是怕傳染別人才將自己封閉在老宅里。
老宅的四周沒有鄰居。近些年村里人都在村頭買新的宅基地,一座座老宅閑置在村中央。劉曉芒站在門前,聽著寒風在干枯的棗樹枝間穿過的聲音,感覺像是站在一個被人遺棄的村落里。劉曉芒已經讓父親回家了。他隔著門玻璃看著弟弟又去給火堆添了幾塊木柴。火堆的光弱了一下,不一會兒又亮了起來,映得屋子里像一間冷清的山洞。火苗的晃動使曉菖的身影也在墻壁上不停地搖晃,看上去像形狀怪異的皮影。
劉曉芒問,你怎么確定被感染了?
曉菖說,小玲感染了,昨天下午給我打電話說住進了醫院,她聽到我在咳嗽,讓我小心點,昨天晚上她的電話就打不通了。
劉曉芒知道那個小玲是曉菖在武漢的女朋友。
劉曉芒哽咽了一下,盡量平靜地說,你如果真被感染,更該跟我去醫院,小玲不是入院了?
曉菖說,哥,不要逼我。我在手機上查過了,這病無藥可救,去醫院也沒用,我出去只會傳染其他人。
倆人一時陷入沉默。劉曉芒聽到大喇叭里又響起了劉剛的聲音。
曉菖問,哥,這病毒到底怎么回事?我離開武漢時那兒還車水馬龍,眨眼間就有這么多人病倒了。
劉曉芒一時不知怎么接茬。曉菖的問題也正是他想問的。他將身上的羽絨服裹緊,倚著門框,看到干枯彎曲的棗樹枝映在暗藍色天幕上,像一幅工筆畫。
劉曉芒說,蘇楠去武漢了。
他說完之后把自己嚇一跳,不知道這話怎么會莫名其妙冒了出來。
曉菖沉吟了一下,說,嫂子是個了不起的人。
劉曉芒對他的說法有點意外,隔著玻璃往屋里看了一眼,曉菖正弓腰將嘴里的香煙湊到火堆上點燃。劉曉芒忽然覺得曉菖成了一個值得交心的朋友,有了種講述陳布朗的沖動。那個去世的男孩梗在劉曉芒心里,實在不知怎樣才能將他趕出去。當曉菖叼著香煙重新站在門邊時,劉曉芒說起了蘇楠的眼淚。曉菖聽完好久沒說話,直到把嘴里的香煙抽完,才敲了敲玻璃,讓劉曉芒看著他。
曉菖說,那些話,嫂子肯定沒對任何人說過,臨去武漢前對你說,說明她做了赴死的準備。
劉曉芒感到一陣窒息,心像是被繩子緊緊勒住了。
曉菖說,你不該怪她,你想一想,她那些話不對你說,又去對誰說呢?
劉曉芒心里涌上一陣感動,眼睛里泛著淚光。不知是因為蘇楠,還是因為曉菖的話。
曉菖說,哥,我對不起你,上次的錢和戒指,是我拿的。
劉曉芒努力笑了一下,我知道是你拿的,你能承認,倒讓我有點吃驚。
曉菖苦笑道,我長這么大,讓咱爸媽操碎了心,我死了,對他們是一種解脫。
劉曉芒氣道,你死了是你自己解脫,爸媽只會陷入更深的痛苦。
兄弟倆分別靠在門上,腦袋隔著玻璃抵在一起,看上去像是分不開的連體人。
曉菖敲了一下玻璃,哥,外邊太冷了,你回家陪爸媽過年吧。
劉曉芒說,你不出來,我就不走。
曉菖沒有說話。
劉曉芒說,并不是每個從武漢回來的人都會感染。
曉菖依然不說話。
劉曉芒的心中忽然涌上一股悲壯,嗓子哽住了,有句話像魚刺一樣卡在喉嚨里。
他想說,即使你真的病了,仍然是我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