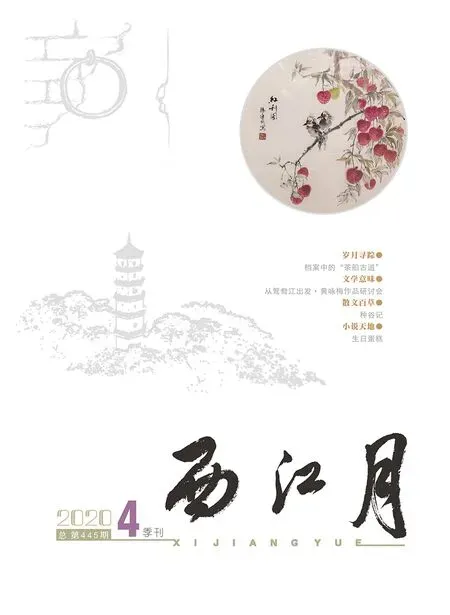父親的扁擔
黃盛后
一天,牙牙學(xué)語的女兒在雜物間拖出一根扁擔,搖搖晃晃撥弄桌子下的玩具,甚是可愛。看到這根老竹制成的扁擔,中間稍寬兩頭小,通身上下呈扁圓形,微黃的顏色,光滑而堅硬,父親平時“趕鬧子”(趕圩)常用這根扁擔挑東西,我才想起這是父親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來看我時留下的。二十年過去了,其間搬過一次家,我依然沒有丟掉這根扁擔。觸摸這根刻滿歲月痕跡的扁擔,我內(nèi)心思緒潮涌,仿佛觸到了父親的深情,觸到了過往歲月的艱辛。
在我參加工作的第三年的一天下午,我突然接到電話:“你爸來藤縣找你,已經(jīng)到藤縣中學(xué)門口了。”我激動不已,單位離中學(xué)門口約百來米,我立即沖下樓去。當我見到父親的時候,父親蒼老疲憊的臉上滿是自豪,他挑了一擔家鄉(xiāng)特產(chǎn),半麻袋的花生,另半袋裝著黑豆、綠豆、長棗等。看到這些,熱淚在我眼眶里打轉(zhuǎn)。我接過擔子,足有四五十斤重。父子倆一路聊著往家里走去。他不停地介紹家里、村中的變化,還問我工作有多忙,辛不辛苦。父親已經(jīng)六十多歲了,一直是體弱多病。從老家到藤縣約有三百多公里,中途要轉(zhuǎn)好幾趟車,且山路彎彎。父親不識字,也從來沒有到過藤縣,我只告訴過他,梧州繼續(xù)往西去就是藤縣。從家里到鎮(zhèn)上、到縣城,轉(zhuǎn)車到賀州,再往梧州,然后再轉(zhuǎn)車到藤縣,一路奔波,父親是如何做到的?
直到兩天后,父親見我工作太忙不辭而別,留下一根扁擔和一張字條,我才知道原來父親當過村干部,能認識幾個字,還會寫自己的名字。
父親是家中的老大,爺爺死得早,奶奶后來又改嫁。那時,父親還不滿十八歲,家里有四個弟弟和一個妹妹,生活的重擔落在了父親的肩膀上。
長兄為父。父親說,那年頭生活就靠肩膀擔,他肩上的擔子特別沉重。他曾經(jīng)進過深山老林砍柴擔柴,深入過西嶺山背過杉木扛過木材。父親做過很多苦活累活,吃過很多苦頭,饑寒交迫之下,他帶著弟弟妹妹們持碗沿村去要飯。后來,在湖南桃川,三個弟弟當了人家的干兒子,妹妹也當了人家的童養(yǎng)媳,暫時解決了吃飯問題。之后八弟、妹妹相繼因病過世,只有最小的九弟因腿有殘疾回到家鄉(xiāng),最后追隨改嫁的奶奶。父親暫時卸下重擔,又因為年輕,能挑擔子,能干重活,鄰村的外婆家里就只有母親一個女兒,缺少勞動力耕種,父親主動上門幫忙。于是父親和母親就湊合成了一個家。之后,就有了我們兄弟姐妹,一家十口住在一間半的兩層瓦房里。要養(yǎng)活一家十口人,壓在父親肩上的擔子是越來越沉重了。
可每當負重前行的時候,父親總是樂觀地說“輕擔擔倒山,重擔壓死人”的道理。父親講挑擔子的故事,必定會提起他去八步(賀州)挑化肥的往事。當年村里一群年輕人里,就數(shù)父親最能挑重擔,日常挑水擔柴百來斤,步伐從容,扁擔悠悠,據(jù)說父親挑兩百斤都健步如飛。
熱血青年總是免不了沖動逞能。有一年,生產(chǎn)隊里有一批化肥要從八步(賀州)運回村里,當時沒有車拉,只能用人工挑回來,大隊要按所挑重量計工分。父親與同村一群年輕人結(jié)伴同行,朝發(fā)夕至,走到天黑才到達八步(賀州),小住一晚。第二天一早就挑著化肥往家鄉(xiāng)趕。那次父親想多掙點工分,逞英雄挑了重擔。由于路程實在是太遠,所帶的水和干糧不足,饑餓與勞累相繼襲來,沉重的擔子終于還是把父親壓垮了,從那時起父親就落下了腸胃病等病根。父親常常告誡我們要量力而行,輕擔才能走得遠。
也許是再也不能挑重擔了,父親慢慢留心學(xué)起了其他手藝,選擇需要耐心和技術(shù)的活兒干。父親說,這是挑輕擔呢!
在村里,父親成了一個多才多藝的農(nóng)民。
父親是村里戲班子、醒獅隊的鼓師。很小的時候,我就喜歡跟著父親去“唱戲”,父親也樂意帶上我,隨村里戲班子到周圍十里八鄉(xiāng)唱戲“賀新歲”“鬧元宵”。跟著父親好處很多,人家知道我是鼓師的兒子,大過年的,免不了會給紅包,還有吃的,一趟下來往往收獲滿滿,兄弟姐妹們都很羨慕我。耳濡目染之下,我對擊鼓有了一定的了解,戲里情節(jié)什么時候高潮要緊鑼密鼓,什么時候平靜要敲木魚,鼓聲點點是領(lǐng)導(dǎo),其他樂器應(yīng)聲附和,才能激蕩出一場好戲。也就是說,父親是戲班子里的領(lǐng)隊,整個戲班子能不能唱好一臺戲,全靠父親,父親還是重擔在肩。
父親說,村里戲班子最喜歡唱有乞討段子的戲。因為演員跪著唱,聲淚俱下,很多觀眾都被唱詞感動,情不自禁地施舍行善,往戲臺上扔錢扔物,戲班子成員多多少少都會分得一些。在春節(jié)期間,父親往往收獲頗豐,可以為家里改善一下生活,減輕負擔。
父親也是村里唯一的泥瓦匠。每一年村里都要燒制好幾窯的青瓦,然后按人頭分到各家各戶,留待蓋新房子時用。從趕群牛踏熟泥胎、堆泥墻、按瓦桶模具修制濕瓦,到晾干一桶桶泥瓦,收瓦裝窯,燒窯十五天,圍堰蓄水冷卻,再到泥瓦出窯,父親都是技術(shù)負責人。而當中的基礎(chǔ)工作制泥瓦桶,村里也只有父親能做,重任又落在父親的肩上。生產(chǎn)隊里一到秋冬季制泥瓦時節(jié),父親就成了最忙的人,往往中午飯都是在泥瓦茅草房里解決。燒泥瓦很關(guān)鍵的一個環(huán)節(jié),就是瓦窯燒紅時的火候把握和窯頂圍堰蓄水冷卻的過程,把握不精準,往往燒不出青瓦。最后這段關(guān)鍵時間節(jié)點,父親總是寢食不安,有時半夜會起來給窯頂堰池換水、煙囪排汽。而鄰村燒制泥瓦時碰到了技術(shù)問題,都會請父親去幫忙,父親會耐心講解并教會他們,明里暗里收徒,對方都會以留家吃一餐飯以示答謝,有時我也跟著蹭吃解饞。
此外,父親在村里還是一個德高望重的拳師,還會制作鐵犁、簸箕等。能者多勞,父親總是忙忙碌碌地挑擔子,在風霜雨雪里挑起春夏秋冬,挑走歲月的艱辛,挑來了幸福和夢想。
隨著兄弟姐妹一個個長大成家,父親肩上的擔子逐漸減輕了。后來四哥參軍入伍,父親覺得無上光榮。而更讓父親值得驕傲的是培養(yǎng)出了村里的第一個大學(xué)生,我啟程上大學(xué)的那天,家里請客放電影,著實又熱鬧了一回,還一路放鞭炮送我到鎮(zhèn)上。村民們羨慕的眼光和夸贊的語句,著實讓父親又風光了一把,父親終于可以釋放重負了。
大學(xué)畢業(yè)后,我有了工作,父親肩上再也沒有擔子了。一根扁擔挑點東西到鎮(zhèn)上“趕鬧子”成了父親人生的最大樂趣。
不幸的是,父親在來看望我后的第二年夏天,摔了一跤就再也沒有起來,沒有留下只言片語,只留給我一個“子欲養(yǎng)而親不待”的遺憾。
睹物思人,父親一定想不到,他無意間留下的這根扁擔竟成了我對他無限思念的寄托,就如壓在衣柜里最底層的那塊布,那是父親過世時所穿的衣服裁成的布,我們兄弟姐妹各分一塊,作為永遠的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