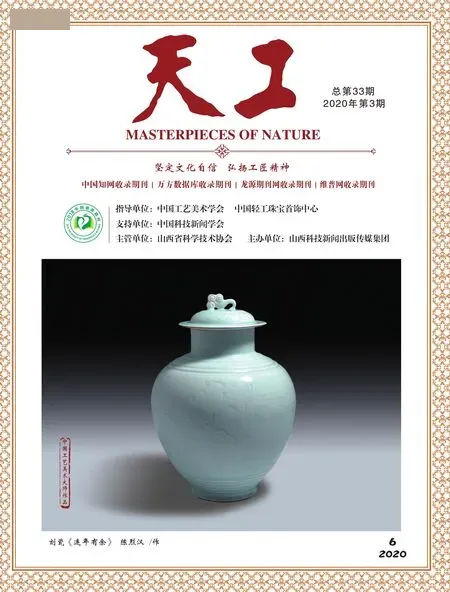寶雞地區民間壁畫的圖像題材探析
文 白雪紅
寶雞地區是周秦文明的發祥地,宗教歷史和文化積淀深厚,廣大百姓除了信仰佛、道的宗教諸神外,民間還出現大量供奉民間俗神的廟宇,這些鄉間小廟都有精彩的壁畫留存。寶雞地區保留下來的建筑壁畫年代在清末到民國之間, 壁畫所繪制的內容題材與寺廟供奉信仰有著緊密的聯系,壁畫的內容題材及表現都很豐富。對寶雞地區留存的壁畫,李強教授通過多年的考察做了詳細的調查并對壁畫進行了深入研究,但對于寶雞民間壁畫的研究依然有著很大的延伸空間。本文將把寶雞民間壁畫的圖像題材和建筑作為一個有機的內在空間,著重探討宗教建筑所營造的象征性環境。文章將探明裝飾題材之間的內在聯系,并深入思考圖像在建筑特定位置的原因。對建筑內圖像布局與設置的討論有助于理解主要裝飾題材在建筑空間的作用與內涵,以及寶雞地區區域性傳統與時代的特征。
一、寶雞民間壁畫圖像題材的布局與設置
壁畫在建筑中是完善建筑空間功能的必要藝術形式,也是提高建筑空間藝術層次的必要措施。寶雞現留存的宗教古建主要有木構殿堂式和窯洞殿堂式兩種。木構殿堂梁架上皆有彩繪,同時,廟墻各面都有彩繪,窯洞殿堂式雖空間逼仄但兩側壁面與拱頂也都有彩繪,這些元素強化了廟堂的宗教象征功能,也使廟堂充滿了宗教氣息,富有藝術審美和文化表征意義。
宗教建筑的功能決定了其建筑空間與內部裝飾的基本設置與特征。建筑彩繪將建筑空間分割為不同的層次,且不同的建筑形制、不同寺廟個體之間仍存在著一定的差異。但考察木構和窯洞兩種不同形制的寺廟,壁畫的繪制者對圖像題材有著較為相似的選擇和組合方式。寶雞地區宗教建筑現留存壁畫以其題材看主要有兩類,一類是佛寺,壁畫以經變故事為主。例如,壽峰寺其中殿現留存左側山墻的壁畫比較完整,是朝元式構圖的“二十四諸天禮佛圖”和獨立僧人像。另一類是民間信仰的村鎮小廟,村廟壁畫的內容比較繁雜,但如果我們仔細分析圖像題材在這些村廟中的分布情況,還是可以獲得關于寺廟內部壁畫裝飾題材的設置規律。通常“關帝廟壁畫表現三國故事、五圣宮壁畫表現東周列國故事、圣母殿壁畫表現封神故事和民間圣母傳說、菩薩殿壁畫表現《西游記》故事”。不同的廟宇雖然繪制的壁畫內容不同,但通常的格式卻是左右側壁對稱作兩大幅壁畫,在靠門(也有的是在供奉的神像兩邊)繪制武士或天王圖起保護和守衛的作用。例如,新民圣母殿在靠近正門的位置都布置了一個獨立的畫方,各繪制了兩位天將,衣帶飛舞,奪眶而出;而金龍山佛祖洞在靠近神像兩側的洞壁上,繪制了兩位1.3米高的天王像,在低矮的窯洞里顯得格外威武。
在寶雞寺廟壁畫中,往往尺幅較大的圣跡圖、故事圖占據了左右山墻的重要位置。例如,關帝廟,關帝即關羽是三國蜀漢的歷史人物,后世民間將其奉之為神,用來驅逐危險。在民間信仰中,關羽是忠義神勇的化身,因而在關帝廟中常繪制三國故事來宣傳關公是最為常見的圖像題材。又如,壽峰寺側殿伽藍殿(如圖1),該殿現存正壁神像兩側兩幅壁畫和右壁壁畫都很有特點,均為三國故事。其正壁三國故事表現手法為白描加水墨渲染又略施顏色。畫面正上方繪制一座宮殿,占去了整個上半部分的空間,其他情節都圍繞其展開,畫面中人物形象生動傳神,各情節之間以云氣自然隔開。右壁壁畫風格與正壁不同,采取通景式構圖,長坂坡、苦肉計、三顧茅廬等故事之間亦以樹石自然隔開,整體連貫統一,畫面采用工筆重彩畫法,設色鮮艷亮麗,人物形象和圖案紋飾的繪制也非常細膩,與此構圖相仿的還有天臺寺關圣殿,其左右山墻的三國故事壁畫保存較好,畫面色彩明麗。
對于寶雞寺廟大量通景式圣跡圖、故事畫通過圖像分析可以發現,壁畫所繪制的場景有較為固定的圖像元素,并且有著特定的組合方式和表現,且表現出模式化、標準化的趨勢,從整個構圖看,“寶雞民間寺廟構圖中會表現一座城樓,在對角的位置會繪制一座宮殿,這就是‘一城一殿(帳)’。這些大型的建筑表現占去比較大的空間,封住了邊角的位置,增加了畫面構圖的穩定感。”例如,陳倉區新民圣母殿兩側山墻的壁畫、壽峰寺伽藍殿正壁壁畫都是這種構圖形式,都是在正上方位置繪制了一座殿堂,占去了整個上半部分的空間,使畫面既有穩定感又有莊嚴感。當然,“一城一帳”的表現方式與畫面的組合關系也有著動態的變化,在不同寺廟的壁畫中所處位置存在一定的差異,有時在畫面左側,有時在畫面右側,處置非常靈活,這也是民間工匠在長期實踐中總結的規律。總之,寶雞地區寺廟的裝飾通常以寺廟供奉的神像為整個圖像系統的中心,壁面上的其他裝飾題材都圍繞其展開,不同寺廟以多種方式在建筑空間內強調這一場景的重要地位。
二、寶雞民間壁畫中的戲曲元素
考察西府地區民間壁畫的題材及其在寺廟里面的位置與布局后,我們發現在故事壁畫的表現上反映出具有地域性特點的圖式風格,即戲曲元素在壁畫中的廣泛運用。
植根于民間的村廟集中反映了當地的信仰,具有濃厚的民間色彩,其壁畫自然也就更加關注民間百姓的思想生活。寶雞地區民眾都酷愛戲曲,每逢節日廟會都會有戲班登臺表演,戲曲的發展與地區性的廟會存在著緊密的聯系。廟會是戲劇演出的主要場地,對秦腔、眉戶、道情等,本地人百聽不厭。官方廟會周公廟廟會邀請省內著名演員全天候演出,民間小型村落廟會也不例外,也會邀請一定級別的劇團做表演,這種習俗一直延續到今日,已經深入民心,成為當地民眾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隨著戲曲活動在民間的普及,戲曲元素的圖像在寺廟的壁畫中成為一項最為常見的內容,遍及各地的鄉間村廟。傳統壁畫與傳統戲曲雖屬不同的藝術門類,但二者之間卻有相通共融之處。三國故事、東周列國故事、封神故事等,由于故事情節迂回,驚險刺激,經典人物形象睿智多謀,個性鮮明,所以在明清時期傳播甚廣。壁畫往往選故事情節激烈的場面,將繪畫與戲曲融合在一起,把通俗易懂的故事情節用圖像的形式再現出來,仿佛藝術表演的時間停頓在那一刻,且在布局上動態靜態的畫面相結合,再將山水、樹木、動物等穿插其中,使人觀之則畫中有戲,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

圖1:壽峰寺伽藍殿三國故事壁畫(局部)
考察寶雞故事壁畫中的人物,我們可以看到人物“形象、服飾受到地方戲曲的影響,尤其是人物的服裝,男性是按照戲曲人物身份裝扮,形成程式化的模板,女性人物多是清式的民間服飾特點”。例如,天臺寺關帝廟兩側的三國故事壁畫中,男性服裝大多著蟒袍,有黑、綠、紅等色,寬腰闊袖并配水袖,腰間有玉帶,白底厚底靴這些都是典型的戲劇裝扮;另外,在南寨五圣宮、新民圣母殿的壁畫中,人物服飾明顯受戲曲的影響,圣母殿中圣母服飾更是展現出明清時期特點,云肩廣袖,具有戲曲服裝的裝飾性。
民間祀神活動在宋代之后有世俗化傾向,既有娛神又有娛人的功能。寶雞地區的村廟,廟前大多有敬神獻戲的戲臺,而演出圖像的題材也一樣出現在廟宇內的壁畫上,如五朝崚關帝廟有一組正在表演的仕女圖像,有吹笛的、吹簫的、撫琴的等八位仕女,人物形象生動,色彩清雅和諧。同樣,景峰寺吳岳殿內,在位于吳岳神像的兩側正壁的壁畫中,一組穿著清式女裝的仕女,瓜子臉櫻桃嘴,細眼彎眉,上披立領條帶狀云肩,正手持樂器在表演,似有敬神獻樂的禮儀功能,由于其處于正壁神像的兩側,加之兩邊的天將,整體在視覺上似乎為廟宇的神像營造出一個象征性的禮儀空間。
三、西府壁畫中的屏風圖像
屏風圖像的繪制在西府地區的民間壁畫中是十分典型的。陳倉區新民圣母殿、千陽南寨五圣宮、庵里村青龍寺等都保留有屏風圖像。屏風圖像有在山墻位置的,但更典型的是位于寺廟正壁的屏風壁畫。

圖2:千陽五圣宮正壁屏風(局部)
屏風在實際生活中既是一個物件又是一種繪畫媒介,在這里,顯然它是作為一種繪畫圖像,通過自身的獨特形式與裝飾,將屏風前面的人物和事件限定了各自的場所。坪頭新民圣母殿陪襯神像的屏風占據了整個正壁,雖然現在端坐在供臺上的是新塑的一位女神,但根據正壁多扇屏風的面積推算以前供臺上可能供奉著多位神仙。仔細看每一扇屏風上都精細地繪制有花鳥或者人物故事,畫風顯得和諧又清雅。同樣,千陽南寨五圣宮的正壁也繪制了裝飾性的屏風。匠人把屏風當作靜物來畫,屏風木頭框架及其上面的裝飾被描繪得一絲不茍,在屏風上隨意掛著眼鏡、折扇以及清代的官方歷書。正壁的屏風和其他壁面上的圖像形成立體空間上的組合,營造出居室內景。而晁峪金山寺左側殿保留的正壁神像背景的壁畫,畫面表現的是打開的幔帳,左右各有一名童子,一個手持拂塵,一個手持書卷,正中是一個神座。雖然畫面形式不同于屏風,但同樣是要營造一個居室內景。和屏風畫一樣強框定出一個狹窄的完全由所供奉神仙所支配的空間。因而,屏風不僅僅是神仙背后的背墻裝飾,它還裝飾著屏風前端坐者的身份,象征著殿堂里唯一性的尊位,村廟雖小,但廟內圖像的布置顯然是被視作一個蘊含禮儀元素的空間。
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壁畫呈現出不同時代的面貌,且其通過壁畫的形式將藝術的時代性與文化的地域性外觀固定下來。本文通過討論寶雞地區民間壁畫的圖像題材,提出了圖像題材與民間信仰理念等方面的聯系。寶雞地區宗教建筑中具有戲曲元素的壁畫、演奏場面等場景以及屏風繪畫題材在當時的文化和宗教背景下具有多重含義,壁畫及裝飾彩畫所營造的更像是一個象征性的禮儀空間。本文雖是關于寶雞民間壁畫圖像題材的討論,但其目的不僅僅是為了分析、探討具體的圖像題材,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分析壁畫中的圖像題材的內涵,我們可以管窺到關中西部地區民俗文化的時代特征及其持續的生命活態,了解民間民俗美術中所反映的視覺習慣和內置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