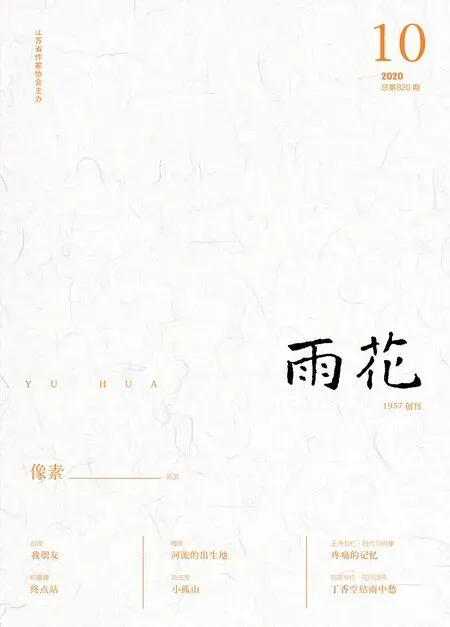豆腐坊
香河龍巷龍首上,便是柳安然家的豆腐坊。
柳安然,原本是位私塾坐館先生,整日與蒙童相伴,念些子曰詩云之類,日子過得頗閑適。有一年,在他手上痛失一副楹聯,自覺有辱族命,恨氣半途改道,開起了豆腐坊。
那副“蓬萊文章建安骨”的楹聯,為柳氏祖上一位大文豪之親筆。大文豪持此楹聯,親往香河認宗。原本該成為香河一段佳話,傳之后世亦能平添榮耀與自豪。然,大文豪身份特別,乃一代帝師。通常而言,這是件錦上添花的美事。但香河老輩人不這么看,伴君如伴虎,哪一天龍顏大怒,后果無法預測。歷史上誅連九族的事,并非沒發生過。
大文豪雖認宗無果,還是留下了那副楹聯。此楹聯之重要,不言而喻。于是族人商定,尊聯由柳氏輩分最高者保管,代代相傳,待時機成熟,將此聯請入宗祠,讓大文豪認祖歸宗。
幾代下來,那副楹聯就這么循序相傳。傳到柳安然手上沒幾年,這被柳安然視若性命之物,卻被一場意外的大火所焚。面對從天而降的大火,柳安然別無他法。只能恨得跺腳:“有辱族命!有辱族命!”
自此,柳安然改弦更張,開起了豆腐坊。
柳安然家豆腐坊,用的是自家后院的草房。草房通長三間。東間,屬鍋灶間。砌有大鍋灶,開三個灶堂口。最里邊支有一口大江鍋,為燒煮豆漿之用。中間和口邊兩個灶堂均小,口邊的最小,灶上安的是家用鍋。這兩口鍋,以日常家用為主。凌晨燒煮豆漿時,也會用來過漿。把大江鍋里的豆漿往另外兩口鍋里舀,以便完成豆腐制作過程中極重要的一道工序:點鹵。
中間,乃石磨間。支著副石磨,磨豆漿之用。磨盤以木桌為支撐。緊靠桌邊有只中等容量的粗瓷缸,承接磨漿時,從磨盤上流淌而出的豆漿。磨盤上支有三角形磨架。磨架橫檔處的麻繩拴于房梁之上,磨架呈水平。將磨架三角尖端套進石磨邊緣處的磨眼,推磨者手握橫檔,按順時針方向用力,石磨便開始工作。
西間,屬壓榨間。擺著張長長的木桌,還有幾只大水缸。長長的木桌之上,放著壓榨豆腐、百葉用的幾箱木框。每箱木框規制相同,呈正四方形,四周有面,上下無底無蓋。其底板、蓋板均需外上。
豆腐要壓,百葉要榨。壓,說來簡單,點好鹵的豆漿,倒進裝好底板的木框內,蓋上蓋板,加上幾塊重物件兒,廢棄的磨盤之類最好,干凈,壓重。
榨,工序就復雜一些。同樣得將木框裝好底板,在框底先墊上白粗布。這白粗布,稱作漿布。長得很,長度可達數十米。制作百葉時,舀一勺漿,放一層布。完成這道工序,講究的是舀漿勻,放布平,松緊適宜。
如此,一層一層,一來一回,裝滿一框,上蓋板,用根長木棍別住,下壓。這木棍下壓,靠機械原理進行力量傳遞。木棍一頭別在鐵環內,鐵環位于木棍下方,自然形成一股向下的牽引力。
榨,時間之長短亦講究。如何掌控,純粹靠經驗。做豆腐百葉的師傅多半不會說,這與點鹵類似,堪稱此行核心技術。
幾只大水缸,存養豆腐之用。新近制作好的豆腐,不能干放,得在水里養著。粗瓷水缸透氣,養豆腐好,不易變味。
百葉的存放,只需濕布包裹即可。技藝精湛的師傅做出來的百葉,一斤幾張都有定數。不用秤稱,張數一數,便知斤兩。一個字:準。柳安然出手便如此。
豆腐坊后身是一條小河,與香河相通。這新鮮的豆腐百葉,出柳家作坊,便可裝上小船,到外鄉去賣。
大哥柳春耕離家之前,劃船外出賣豆腐、百葉的,多半是妹妹翠云。
柳翠云劃著小木槳,邊劃邊吆喝,她的叫賣聲在香河上響起:拾豆腐——百葉咯——拾豆腐——百葉咯——
就這么邊劃邊賣,不一會兒,柳翠云賣豆腐的小船,就到了鄰村的水面上。沿岸水樁碼頭上,有村民叫喊,賣豆腐的,把船攏下子,給我拾兩方豆腐。
在豆腐、百葉這一組合中,百葉天然處于從屬位置。一般人們提及,總是豆腐優先,百葉次之。有時,僅言及豆腐,完全忽視了百葉之存在。
這一帶,村民所言“兩方”,并不確指,是個概數。柳翠云外出叫賣時日已久,自然知道村民們的意思。船到跟前總會再詢問:豆腐拾幾方?當事人自會報上數目,若是自作主張,只拾上兩方,多半會弄錯。
曾經有一段時間,柳家這賣豆腐的小船,由柳翠云一人獨行,變成了二哥柳春雨和他的心上人琴丫頭兩人結伴而行。那也算是柳春雨和琴丫頭相愛之后,度過的美好時光。
拾豆腐——賣百葉咯——柳春雨劃著木槳,邊劃邊叫喊。細心的一聽,便知他與妹妹翠云的叫賣稍異。柳春雨將“拾豆腐”與“賣百葉”區分開來,顯然更準確。其實,將“拾”與“賣”二字區分,也是當地這一行的習慣。
柳春雨叫賣聲剛出口,沒等有人招呼,坐在船頭的琴丫頭便來個鸚鵡學舌:拾豆腐——賣百葉咯——
看得出,跟春雨哥外出,琴丫頭有些興奮,開心得很。琴丫頭一開心,就要跟她的春雨哥一起劃槳。這賣豆腐的小船,空間容量并不大,艙中已擺著幾筐百葉、幾缸豆腐,承載的分量不輕。再加上他倆,小船吃水已經很深,稍一大意便有翻船之虞。
每當這時,柳春雨總是正色命令琴丫頭,規矩點兒,坐著別亂動。要不然,船一晃蕩,掉下水,不拉你上船。
用落水自然嚇唬不了琴丫頭。從小泡在水里長大的,哪能不會水?像她二哥那樣在東北當兵多年,弄得自己一點水性都沒有的,在香河極少。
琴丫頭根本不在乎春雨哥的臉色,更不理會他的“命令”。依然故我,搖搖晃晃地移到春雨哥跟前,想搶木槳,“人家要跟你一起劃。就要跟你一起劃!”
漂亮姑娘一撒嬌,難見小伙子不中招的。更何況,現在跟柳春雨撒嬌的,可是給自己雨露滋潤的小琴呢!柳春雨很快將自己主權的一半,拱手相讓,別無怨言。
賣豆腐的小兩口,把船靠過來!岸邊有新媳婦模樣的,在向小船上的柳春雨、琴丫頭招手。
被人家誤以為小兩口,柳春雨倒有些不好意思,不由得責怪了一聲:都是你不安分,不好好坐著。我不安分怎么啦?人家喊小兩口你不愿意?你說,你說!琴丫頭索性停槳不劃,故意刁難她的春雨哥。
生意在眼前呢,柳春雨暫不理會琴丫頭的話題,而是詢問岸上的新媳婦:請問需要拾幾方豆腐,稱幾斤百葉?
新媳婦見狀,掩口微笑著,說出所需豆腐、百葉的數量。心里想的是,真是情投意合的小兩口!其實,她是推己及人,自己新婚不久,正是如膠似漆的階段。眼前的一對青年男女,讓她見著就開心。
柳家的日子本該這么甜甜蜜蜜過下去,哪知小妹妹翠云突然不聲不響,把自己懸在了平頂房內。
柳家正屋三間,朝南,紅磚砌成的空心墻,俗稱“鴿子窠”。屋頂,用的是洋瓦。正屋前面,土坯墻圍成的院子。西邊建有平頂房,雖說墻壁也是“鴿子窠”,但頂是水泥澆的。這在當時較少見。靠正屋西廂房與平頂房之間,砌有樓梯,拾階而上,便可上平頂。這平頂的好處,一到夏季便凸顯矣。
前院的大門,與堂屋正對。院門用柳條和蘆葦混編而成,有了“柴門”之意味。說來,就柳家的條件而言,不至于置不起一副木門。看來是老先生有意為之。
大門直接出龍巷。院內靠南邊,三棵苦楝樹,一字排開。樹有些年頭了,枝枝杈杈都伸到了院墻外的龍巷上。
正屋后身并排而建,還有一進,通長三間草房,為豆腐坊。前后兩進之間,兩端用雜樹圍成后院。正屋的堂屋不僅有前門,好通前院,亦有后門,通后院。后院的草房與正屋一般格局,也開著前后門,前門通正屋,后門通水樁碼頭。
一家之主柳安然,住正屋東房間。當地風俗,東房間是上手,上手為大。正屋當中一間是堂屋,香河一帶的人家都是這樣的格局。正屋的西房間原本住著柳春耕、柳春雨兩兄弟。有一段時間,也曾出現過琴丫頭的身影。后來就只有柳春雨一人住。
前院西邊平頂房住的便是柳翠云。一家人,怎么也不會想到,翠云會選擇在自己房里結束年輕的生命。
她這樣棄父而去,難道不怕承擔不孝之名?就算舍得自己的兩個哥哥,那剛相處一年的對象王志軍,自己蠻滿意的,怎么舍得離開呢?再說,不就打了賭,有什么大不了的?遠的不說,近在眼前的水妹,未婚先孕,丑丟得不比你大?如今人家整日挺著個大肚子,不也活得好好的?自己這一朵花,才開呢!
挖草塘,是冬季勞作的主要農活之一。干此等農活,多半在大田靠圩埂的地方。選好地點,便可動鍬開挖,其深度至成人身高即可。草塘,通常呈正方形,偶有圓形。因其主要用來貯藏發酵草泥,故而被稱為草塘。每年冬季,香河一帶都會開展積造自然肥運動,組織發動社員下河汊湖蕩,罱泥罱渣,絞水草,裝運進這草塘之中。經一冬發酵之后,成為有機肥,開春便可發往大田,增添土壤肥力,供莊稼吸收。
一日,一幫大姑娘小伙子在一起挖草塘,挖的挖,抬的抬。從塘中挖出的泥土,除去用于加固草塘四周的,多余的必須運走。其運輸工具,通常是木杠加籮筐。也有扁擔挑的。這不,抬籮筐的姑娘為了步調一致,率先打起勞動號子:
歪尼個好子——歪尼個好子——
這邊姑娘們號子剛出口,那邊小伙子們立馬接上了茬兒:歪——歪子喲——嗬——
想占姑娘便宜的,眼珠一轉,號子從嘴中喊出,變了味:歪(玩)尼(你)歪(玩)子喲(要)——
號子,通常為枯燥農活之調節。調節干活者的步調,是其一。農活當中,個體單干的多,相互合作的也不少。這里面就講究步調一致。此外,更為重要的是,號子還能調節干活者的情緒,減輕勞動強度。然,在特定情境下,也會成為某種誘因。
時令雖已入冬,但只要天氣好,無風,那太陽曬起來,實在是暖和。眼下,一群青年男女,都是青春煥發、朝氣蓬勃的年華,在號子鼓動下,沒用多長時間,發焐了。身上的衣服成了累贅。一個脫,個個脫。這一脫,衣服自然單薄了許多,大姑娘們身體特定部位的弧線就凸顯出來。惹得小伙子們眼饞、手癢。有小伙子帶玩帶笑地動起手腳,你捏他摸的,笑鬧起來。這些姑娘們也不都是省油的燈,哪能眼看自己的姐妹吃虧?于是,在塘口邊追逐著想還手的有,在塘內舉起手中器械反擊的也有。
空氣里,散發出陣陣撩人的汗腥味,叫這幫青年人興奮、不安。有小伙子唱起了民間小調——
豌豆花兒白,
大麥穗兒黃,
麥田(那個)里呀,
大姑娘會情郎,
哪知來了一陣風啊,
哎喲喲——哎喲喲——
刮走了姑娘的花衣裳。
民間小調唱得小伙子們心口上蹲了只貓。貓爪子叨心,心就有些野,有了急切的愿望和目標。果不其然,有人盯著翠云豐滿的胸脯,直叫喚:翠云,如若你脫了上衣,在草塘里轉一圈,我們幾個給你買件嶄新的的確涼褂子。
一件新的確涼褂子!沒聽錯吧?那可是要花十來塊錢呢。要知道,這幫大姑娘小伙子做上一整天,才值角把錢,還只能記工分。想要拿錢,那必須等到年底隊上分紅才行。十來塊錢,在當時也算是一筆不小的財富喲。
況且,的確涼才剛剛時髦起來,幾乎是每個姑娘的夢想之物,求之不得。雖說眼下穿不上,但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么?那蝴蝶紛飛的季節,在向姑娘們招手呢。身為姑娘,一旦穿上花的確涼,那不就成了花蝴蝶?還不叫其他姑娘羨慕死!當然也會把那些小伙子,眼睛看得直直的。
賭!
賭!小伙們敲著扁擔、木杠,跟著起哄。籮筐上了天,草塘內樂開了花。這些騷公雞,撩著,哄著,想看好戲呢。
一件的確涼?吹牛吧。也有姑娘不太相信。
騙人是烏龜王八蛋。領頭的小伙子急得發誓。
賭!賭!有姑娘也跟著吼嚷起來,在一旁慫恿著。
不就在巴掌大的草塘里跑一圈么?賭就賭!柳翠云如魔附體,只覺胸前兩只玉兔,脹脹的,蹦跶著,直想往外竄。
好戲終于如小伙子們所愿,上演了。
待柳翠云一圈奔跑下來,渾身燥熱,直想喊出聲來。抬頭看時,四周竟空無一人。
柳翠云腦門上像被木杠猛擊了一下,“嗡嗡”的,她腳下一軟,跌坐在草塘中。愣愣的,傻傻的,好半天無什么動作,死死盯著遠處空白的天空。此時,天空中飄來一朵白云,亦如翠云潔白的上身。
猛地,翠云的手無意中觸到自己的乳房,“哇”的一聲,撲到那雜亂的衣物上,雙手狠命地掐那致命處,淚水不斷涌出來。
出了這種事情,閑話自然會多起來。村上人不怎么正眼看她了。
其實,一到夏季,香河一帶上點年歲的女人,多半敞胸露懷,搖著芭蕉扇,和男人們同坐一條凳上說笑、納涼。即便是剛開懷的年輕媳婦,給孩子喂奶,當了其他男人面,也敢撩起衣服,捏住白晳晳的乳房,將乳頭往孩子嘴里塞,毫不避諱。
然,做姑娘時,如若有這些舉動,則是萬萬不行的。稍有放肆,便遭眾人指責。本地鄉俗,歷來如此。
翠云這丫頭,平常蠻穩重的,怎么就做出了這種事情?膽子真大。聽說是為件的確涼褂子,丟人現眼啊。哎喲喂,將來出了門,那還有個好?巷口上,幾個老太婆、大婦女,七嘴八舌,正談論柳翠云的事情。
柳安然實在撐不住,已臥病在床好幾日矣。“家門不幸,家門不幸。我柳某枉為讀書之人,教子無方,教女無方。此命可休矣。”柳安然在自家堂屋里,把頭搖成了撥浪鼓。
盡管琴丫頭和柳春雨兩口子在事發的初期,都用心地看護著柳翠云。在柳翠云主動提出來照顧父親時,他們放松了警覺。一天早晨,柳春雨敲妹妹的屋門,無人應答。知道情況不妙,趕緊用力撞開屋門。見到吊著的妹妹,急忙將其解救下來。來不及跟老父親細說,便抱著妹妹直往大瓦屋奔。
萬幸的是,因為發現還算及時,柳翠云經醫療點醫生搶救,很快便蘇醒了。
令柳春雨兩口子想不到的是,在搶救柳翠云的節骨眼兒上,老父親竟離開了人世。這真讓柳翠云生不如死。父親的靈堂上,她哭得死去活來,完全是一副不要命的架勢。
爸爸——是我害死你的呀!你一句都不跟我們說,就走了,叫我還怎么活呀,爸爸——
未婚夫王志軍在一旁極力勸慰著,為翠云擦眼淚。這柳翠云,淚如泉涌,根本止不住。王志軍接到老泰山病逝的電報,立馬從部隊上趕到香河。當然,王志軍也隱約聽到了未婚妻前一陣子出過什么事。
柳春雨更是欲哭無淚。長這么大,他從沒覺得像現在這樣難。盡管身邊站著妻子,站著妹夫,但他仍然感到孤立無援。父親這一走,意味著從此以后,柳家的擔子必須由自己承擔起來。
琴丫頭連夜為柳安然趕壽衣。有縫紉手藝的琴丫頭,此時幫上了大忙。
原先,家里面倒是想給柳安然準備壽衣的。老人家一再阻攔,說無需花這些冤枉錢。百年歸天有什么穿什么。還是柳春雨再三堅持,給老父親先做了一副壽材。
香河一帶,到了一定年歲的老人,在世時就先做好棺材,叫壽材,也叫喜材。本地鄉俗如此,柳安然也就順從了。
面對白布覆面的老父親,柳春雨似乎聽到了他時常嘮叨的一句話,香河這塊真龍地,是出能人的所在啊!
柳春雨忍不住掀開白布,但見老父親雙目似合非合,雙唇似閉非閉。然,他老人家想再看一眼,想再吐一言,均已無可能矣。柳春雨徹底真切地意識到,父親走了,真的走了。這才顫抖著雙手,緩緩地,緩緩地,將老父親雙目合上,雙唇合上。瞬間,滿心酸楚,淚水止不住奪眶而出。
老父親去世,柳春雨無以為報。他心里清楚,父親一直很看重自己,希望自己能走出去,承延柳氏家族祖上的文脈。父親這樣的期盼,在柳春雨身上無疑難以實現。多年之后,柳家出了個大學生,經過多年摔打,成長為了楚縣縣委書記,年輕有為,口碑不錯,也算是沒有讓柳老先生徹底失望。此為后話。
柳安然的后事,在香河一帶辦得可算是風風光光。送花圈雖然在鄉間并不時興,但還是有不少人念及柳老先生的身份,送來了花圈。鄰居們多半是一捆紙錢送上門,以示禮數。幾天之中,村上的民眾幾乎戶戶都有人登門,甚至也有鄰村人專程前來拜祭,人們無不感懷老先生的人品。
送葬那天,香河整條龍巷,排起了長長的隊伍,酷似條蠕動的長龍。村民們都希望最后再送德高望重的柳老先生一程。
裝著柳安然靈柩的船,離開村莊,駛向香河公墓垛田。柳春雨、柳翠云作為孝子孝女,均一身重孝。也就是村民常說的,披麻戴孝。披麻戴孝的,還有翠云的未婚夫王志軍。此時,柳翠云手扶靈柩,嗚嗚咽咽哭聲不斷,一如船底激蕩而起的水聲,低沉、悲切。柳春雨、王志軍兩人立于船頭,一路將紙錢灑到香河的水中。那些紙錢,隨寒風飄在波浪之上,顛簸幾下之后,便隨波而逝。
香河南岸,亦有眾多村民為柳老先生送行。送葬船上高高的白幛在寒風中飄拂,村民們耳中不時傳來嗚咽的器樂聲,哀婉、憂傷。他們一直眺望著,目送著柳老先生離開村莊,離開香河。
香河潺潺流淌,水面上不時有幾只無名小鳥飛過,一支吹奏著哀樂的送葬船隊,緩緩地沿香河向垛田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