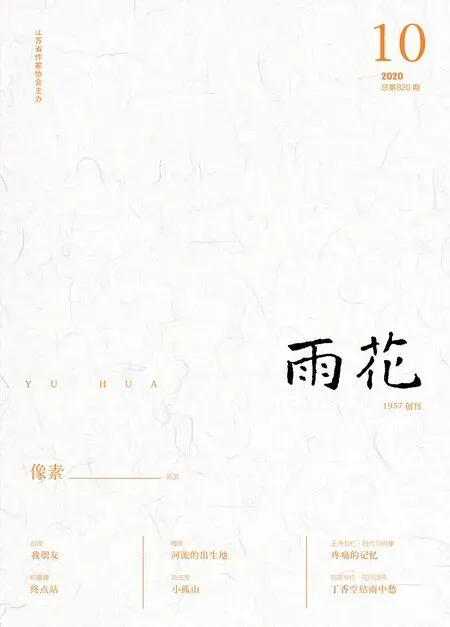山水與人的解放
這一年,時節剛到五月,廣州的酷熱便像山火一樣將人使勁烘烤。這種情形,數年未有。廣州即便到了夏季,那種熱也總是不乏潮濕,很少有干燥如火之熱。再加上年初新冠病毒肆虐至今,人人深居簡出,坐在家中,猶如困獸。
詩人黃禮孩來信息,相約去從化山中一聚,如同縫隙中有了光線,我立刻應允。
當天清早,在天河公園附近,和詩人世賓、黃金明匯合,一路談天說地,看著窗外的樓房漸漸低矮,直至一個多小時之后出現了綠色的田野,方才感到城市的控制開始松動。路過山腳的一個村落,傳言陸秀夫背著小皇帝跳海后,他的后人為避戰亂遷到了嶺南,先在南雄珠璣巷,后遷至廣州從化錢崗,也就是眼前的這個村落。歷史的煙云細節無從考證,但這個傳說意味深長,這是一種身份的寄寓,是對歷史的一種想象性的聯系與延續。
東南沿海對于大宋王朝的最后眷戀,也是邊緣對于中心的一種永恒渴念。這種渴念變成了挽歌,在隱秘地傳唱。我這個從西北內陸到東南沿海的人,時不時總能夠聽見,每每聽見,情緒總是變得綿延而恍惚。
車向山坡上駛去,爬上了一個陡坡,轉彎后,停下。我下車活動一下身體,看到一座小樓守著一個小廣場,一只疲憊的狗躺在樹蔭下。
保安走了過來,我們說:“是莫先生的客人。”保安點點頭,讓我們在原地等著,會有車來接。因為我們的小轎車底盤太低,沒法在崎嶇的山路上行駛。
等待之際,我獨自迎著一側的山巒走去。山巒仍在遠方,那是等會要去的地方。但進山之后便不能眺望,只有站在山下,才能看清山的輪廓。我的前方,有一道低矮的堤壩,不確定在它的后邊有什么。每走一步,堤壩與遠山之間的空間都越來越開闊,直至走在近前,發現那巨大的凹陷,是一片近乎枯竭的巨大湖底。近堤壩一側還有淺水,其余則如同茂盛的草原一般,長滿了葳蕤的綠草。從堤壩到湖底少說也有十數米,因此完全是山上蒼鷹俯瞰草原的視角。
一輛車停在遠處,猶如甲蟲般渺小。兩位女子從中走出,想在這年輕的草原上漫步,結果灘涂松軟,一位女子陷了下去,另一位女子趕緊去拉,兩人嘻嘻哈哈的聲音回蕩在空間之中。目睹這樣的場景,我心頭為之一振。被新冠病毒壓抑數月的情緒忽然松綁,我摘下口罩,這個柔軟的嘴巴刑具。我和世界之間不再有阻礙。
在遠山和轉瞬即逝的笑聲中,平遠空曠的境界從中抽象了出來。我想起了宋代馬遠的名畫《踏歌圖》。《踏歌圖》中,遠景是奇峰聳立,近景是山間小路,上邊行走著幾位神態各異的人,他們手舞足蹈的樣子,令人不免想象他們在共唱著一首歌。“豐年人樂業,垅上踏歌行。”畫上的詩句給予了提示,但我總覺得多余。此畫的高妙之處,在于畫面的中心是遠景與近景之間的一片留白,那是無盡的虛,也是無盡的意蘊所在。
畫于南宋的《踏歌圖》改變了北宋繪畫中的“遠觀其勢”,構造了一種“近觀實質”,逃出那種全景式的近、中、遠三景,僅選近景和遠景來呈現。這已經不僅是繪畫,更是人與自然關系的哲學。我們更愿意如何來看待這個世界?世界又是如何呈現自己的?《踏歌圖》激起的追問我一直難忘,此刻又被激活了。那《踏歌圖》跟我眼前的景分明是一樣的:遠景是山的寂寥清寒,近景是人的歡歌笑語。
矛盾嗎?沖突嗎?好像又不,好像又非得如此不可。
留白何在?在這湖底上方的空中,那里曾經是水的世界,現在已經失去了蹤跡。那蹤跡只在望者的心間。
我是一個望者,一個以望作畫的人。
我又一次聽見了大宋的幽微回響。既然如此,宋就沒有真正消亡,宋比元更持久。從這個意義上說,挽歌比殺戮更持久。
車來接了。
車駛進了山間小道,每到轉彎之際,都令人心臟收縮。容易暈車的人,怕已經開始忍受嘔吐的沖動。
手機信號格開始變弱,直至沒有了信號。這對于手機的奴隸們來說,并沒有感到自由的快感,而是陷入了茫然與焦慮之中。
前面的山坳里,停著幾輛車,看來是會合地點。我們下車,有幾位朋友坐在石頭上休息。有人說莫先生上山了。我坐了一路車,也想上山走走,活動下筋骨,看看山內風景。我和幾位朋友沿著山道,慢慢向上走去。濃密的綠色植物讓人心情愉悅,不時還能看見鮮艷的野花。我忽然意識到,假若沒有電子產品,在生活中要經常看到這么鮮艷的自然色彩,其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大約走了半小時,就開始返回。俯瞰谷底,發現有些樹木之高大是超乎想象的,它們幾乎有數十米高,生命的生長性得到了完美體現。我在看這些樹的時候,朋友給我介紹了莫先生的計劃:將這上千畝的地方,做成一個讓人可以安心投靠的棲息地。比如,有養老院,有學校,有度假地,類似一個社區,人們居住在這里,重新跟大自然生活在一起。
這倒是一個宏大的想法。
走回到山坳,人都齊了,莫先生也回來了。他身形瘦小,行動靈敏,眼鏡后的目光時常有很明亮的色澤。那個宏大的想法就在他瘦小的身體內滋長,驅動著他。簡單握手之后,他就招呼大家去吃飯。幾輛車組成的車隊,在崎嶇的山路上跌跌撞撞,緩慢爬行,然后到了一個山間平臺。那里煙火繚繞,原來是燒烤爐已經支起,牛羊肉塊、魚類和各類蔬菜被穿在竹簽上,只待放在火上烤。
眾人坐在小方桌前,便有山泉沏的綠茶端上。在此間隙,莫先生說了自己的想法。原來他是以做教育為本的,認為有六種教育對人的生命至關重要:“藝術陶冶人,體育健康人,科技發展人,生活培育人,心育愉悅人,生態影響人。”而他現在想做的事情,就是把這些融匯在一起,而這一切的核心,他稱之為“天人山水”。他說完之后,還用自己的名字開了個謙虛的玩笑。他說,他叫莫道明,就是講不明白。我暗暗想,他的名字很奇特,有多重解讀:要說講不明白,自然大道也是講不明白的。
將生命的能量用在改造世界上,最直觀的莫過于與自然的斗爭。將山丘夷為平地,將湖海填成平地,逆造化之力而行動,是人的力量的巨大展現。莫道明先生打算把余生用在這上邊,他的雄心壯志像是生命內部的大海,波濤洶涌,時刻準備溢出他身體的堤壩。大自然是需要發現的,沒有人的發現,大自然只是沉寂在那里,什么也不是。是人的目光照亮了自然,進而是人的行動改造著自然。在這個過程中,難道自然就沒有改造人本身嗎?當然,這是相互的,人也被自然所改造。人終究是自然的產物。
燒烤的食物散發出濃郁的香味,大家一邊吃著燒烤,一邊繼續聽著莫先生的講述。這是他理想的提前實現,我們也在他的言語中想象著這里的未來。
他提到自己為了規劃這塊地方,曾去印度的一個實驗社區考察。那是一個不對外開放的社區,他們費盡千辛萬苦才得以進入。他在里邊還看到了不可描述的奇跡。奇跡,是個人化的,在這里恕不具體提及。
我沒有向他求證具體的社區名字。我想起了印度建立于1968年的國際社區“曙光城”,那里有著來自五十多個國家的兩千七百多位居民。它的愿景是成為一座世界之城,讓所有國家的民眾都能在和平與進步的和諧中生活。超越一切教派,一切政治,一切國界,實現人類大同。在那里,人們嘗試著擺脫現在消費主義盛行的主流生活,探索一種更加符合自然靈性的生活。有位村民面對采訪,說出了讓人震驚的話:“有時訪客們會感到困惑,為什么我們還沒有實現夢寐以求的烏托邦?我理解他們的想法,但我認為重要的不是我們沒有取得的成就,重要的是我們每天早上醒來都愿意繼續嘗試。”
也許,生活就在于這種不斷的嘗試。
莫先生規劃的社區與曙光城有無關系,這并不重要,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這種試驗對現代生活的某些方面有所矯正。
現代生活已經被批評得太多了,現代生活當然不是一種完美的生活,但古代生活又何嘗是完美的?古代人對于古代生活的怨言是如此稀少,他們反而總是在向往更加古老的時代,這其中的意味是非常值得深思的。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現代生活需要矯正,古代生活就不需要矯正嗎?如果古代生活沒有被矯正,何來今天的現代生活?置身生活內部而盡力對生活進行改造,這本身就體現了生命的一種偉力,而生活以及無數生活構成的歷史也需要這樣的改造,以實現更多的可能性。
歷史已經沒有可能性,也正因此,歷史在行進的過程中格外需要可能性。
吃完飯,從小平臺搬到了下邊一個洼地,其間有樹可以遮陽。有古琴悅耳,還有年輕人組成的樂隊演奏,一點也不違和。如果有人愿意上前朗誦自己的作品,也悉聽尊便。眾人各搬小凳,隨意排列坐好,面前小桌有新鮮水果奉上。我全然放松,生出“雅集”之感。中國歷史上影響最大的一次雅集,毫無疑問,是蘭亭雅集,王羲之的書法名作《蘭亭序》不用多說。其實,我對《蘭亭序》的內容,也是念念不忘,就對心靈的沖擊而言,甚至大于書法本身。
那是一種生活美學,將日常生活的相聚變成藝術。后世相聚,仰望蘭亭,也不必自卑于風骨與才華的不足,重要的是,有了蘭亭雅集以及《蘭亭序》帶來的文化想象,中國人的每一次相聚都有了一種想象性的空間。它不是一種參考,不是一種標準,而是一個出口,讓眼前的相聚不止于眼前,而是嘗試著與歷史相接。
“俯仰之間,已為陳跡。”《蘭亭序》中的這句話,極為沉痛。所幸,蘭亭雅集的文化想象空間延續至今,而今天又在此玄妙空間中找到依據,并繼續展開。莊子說:“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也是在文化想象的意義上才能得到真正理解。人必須突破自己的狹隘與盲目,而與更大的事物構成譜系,才能獲得源源不斷的能量。就像唐人張懷瓘稱贊王羲之的《蘭亭序》時所言:“千變萬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發靈,豈能登峰造極。”
一個人的“神功”,依賴于“造化發靈”,實際上就是人對于造化的深沉領會。每個人都可能領會到自然造化的“發靈”,但總有人領會得更深刻、更徹底。
山間鳥鳴,與人聲唱和。幾乎每個人都上前發出了聲音,大山默默吸納了這些聲音,永遠不會吐露秘密。只有洼地的末端,有小溪在流淌,仿佛將人聲轉換成了水聲。
有山有水的地方,確實令人感到踏實。中國古人將大自然稱為“山水”,這是極具智慧的。山水,在中國人的生活和文化中,構成的人文意蘊之富厚是超乎想象的。文化對于生命的塑造,于審美上最關鍵。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自此,智慧與仁德便是中國文化試圖兼容的兩個方面,并化入到中國人骨子深處的美學當中。明代影響極大的文人袁宏道說:“意未嘗一刻不在賓客山水。”內在的精神被山水所俘獲,竟然每時每刻都與山水關聯,山水已經成為生命的骨血。清代的張潮在《幽夢影》中說:“有地上之山水,有畫上之山水,有夢中之山水,有胸中之山水。”把山水分了類,意味著山水對于生命的一層層滲透。
在這里不得不提中國原創的兩種思想: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它們為中國人的生命樣態設定了兩種狀態,要么“入世”,要么“隱逸”。入世是儒家的范疇,道家傾向隱逸。隱逸,太難了,甚至可以說,沒有將入世作為前提的隱逸,都是對隱逸的誤讀。否則,為何只有陶淵明的鄉野生活是隱逸,而山野樵夫的普通生活就不是隱逸呢?
就像平日里來山中,就不如新冠病毒肆虐之際來山中。這其中的滋味便包含某種精神的探詢,這山便不再是土石的堆積,而成為山本身。
老子說:“道法自然。”這其中便有太多可以領悟的東西。道與自然之間并非是完全等價的事物,而是大道要向自然本身去探詢。這就意味著,道不是先驗的,更不是給定的,而是在人與自然的關系變化當中。
聽著音樂,凝視周遭山林水石,忽然就被融化了,仿佛那個被肉身承載的我,漸漸不再狹隘,而是與目光合一,進而與目光所及之物合一。天人合一的感覺,就是以此刻這樣的感受為基礎的。
劉勰《文心雕龍》中有八個字:“山沓水匝,樹雜云合。”這是自然景觀的呈現。在這句話后面,跟著八個令我極為難忘的字:“目既往還,心亦吐納。”目與心的關系,構成的是人與自然之間的通道。這個通道并非敞開的通衢,而是藉由藝術的創造而呈現和生發的。比如山水畫,比如詩,比如文章,比如音樂。唐代大詩人王昌齡《論文意》中如此談到詩在生命中的發生:“夫置意作詩,即須凝心,目擊其物,便以心擊之,深穿其境。”這個看法正好與劉勰的看法構成互補。劉勰說的是從目到心,而王昌齡恰恰說的是從心到目,要將心的力量通過目光投射出去,這個力量是極大的,是“擊”,而不是“觸”,并“深穿其境”。兩種說法不僅是互補,也是抽象與具象、發生與發聲的互補。劉勰看重的是寫作在人類精神與自然能量交換過程中的大尺度,而王昌齡所說的是“寫”的穿刺,以及在這個過程中,個人之思如何能夠最大限度地獲得自然的能量。
作為一個寫作者,我太能理解王昌齡所說的意思了。那是一種隨時準備好的狀態,如同箭在弦上,等待著一個微小的擾動,箭矢便如電射出,如果能夠射中那個擾動的目標,并且洞穿擾動的原因,那么,這樣的寫作將會是極為有力量的,是強悍的。
人的自由為何與藝術、與寫作有關,就是因為人唯有在這個過程中,才深刻理解了自然,理解了人自身。從馬克思到馬爾庫塞,都提醒我們要注意人本身的自然屬性。我們時常會忘記這樣的自然屬性。馬爾庫塞說:“解放最終和什么問題有關,亦即和人與自然的新關系——人自己的本性與外界自然的新關系有關。”解放就是獲得自由的過程。從來不曾存在百分之百的自由,人類的自由是靠著解放的過程而緩慢獲得的,這種獲得不是物的給予,歸根結底,還是一種精神的領悟。所以,自由才是珍貴的。
當我們發現了山水的時候,發現了山水當中的超越維度——天,發現了山水當中的生命維度——人,我們就是在領悟自由,就是在緩慢地實現人的解放。
黃昏毫不遲疑地降臨,日暮時分,天氣沒有涼爽,暑氣反而被熱透的土地釋放出來。再風雅的集會,也會有曲終人散之際。就像永和九年那場讓王羲之寫出了天下第一行書的聚會,已經散場了一千六百多年,這個數字注定還要增長下去,直至文明的終結。還有更多的雅集,已經無法追溯,消失于時間的幻象當中。
莫先生沒有再說些什么,在音樂聲中,他應該想了很多,但有太多的話只能藏在心底,無人能說。放眼廣州從化的這一片山水之地,不能說這是桃花源,更不能說這是庇護所,只能說,這里有可能實現人對自身的安放。一個人可以把自己的總和投入到青山綠水當中,為自己的生命尋找一個可靠的、穩固的邊界。
足矣。
車出大山,手機信號重新恢復。從此一瞬起,那山水便不再是那山水。回復一些俗世信息,然后發布這里的山景照片,配上一句實實在在的文字:“逃入大山,一會兒古琴,一會兒蔡琴,好像瘟疫已經結束。”微信朋友圈的熱鬧開始了,有多少人渴望著逃離,正如我。
而此時,車掠過了山下的村落,那個傳說住著陸秀夫后代的村落。來時,心心念念要去走走,可回時,就這樣平淡路過了。
心底默念著白沙先生的詩,如同宗教信徒默念著經書上的圣文:
“江山幾處堪還我,泉石邊頭合有人。高著一雙無極眼,閑看宇宙萬回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