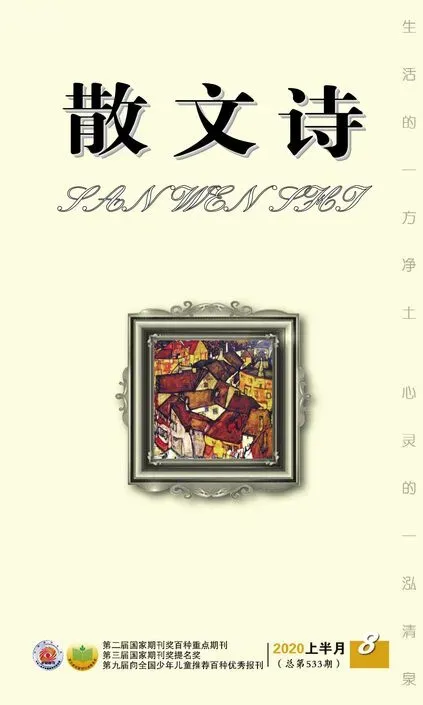南風北吹
◎費城
雪落在人間
雪落著,靜靜的墓園。那個掃墓的人獨自站成了空曠,站成樹影下蜷縮的倒影。他埋頭痛哭,仿佛需要將悔恨、愧疚與歉意,來填補這余生的缺口……
無聲的雪,無邊地下著,為世間騰出空白。在這匆忙的人間,還有什么不能被歲月消解?
比如貧窮、衰老,以及那些不能被時間喊出的創痛——這生命的沉軛、朽損的疤痕,都將在一場大雪之后,被世界遺忘得干干凈凈。
雪落的人間,一定有些什么,值得我們倍加珍惜。慌亂的腳步退避至人群之外。而草籽,深埋在積雪之下,獨自承受著黑暗,等待生命被再次打開。
在鋸木場
在鄉居鋸木場,寂靜像陰霾籠罩著我。那些高低參差的棗木叢,抖落下滿地葉子,彼此攙扶著枯瘦的樹影,站立在木窗前,它們被大風吹動的樣子滿是驚惶。
那些黑黝黝的樹影更暗了,樹枝枯折,仿佛壓低了天空。而院墻之上,衰草連接遍地秋光,已經沒有人愿意拔掉它們。仿佛那里是它們的家,根系很深,早已經透徹了瓦壁。
一把云梯,從天上垂落下來,與舊年所見一樣。仿佛多年以前,那個寂寥的少年,獨自站在明晃晃的寒風里,看一棵拐棗樹,如何在整個季節最末的日子里,落盡全部葉子。
啊,心地荒蕪之人,多少年過去,早已經不知去向。繁霜降滿的莊園門外,路人們正小心探詢故人的消息。
時光與流水
需要用多長時間,來安頓我們的生活?月光下的村莊幽暗,清風在草葉間游離,時光如流水,于是我們便生活在水中,像一尾銀魚,潛經歲月的遺址和廢墟。
需要用多長時間,來安頓我們的靈魂?當輕快的馬車運來天邊的落日,芳香的稻穗越過谷倉,仿佛要堆到天上。需要用多長時間,來安頓彼此的愛情?那草葉間游吟的鳴蟲,是不是十八年前的那一只?是不是也曾見證月光的衣妝和燭照下含淚的眼睛?
時光流走了多少泥沙,雖然我們從未曾離開。需要用多長的時間,才能平息你我血液里的濤聲?當幸福的姐妹齊集河畔,唱響動人的歌謠,那流水洗亮她烏黑的發辮和款款的目光。
你能聽懂歲月深處,涌動的希望和夢想嗎?
南風北吹
挑開月光,摸索幾聲蟋蟀的淺唱。手持一根青草,我便能拾回曾經丟失的童年。陷在菖蒲的凝綠里,生銹的犁鏵敲打出土地喑啞的聲響。親臨土地,便能觸到作物拔節的喘息。
今夜,借一點點星光,便能照亮遠方家門的木紋,照亮屋檐下的牲口,以及頭纏白布、滿臉淚水的母親。今夜,你在燈下栽種誰的華發?誰在向晚的風中輕喚我的乳名?
途經每一所鄉村旅店,我試圖用歌聲詮釋,一個旅人全部的愛或憂傷。
南風一路北吹,在舊居的院前駐足,聆聽鐵匠鋪徹夜敲打星空的脆響,仿佛在給歲月打上補丁。而芬芳我生命旅程的,依然是旅途中那只戲風的蝶么?
如果今夜夢里有風,我該搭乘哪一片淺白的月光回家?
我們未知的幸福
夢中,未知的幸福一再離我遠去,形同雨中的燈籠,穿行于草芥、林莽,像從來無法捕捉到的蟲鳴,在齒芡草的故鄉,在遠方,微微搖擺……
當命運的塵土再次歇落在我的肩頭,那些土地上奔跑的花朵是衣衫上的補丁;當一滴堅忍的淚水,凝固在眼角,我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沸騰——
時間戛然停止。
雖然記憶,從未停止過遺忘。那片雜樹間的草地,干草棚外的樓梯只允許一雙歲月的大手悄然撫摸,像無法尋訪的童年,期間也曾棲落著鳥鳴。
而刈草人,正在別人家門外眺望未來,潔白的曙光,正從她烏黑的鬢發開始,瞬息穿透她貧窮的一生。有沒有更簡潔的詞句,拼湊出藍天和夢想?
春天的搬運工
在春天,一只螞蟻上路了。
它們將云影和炊煙,隱藏在光陰背后,從春天的根莖出發,穿越返青的麥芒,把一季的相思運抵麥穗飄香的故鄉。
在春天,有誰會像一只螞蟻那樣奮不顧身?沉溺在春天的風景里,不發一言,沿途交還緩慢的時光,跟隨一個路人,從內心的荒蕪走向季節的縱深、無垠,走向希望與繁華。
在春天,有誰能夠真正讀懂一只螞蟻內心的深重?它們的語言是大地的辭令,在天地間改變著四季;它們小心翼翼的觸角,不經意引爆了,一株果樹遲遲未至的花期。
在春天,一只螞蟻上路了。它們負重前行,用頭顱輕叩大地,試圖用腳印丈量人生這部大書;它們低眉順目的樣子,仿佛迫不及待向命運遞交虔誠的答卷。
眾草之上,這些春天的搬運工,它們有著比天空更遼闊的魂靈。我愿借一朵野花的心聲,說出:
每一個春天綻放的過程,與每一只辛勤的螞蟻有關。
緘默的石頭是一種歌唱
緘默的石頭是一種歌唱。歌唱在季節之外、人群之外。我需要多少勇氣,才能抵達你內心的滄桑、憂郁和苦澀?
昨夜,月光照耀黑色的山頭,那些遲開的花朵,綻放如河流兩岸的石頭,冷漠、凄清又惆悵。這是怎樣一種花朵?它綻放在石頭內部,是否有著石頭一般堅硬質地的核心?
淚水滑過臉頰。一只候鳥循著季節的尾音,為我帶來今年的雨、去年的霜。在這個季節的深處,靈魂綻放著絢麗無序的花朵。它們都是石頭的花朵。
緘默的石頭不只是一種歌唱,它永遠痛苦的內心,在感觸與碰撞中濺出水樣的火花,必將窮盡我的一生,告別內心的憂傷和痛楚。
在白鳥飛回的季節,雨水如同淚水一般清澈。那個涌動著幸福潮水的夜晚背后,那個火山凝固的清晨背后,石頭藏起它們多情、含淚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