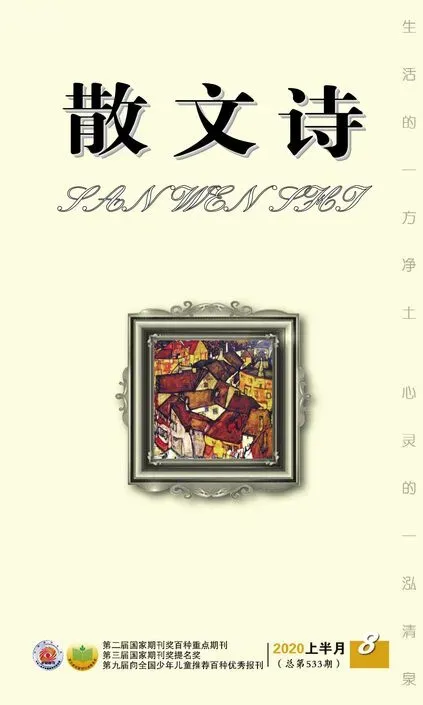背后
◎彭俐輝
發生過許多事的地方
發生過許多事的地方,有人安靜,有人尋求新的故事發生。
開始即結束,結束卻終沒結束。
一件舊衣飄飄,一泓溪流繼續流淌。
風變換著方向吹來,東西是一種,南北是另一種。
是的,是風把許多事越吹越淡。
是風,讓我多年以后,站在發生過許多事的地方,疑竇叢生。
——那些事真的與我有關?那些人真的與我有過交集?
發生過許多事的地方,還在發生許多事。我在丟盔卸甲的岸邊,看見帆船遠去,一只接一只,不分前后。
異鄉的路口
左邊南方,右邊中原。路呢?路在每一次風起云涌的時候,變成胸無大志的波瀾。方向決定步速。
陽光直直如鉤,像是要釣走什么。
車來車去,扔下一地塵囂,不確定的去留,不確定的舍與得。
一個人的路口,燈盞,路標。
川流不息的夢,碾軋川流不息的夜晚。
明月一朵,間或溝渠深深。
在深夜,敲開一顆核桃
夜深了,我要把一顆大腦,從堅硬的包藏中挖掘出來。
它在想什么?是否契合了我的想法?
我敲,七八粒星星窗外,三五枝疏影墻邊。
我要慢,恍如耐心對離愁。硬碰硬,必有一傷,必有悲從中來。
冷暖自知的夜晚,只有安靜對安靜。
我試圖接近一種思想,凝視是一種,剝開是另一種。
高巖不是巖
高巖不是巖。是一個長長的斜坡,是上來下去時呼吸轉換的一個驛站。云朵凝止,三五幾人對坐而望。
風不停,間或跑進一座小亭,把石凳吹暖。
幾棵梧桐樹站在兩側,掛滿的閑愁,壓低了匆匆的身影。
雨季說來就來,雨水奔跑的時候,卷起一地透亮,仿佛有什么在追趕,越跑越快。
高巖不是巖,假山占幾分,噴泉占幾分,余下的,留給天空去想。
隨便走走
很多個下午,我突然就奪門而去,扔下不想回頭的空屋,不知所措。去哪?哪又在哪?
公園,湖邊,曠野。仿佛哪里都可以,又好像哪里都沒必要,就像去想一個人,想著想著,就想不下去了。
而人已在路途,那就隨便走走。車站,商場,廣場,讓坐不住的身體,在時光里晃蕩。
沒有永遠的有意思,也沒有恒定的沒有意思。樹因為相遇而喜悅,石凳因為我的落坐而急劇沉寂。
我不走向花朵,那過于艷麗。我也不去殘墻,容易想起斑駁。我只是隨便走走,走到草地,就折一枝清新,走至書店,我就為密密麻麻的書,重新命名。
命名出我歡喜的那一種。
步行街的步
多數時間,我是與建筑平行。偶爾,我也垂直問路。但走不遠,人群間異樣的目光會打亂我的信心。
步行街的步,不是朝前,就是往后,一群人盲目地走,一些人懷揣目的,直奔目的。熱鬧非凡,各帶光暈。
身在而心不在的,猶如閑庭信步,唯有不問遠近,跟在風的后面,忙得失去了自我。
前是后,后是前,沒有方向的步行街,腳步自亂。
從舊城到新城
寬了的,不只是路,還有無法確認的現在。
陡坡降了,有了風景的河岸,棲息著謎一樣的飛鳥。斷口出現新徑,熟悉的轉彎處,多了步入天空的云梯。
一座天橋從此名正言順。
坡上的花都開到了腳尖,一路走去,總覺得兩旁會突然竄出一段記憶。
一個書攤,一家裝裱店,一碗小吃,一個修面師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