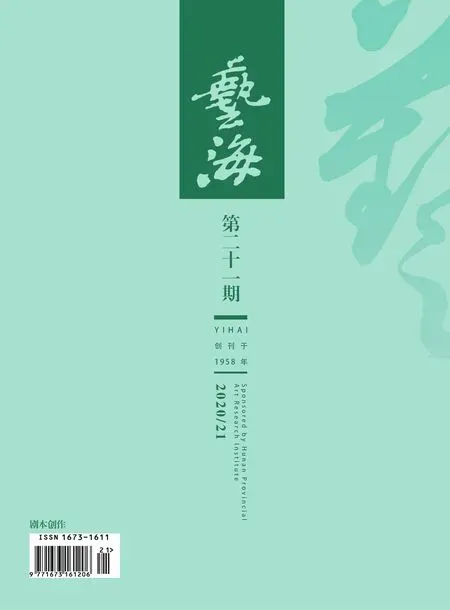一部從生活中打撈出來的劇本
——話劇《小鎮琴聲》創作談
■ 李寶群
話劇《小鎮琴聲》已由國家話劇院于2018年搬上舞臺。這個劇本的創作之路曲曲折折,讓我感觸良多。
《小鎮琴聲》是我和青年編劇潘乃奇從生活中打撈出來的。
這部劇本寫的是浙江農民造鋼琴的故事。故事背景是浙江德清某小鎮上一群農民從八十年代開始,在缺少原材料、缺少技術人員、缺少資金等情況下,敢為天下先,積極引入上海的工程技術人員,克服重重困難艱苦創業,最終建成了聞名全國的鋼琴小鎮,由他們生產的鋼琴暢銷國內外。故事很獨特,很有傳奇性,人物也很鮮活,其中蘊藏的東西也很豐富。
我和乃奇都被這一個題材深深吸引了,深感這是一座富礦,可以挖出金子來。
但是,創作過程中一個個難題出現了,如同一座座大山一樣橫亙在我們面前。
(一)
首先是如何熟悉這片生活,走入這些生活中的人以及生活中的故事。
從生活出發,到生活中去,是創作的基本規律。我和乃奇一次次前往德清,最終和小鎮上的人們成了朋友。我們走進了一家家鋼琴廠,走進了一個個德清人的家庭,結識了一位位當初的創業者:當年從上海請工程師的老廠長、現在正管理現代化鋼琴廠的女經理、正在一線工作的技術工人、鎮上開飯店的老板娘、致力于研究德清歷史文化的學者、新一代的鋼琴人……還有他們的妻子、丈夫、朋友。德清人熱情好客,相處時間長了,便滔滔不絕地給我們講起了很多當年的故事以及這些年創業的事……每個人的生活都是那么精彩,每個故事都是那么生動,都足可以寫出一部部大書。我們仿佛闖進了一片生活的海洋,一個充滿了生命光芒的嶄新世界。
那些日子,我們的足跡踏遍了德清的山山水水,這里有很悠久的歷史文化遺存,有很淳樸的鄉風民俗,有秀美的山水田野,一代代德清人生于斯長于斯,他們的血管里始終流淌著自強不息、開拓進取的血液,敢于走出去尋找新的生存之路,敢于創造新的生活,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群鄉村的農民敢于做別人想都不敢想的“鋼琴夢”,不僅與改革開放那個時代有關,也與他們的歷史文化傳承有關……
那些日子,我們無時不被德清發生的一切所感動,內心不斷涌動創作的靈感與激情,中國的農民、中國的鄉村值得寫,我們要寫出一部真實有質感的農村戲,一部不一樣的農村戲。
(二)
進入構思階段,新的難題不斷出現。
怎樣把豐富鮮活的生活素材寫成戲?選擇什么的視角切入這一題材?怎么從生活到藝術?怎樣藝術地聚焦人物?怎么才能不陷入一般化公式化概念化的套路?選擇什么樣的戲劇樣式、什么樣的風格、什么樣的舞臺呈現?怎么才能讓戲更具有現代意義?
當下中國戲劇舞臺上有很多農村戲,如脫貧致富戲、扶貧戲、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戲,一個長期困擾我們的問題是,很多創作都缺少審美品格,尤其是缺少獨特豐滿且令人難忘的人物形象,近乎政治宣傳戲。我們希望跳出這一套路。我們堅信,藝術即人學,著力塑造有血有肉有靈魂的人物,用人物說話,展現人物個性化的命運和內心世界才能打動臺下的觀眾。
《小鎮琴聲》用大量筆墨塑造了農民阿德這一鄉村小人物,自兒時起他就夢想像白鷺一樣向遠方飛,長大以后他走南闖北開闊了視野,回到小鎮后成了出名的辦廠“能人”,有文化,腦筋活絡膽子大,敢想敢干,做事情“一根筋”,只要他看準了的事,千方百計去做,能把別人想做卻不敢做,做不成的事做成,他身上還有農民特有的狡猾、精細和智慧,懂得審時度勢利用政策,利用“時間差”來最終達成愿望。他有一個小人物的內心世界,創建鋼琴廠最初的動機也是“阿德式”的——為了得到心中戀人文鶯的愛情。為了實現這一“偉大目標”,他去上海請來了工程師和技術員,他說服了旺財叔、劉一手等鎮上的各種能人和老百姓和他一起干。在創業過程中,他經歷了國營企業要找回工程師、背負違反政策的罪名險些被抓、多次實驗失敗、愛情失敗、文鶯與鋼琴家結婚、旺財等多位合伙人與他分手另建廠子、企業資金告急、旺財等用他的旗號到處行騙、鋼琴小鎮聲譽受損、客戶紛紛退貨……一個個困境,一場場危機,四面楚歌,舉步維艱,掙扎其中,煎熬其中的阿德有過痛苦、迷惘,也有過孤獨和無助,但他的夢沒有夭折,他沒有倒下,他的夢想與野心反而越來越大,他想成為中國琴王、世界琴王……
阿德只是一個鄉村小人物,不高大更不完美,但這一人物身上顯現了中國農民特有的異常頑強的生命力,也顯現了許多底層小人物為了生活和夢想百折不撓,不肯服輸,屢敗屢戰的強勁精神氣質。中國的改革開放實際上是對人的解放,是對蘊藏在普通小人物身上的創造力的解放。中國經濟的進步,中國社會的進步,說一千道一萬是由億萬小人物對生活的追尋,對夢想的追尋,用血汗和智慧奮發創造筑成的。沒有許許多多的“阿德”,便沒有中國鄉村的今天。
圍繞阿德,我們還精心塑造了阿花、旺財、八級半、鄭大錘、劉一手、三剪子、阿清、水根等一群鄉村小人物,還有從大城市來的工程師歐陽、一生酷愛越劇的名演員文鶯、出國深造歸來參與企業管理的鄉村青年小峰,他們各具個性,各有各的人生故事,各有各的“戲份”,形成了一部鄉土氣息濃郁又有年代感的群像戲。
這些人物都來自生活,又沒有簡單照搬生活原型。在生活真實的基礎上塑造藝術形象,一直是我們創作這個劇本時的重要追尋。
為了寫活這些人物,我們在寫作過程中又一次次回到德清去補充生活題材和汲取靈感。劇中的阿德身上有多位早期創業者、多位鋼琴廠廠長的影子。阿花的原型則是當地一位極有個性、敢恨敢愛、開朗熱情的飯店女老板。旺財這一人物的塑造得益于多位早年外出闖蕩做過多種生意的個體戶的經歷。文鶯、阿清、小峰等也都有各自的原型,而且不止一個。此外,我們還深入研究了很多著名“浙商”代表人物的人生故事,從中汲取創作養分,進一步豐富和深化了我們筆下的人物形象。
從生活出發,對生活持一份敬畏之心,寫作時忠實于生活、忠實于對生活的感受與體驗,真誠地表達。長期以來,這種現實主義的基本創作方法經常被人詬病,但說到底,藝術是來自于生活的。生活永遠是一片滋養創作的沃土,一個極為重要的創作源泉。好的劇本創作就是要從生活中打撈劇本。《小鎮琴聲》的創作讓我們再次真真切切感受到了這一點。
(三)
寫作中遇到的另一個難題是,怎樣講述這些鄉村人物的故事?
有了人物,有了故事,有了相應的藝術內容,必須尋找到一個“最合適”的藝術形式,到底應該選擇什么樣的結構才合適?這也是一直困擾我們的一個重大課題。
為此,我們多次推翻原有的構思,嘗試過很多種戲劇敘事架構。最初,劇本是按著時間順序一個年代接一個年代“順時針”展開的,但寫了幾稿總是感到不滿意。幾經尋找,最終我們找到了現在的劇本敘事方式——即采用老年阿德在病中坐著輪椅與老伙伴水根、旺財一起回顧自己的一生,用這種回溯敘事的方式打開全劇,并將其貫穿始終。隨著老年阿德的回首往事,故事有層次地而且十分自由地展開來。他時而是敘說者,時而又進入到往事時空之中,時而又跳出來,回歸敘說者的身份。有時他還與往事時空中的阿德,兩人產生交流,這樣的戲劇架構使得全劇更具人生況味,更有滄桑感,全戲也會更有韻味。后來的演出證明這一選擇或許是最合適的。
悲喜交加,悲中有喜,喜中有悲,既注重生活化也注重舞臺的詩性和詩化,既注重再現寫實,也注重表現,注重寫意,這也是我們在不斷尋找的過程中逐步建立起來的文本風格。漫長的歲月里發生了許許多多事,有的令人沉重,有的諧趣可笑,由幾個老人的視角回望過去的生活,當年那些悲劇意味的往事也有了幾分喜劇的意味,有些喜劇的場景也參雜著悲苦和艱難,而真實地再現生活,保持鄉村生活的質感、時代的質感,固然是我們要追求的,但鄉村的生活、小人物的生活永遠有一種別樣的詩意,這種來自生活的詩意也是我們想寫出來的。這些風格上的定位,后來在著名導演傅勇凡的執導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
(四)
《小鎮琴聲》的排演過程相當曲折。最初,德清方面計劃與本省的話劇院團聯合推出,后來劇本被國家話劇院看中,又決定改由國家話劇院與德清聯合制作。劇本修改了幾稿以后,導演人選又發生了變化,檔期已經排定,新導演才最后確定。這期間,劇本前前后后共修改了十余稿,反復聽取各方意見,反復調整反復打磨,進入排練場之后,劇本仍在不斷修改完善。每一次修改,我們都堅持從生活出發,以寫人為中心,著力豐富人物強化人物。我們渴望奉獻給觀眾一臺活生生的人物,渴望在舞臺上涌動出一條由人物的命運起伏沉浮組成的小人物心靈的河流。
感謝國家話劇院,也感謝德清,這是一次難得的實踐機會,讓我們走近鄉村,走近一個個鮮活的鄉土人物,圓滿完成了這部通過小人物的塑造顯現中國農村幾十年發展變遷的農村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