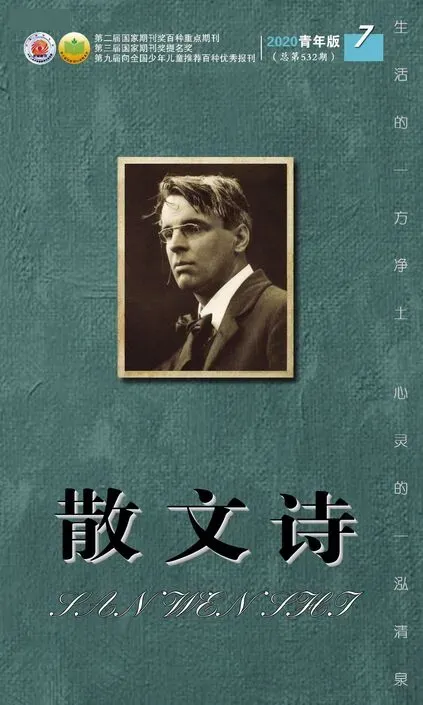確切的日子
張翔武
確切的日子
白天, 城里沒多少人, 到天黑, 人就更少了。
地鐵、 大巴、 公交車這些鐵皮昆蟲全縮回了它們的巢穴, 延長了冬眠。
晚8 點, 面包店已經打烊。 沿街一扇扇卷閘門緊閉著, 即使白天, 大部分鋪面也是緊閉著的。 有些店門上貼著告示, 說20 天前就該重新營業。 個別店主把重新營業日期一改再改, 直到失去了耐心, 再也不去改。 誰也不知道那個確切的日子。
沒有買到面包, 我們隨便兜轉了一會兒, 然后轉身回家。
除了一對眼睛, 我們已經好久沒有見到人們的臉了。 只有宅在家里的時候, 才能看到電視劇里人物袒露他們的焦慮、 喜悅和恐懼, 在那些和以前一樣的妝容精致的臉上。
一些人和他們的狗站在逐漸濃稠的夜色里, 放風, 呼吸, 漫步。 狗不知道人類世界出現了什么變故。
我們默默地走。 偶爾遇見一些行人, 他們也沒有說話。 別人迎面走來, 我們就提醒自己小心避讓對方。
眼睛主要用于看路。 我們開始習慣于安靜, 像剛去參加了一場葬禮。 而別處的城市里, 確實出現了為數不少的死亡, 一些遺體失去了與未亡人告別的機會。 在那些從來不曾見過的死者里, 只有少數幾個名字被我們記得, 但不敢保證能記多久。 更多人不過是死亡數據中的基本單位, 可是每位死者仍帶來了一些人漫長的悲痛。
沒有什么值得高興的事, 我們苦等確切的日子的到來。
旅 途
一個人穿過早晨的墳地去上學。
一個人陷入泥濘, 高一腳、 低一腳走路回家。 大堤望不到頭,長得叫人害怕。
一個人注視燃燒的蠟燭。 下了晚自習, 同學們都回了寢室。
一天下午, 我踏上一艘客船, 迷糊中聽見馬達響了整個晚上。 又有多少次, 我登上火車, 坐在窗邊, 注視那些山山水水不同的著裝。
我想著盡早到達目的地, 融入新的地方和新的人群。
直到回想起來的時候, 我才明白, 那些漫長旅途才是我難得的平靜, 像有所準備, 將全力去干點什么。
點 火
我們去給祖墳送燈, 帶著稻草、 香蠟、 紙錢。
天色漆黑, 我們穿過田野回來。
我們又抱起一束稻草, 拆散, 分成小把, 點燃。 我們高高舉起火把, 邊在菜園里、 田埂上快速走動, 邊大喊: “趕茅果!”我們加快步子, 小跑起來。 嗓門也更大了。 那句話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們不是很清楚, 以前也只從父母口中得知了一個大概。
火焰, 煙霧, 叫喊, 奔跑, 像一場驅逐儀式。 那些被驅逐的東西和我們手持火把追尋的意義都看不見, 只在我們的感覺之中。
火把照亮我們的臉。 在菜園、 田間磕磕絆絆, 奔跑, 叫喊,與黑暗中的某些東西搏斗——它們總是敗退又重來。 那種感覺讓人興奮、 刺激, 還有那么點兒神秘的意味。
黎明時分, 我站在田埂上。 昨夜稻草燒完的黑色余燼殘留在開始返青的野草上, 天地之間, 一片寂然。 我打量煥發新綠的戰場。
秧 雞
早上, 他起床, 打開書本、 網頁, 所有文章只剩下標題, 全部內容像被砍伐的森林消失不見, 甚至斷樁殘茬都被焚燒, 書頁不過一片荒原。
他想去寺院借來幾本經卷, 里面沒了菩薩或圣像, 這些道場承載古老的空虛, 老鼠、 流浪的貓狗出沒庭院, 山茶花已經頹敗, 雜草掩蓋了地磚。
人們對一個聲音著魔, 上癮般癡迷他的話。 在路上, 人們木訥或狂熱, 好似大腦萎縮, 對世事無動于衷, 唯一的反應只有本能。
從前, 他想做一只鳥。 可是無論在哪里, 他發現自己都置身于籠子, 只有大小的區別。 直到他瘋了, 那些追捕的人終于罷休, 因為沒人愿意花費時日陪一個瘋子玩耍。 那個人在夜里仰望月亮, 常常喃喃地說: 我是一只能飛很高的鳥兒。 他身上慢慢長出羽毛, 變成了一只秧雞。
賀蘭山下
開闊的北方平原, 植被稀疏, 棗樹林、 白楊林也只偶爾出現。地上淺草的葉子尖細而硬扎, 它們給自己過塑了一層保護外殼,用于抵擋從更北方不斷吹來的疾風, 免于失水過多, 免于凍死在極其寒冷的荒原。
在這塊平原的西面, 其實架有一道天然的屏障——賀蘭山。嶙峋的石塊崢嶸于山體之上。 這些山嶺沒有柔和起伏的輪廓線條, 反而像舊石器堆放處, 時光和恒久的疾風打磨出不計其數的石器, 堅硬鋒利。 那些破碎的石器散落在山巔、 山坡、 枯溝、 山道, 形成一片隱忍的寂靜。
一只灰色的巖羊受到汽車的驚擾, 小步跑過亂石間, 登上陡峭的山坡, 隨即走向更高處。 絕壁上, 幾只巖羊蠕動, 個個身形從容自在, 如履平地。
西夏風
天上飛著點點黑豆般的燕子, 它們突然俯沖, 幾乎貼地滑翔,又猛地上躥, 折身飛往一座渾黃的土丘。
大大小小的土丘都是古墳。 生前權力越大、 身份越顯貴的死者, 他的墳墓也就越發高大, 占地越廣。 這種奇怪的邏輯, 不過源于欲望的延伸。 在風的激烈刮擦下, 堪稱巍峨的墳墓喪失了銳氣, 原本的龐然禿了、 矮了, 逐漸縮成無限的小。 風剝走了墳墓上層層包裹的黃土, 順手也揚棄了墓中死者僅剩的威嚴與榮耀。
墳頂四周, 許多圓溜的黑洞, 像一個個射擊孔。 一只燕子鉆出洞口, 展翅, 縱身, 掠向別處。 墳墓已經是人鳥共享的場地。
這片陵園長好幾公里, 寬又有好幾公里。 古墳如零落的棋子,擱在原位, 博弈從來不會結束, 而棋手們已經不得不起身離場。
路過一座墳, 走了很遠, 才看見另一座。 一座墳與另一座墳的距離如此遙遠, 恰好對應了死者們生前的關系。
雪 山
雪山老了。 跟人相反, 雪山越老, 她的白發越少。 飄落的白發融化成清水, 帶著冷清的氣息歡快地流下山去, 流過魚塘、 果園、 青稞地、 菜園、 四合院。
也許只是眨眼間, 或者過了很多年, 雪山不剩一絲白發, 已經滿頭烏漆漆的。 沒了以前的終年積雪, 雪山不再叫原來的名字。當然, 獲得新的面貌后, 雪山自然成了另一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