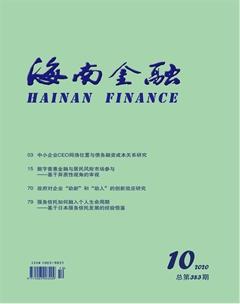數字服務稅的利益衡量與中國應對
郭媛媛

摘? ?要: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推動了國際稅收秩序的重構,部分國家陸續開征數字服務稅,意圖在數字經濟進程中把握優勢地位。本文基于利益衡量標準分別探討數字服務稅的合法性與“用戶價值創造”理念的合理性,分析OECD國家數字服務稅或類似稅收進展狀況和發展趨勢,并結合我國國情提出中國應對數字經濟稅制變革的前瞻性思考。建議我國在堅持稅收中性和稅收公平原則的基礎上,短期內暫緩征收數字服務稅,穩步推進中完善數字服務稅規則儲備方案,加強數字經濟國際稅收協作,以積極靈活的方式應對數字經濟帶來的稅收沖擊。
關鍵詞:數字服務稅;美國301調查;利益衡量;中國應對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20.10.006
中圖分類號:DF432.9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1003-9031(2020)09-0050-07
一、數字服務稅之緣起及利益動因
隨著數字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展以及各國為了爭奪國際話語權的現實需求,數字服務稅(Digital Service Tax,以下簡稱DST)如雨后春筍迅速席卷全球,早期在匈牙利、韓國和印度等國家予以實施。匈牙利于2014年開始征收廣告稅,并采用累進稅率,政府將其稱為“Google稅”。2017年和2018年調整后,現在每年對超過1億匈牙利福林(348,440美元)的廣告收入征收7.5%的稅。韓國于2014年采取數字稅收行動,并通過修訂增值稅(VAT),使數字服務的銷售范圍擴展至外國公司或個人提供的音頻、視頻、游戲和軟件。印度于2016年開始征收均衡稅。2018年3月,歐盟委員會提議對數字稅收采取兩步走的方式,其中臨時性的措施就是對用戶在價值創造中發揮主要作用的總收入征收3%的DST。基于現行的企業稅收規則適用于數字經濟企業會導致利潤征稅地和價值創造地之間的錯位,英國政府自2020年4月1日起將對從英國用戶獲得價值的搜索引擎、社交媒體服務和在線市場的收入征收2%的DST。2019年9月,法國議會已明確采用法國DST,并將自2019年1月1日起追溯適用,稅基包括納稅人為提供在線廣告、線上銷售和平臺傭金等業務獲得的全球總收入乘以在法國生產產品或提供應稅服務的比率,其固定稅率為3%。此外,澳大利亞、意大利、挪威和西班牙等國家也紛紛開始推行DST。
上述國家開征DST多是基于本國利益的立場,其利益動因具有深層次和多方面兩大特征。一是為了增加本國財政收入和緩解國內的財政壓力,彌補數字經濟時代由于稅基侵蝕嚴重導致的稅收漏洞。開征DST之前,法國的財政赤字已突破歐盟規定的3%的警戒線,在財政危機的壓力下迫使法國開辟新的稅源。而美國科技公司多利用歐盟部分國家的稅收洼地或采取“荷蘭三明治”等方式,將利潤轉移至低稅率國家從而實現避稅。虛擬化和無紙化的在線交易方式,為跨國數字企業不在創造數字經濟收入的國家設立常設機構創造了機會,但加劇了當地稅務機關依據現行稅收規則進行征管的難度。二是基于稅收公平和公眾福利的保障。DST最重要的依據之一就是“用戶價值創造”,數字經濟使消費者具備消費者和生產者的雙重身份,即產消合一。消費者在享受數字企業提供的服務的同時,也通過參與數字企業的消費活動為其創造了價值,但在目前的稅收制度下,數字企業創造的價值并沒有分配給消費者導致雙方處于不對等的收益狀態。以谷歌、臉書為代表的跨國互聯網企業在歐盟繳納的稅率平均值不到10%,遠低于歐盟中小企業的稅率,加劇當地企業和數字企業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更是突破了稅收橫向公平的基本原則。三是爭奪國際稅收話語權的利益動因。數字經濟規模的擴展推動全球開征DST的步伐,保護本國數字企業發展和加快國際稅收規則協調需要達成雙向平衡。各國所代表的利益群體的差異性導致國際稅收秩序依然發展遲緩,但數字經濟不可阻擋的全球化趨勢也必將推進國際稅收秩序的重構,部分國家率先實施DST并在全球范圍內推廣DST的理論核心和基本規則,為未來數字經濟國際稅收秩序的重構提供了方向和指引,以此爭奪國際稅收規則的主導權。
二、數據服務稅的利益制衡:合理性與合法性
(一)數據服務稅的合理性辨析:用戶價值創造
歐盟多次主張“用戶價值創造”系DST的核心理念,其將“用戶價值創造”解釋為立足于數字經濟時代,算法、用戶數據、銷售功能和知識的組合會產生價值,如用戶在社交媒體上分享自己的喜好就為價值創造做出了貢獻,這些數據以后會被使用并貨幣化,用于定向廣告投放,而創造的利潤卻并沒有在用戶所在國被征稅,也就意味著企業在征稅時不考慮用戶對利潤的貢獻。歐盟以此為依據針對“用戶創造價值”總收入在歐盟所占的比例來征收DST。此外,英國和法國引入DST時也將“用戶價值創造”作為依據,英國根據“用戶使用平臺軟件并持續投入時間為平臺企業創造超額利潤”來定義用戶價值創造。新西蘭DST提案中也指出數字企業提供的服務價值取決于用戶群的規模和積極貢獻。然而,“用戶價值創造”并沒有一個通用的全球標準,美國針對法國DST展開的“301調查”也指出,法國的DST歧視美國公司且與國際稅收政策的現行原則不一致,對于受影響的美國公司而言是非常沉重的稅收負擔,用戶在參與過程中創造的價值與用戶使用數字平臺所需要的支出相抵消。美國和歐洲國家對“用戶價值創造”存在分歧,表明這一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并不明確,將導致DST難以得到全球130多個國家的一致認可,加劇DST實施的不確定性。
本文認為“用戶價值創造”理論具備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不完善之處。一是關于數字企業和用戶之間的交易是否就必然涉及到價值創造,還有可能是雙方共贏的結果。英國將“用戶價值創造”界定為“用戶持續投入時間積極參與”,然而“消極和積極”的界定以及“持續投入時間的標準”是存在質疑的。二是僅關注“用戶價值創造”是不全面的,因為用戶的積極貢獻會產生網絡效應,即使用服務的人越多就越可能獲取額外的價值,這不僅僅在數字行業很明顯,在很多傳統行業也同樣適用。如早期通過傳真機發送信息,參與的用戶越多,傳真機就越有價值,電信網絡的運作方式亦是如此。三是用戶價值創造是否在用戶所在地、用戶參與的時間節點、產生的價值創造過程以及用戶價值創造的衡量標準,都是尚未解決的問題。
因此,在“用戶價值創造”的概念界定尚未達成全球共識的情況下,單方面提出該理論容易加劇各國之間的利益沖突,也給未來國際稅收秩序的構建留下了隱患和詬病,故亟需各國加強交流達成一致意見,才能使DST具有更完善的理論基礎。
(二)數字服務稅的合法性辨析:美國對法301調查為切入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于2019年12月2日發布了一份調查報告,該報告指出DST對美國商業造成負擔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1.DST對美國數字公司具有歧視性;2.追溯適用不符合現行的稅收原則;3.DST適用于與法國境內實際存在無關的收入,違反了現行的國際稅收原則;4.DST適用于小部分數字公司違反了針對數字經濟的國際稅收原則;5.DST僅針對營業總收入而不是實際收入征稅,不符合現行國際稅收管轄權規則。美國據此有權根據301條款采取適當的應對行動,在此基礎上對原產于法國的商品征收高達100%的關稅,估計進口價值約24億美元。美國針對法國展開的“301調查”是為了在國際稅收利益博弈過程中維護本國的稅基安全,防止DST打破美國作為數字經濟利益輸出國的優勢地位。
美國301調查引發筆者對DST合法性的質疑。根據法國DST的規定,其主要針對美國以谷歌、蘋果、臉書為代表的巨頭數字企業進行征稅,能夠達到法國DST課稅門檻的9個企業中有8個都是美國企業,法國提供數字服務的公司卻不受影響。然而據此不能完全認定法國具有歧視性。根據OECD范本規定的無差別條款,其判斷標準主要為國籍、常設機構、扣除無差別和資本無差別等。根據目前的國際稅收規則,由于美國數字企業在歐盟等主張DST的國家沒有設立常設機構,因此不適用協定中規定的“常設機構無差別和資本無差別條款”,而美國企業作為非居民企業,也難以主張國籍無差別,扣除無差別多適用特許權使用費而不是DST,所以美國主張的歧視性待遇是不成立的。
根據目前的國際稅收體系,各國在稅收條約中規定,只有當公司在該國管轄范圍內成為“常設機構”時,才應對該公司征稅。常設機構的概念一直是爭論的焦點。利潤來源國要求擴大常設機構的定義,而居民國要求縮小其定義,以常設機構是否包括重要有形財產為判斷標準。但目前學界普遍主張,以公司在管轄區內是否有永久性的實際存在作為常設機構的判斷標準。如一家在A國設有辦公室、工廠或車間的公司將對其在A國的部分收入交稅,而一家能夠在A國銷售貨物而沒有任何實際存在的公司則不需要交稅。然而目前以“數字存在”或“重要的經濟存在”來重新定義常設機構,即使公司在管轄區域內沒有實際存在。如以色列的重要經濟存在測試、斯洛伐克共和國將數字平臺納入固定營業地的范圍內,而印度的重要經濟存在測試也于2018年生效。美國最高法院在南達科塔州訴Wayfair案中承認,隨著技術和社會的迅速改變,經濟聯系日益加強,以公司在該州具有實際存在為標準來征收特定類型的稅款將不再有意義。據此,法國是否違反稅收協定中常設機構的規定是存在爭議的,盡管目前以永久實際存在作為認定常設機構的普遍標準,但因為其與數字經濟的特征相抵觸,DST所針對的數字企業一般在用戶所在國不構成常設機構,歐盟也主張DST屬于間接稅,因此稅收協定的內容不適用常設機構的規定。正是因為反對傳統認定常設機構概念的爭議一直存在,所以DST是否是直接稅還是間接稅,是否適用稅收協定將決定了DST的合法性。
三、數字服務稅發展的國際趨勢——以OECD國家為例
通過對數據進行統計,截至2020年3月,奧地利、法國、匈牙利、意大利、土耳其和英國已實施DST。捷克共和國,斯洛伐克和西班牙已經發布了實施DST的提案,拉脫維亞,挪威和斯洛文尼亞已經正式宣布或表示有意圖實施DST,而波蘭目前暫停了有關數字服務稅的工作。各國所提議和實施的DST在結構上存在差異。如奧地利和匈牙利只對在線廣告收入征稅,法國的稅基則更加廣泛,包括提供數字界面、定向廣告以及為廣告目的而收集的有關用戶數據的傳輸所產生的收入。稅率則從英國的2%到匈牙利和土耳其的7.5%不等(盡管匈牙利的稅率暫時降低到0%)(見表1)。
從表1可以看出,英國、奧地利、意大利和土耳其都已經開始實施DST,其余大部分國家選擇暫停征收DST或處于觀望狀態。各國征收的稅率普遍偏低,稅率最高的國家匈牙利也僅為7.5%,各國各自為政根據全球形勢來單邊開征DST,征稅對象、稅率、國內外稅收門檻也存在差異。美國和法國針對DST的不同態度加劇全球形勢的緊張,歐洲國家期待中國采取措施來應對數字經濟帶來的國際稅收秩序的變化。因此,立足于目前緊張的國際局勢以及數字經濟所帶來的巨額利潤,中國應及時拿出應對方案。
四、中國應對數字經濟稅制的前瞻性思考
(一)堅持稅收中性和稅收公平原則
數字技術的蓬勃發展成為經濟研究的熱點并納入各國的發展戰略之中,由數字經濟而引發的DST,也是新時期稅收利益輸入國與利益輸出國之間競爭的結果。美國一直處于數字經濟領域的核心位置,必然不允許其他國家分走數字稅收的奶酪,歐盟成員國國內針對DST也尚未達成一致意見,美國對法國的301調查法案也迫使法國暫停對DST的征收。2019年和2020年的中國政府工作報告中都提及數字經濟,在全球疫情之下,數字經濟的優勢地位愈加凸顯。在國內外目前的特殊環境下,中國是否推進征收DST,要堅持稅收中性和稅收公平的基本原則。一是數字技術的商業模式發展方興未艾,要促進以騰訊和阿里巴巴為代表的數字企業的發展潛力,要在核定合理的稅收利潤的基礎上開征DST,實現國家征稅權和企業發展之間的動態平衡,盡可能減少其稅收負擔增加稅收優惠等;二是堅持稅收公平的原則,數字企業與傳統企業創造的利潤以及各自的稅收負擔是不匹配的,提高對數字企業的稅收收入并降低傳統企業的稅收負擔,既可以實現稅收公平也可以保障國家的財政收入。
(二)減稅降費的形勢下短期內慎重開征數字服務稅
2019年國務院的《關于減稅降費工作情況的報告》提出深化增值稅改革,將基本稅率從16%降低至13%,實施小微企業普惠性減稅,并清理規范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受到疫情沖擊,全球經濟需要數字企業的發展來實現經濟復蘇,全面開征DST與減稅降費的大環境相悖,但這并不意味著DST沒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盡管目前歐洲部分國家開征的DST稅收門檻較高,尚未嚴重波及中國數字企業的稅收利潤,但長遠看來其針對數字企業大規模征稅是大勢所趨。既要考慮當前降稅降費的客觀環境以及促進數字企業迅速發展的客觀需求,中國暫時不建議全面開征DST,現在開征DST既不利于經濟復蘇也會加劇中美之間的緊張局面。基于應對國際形勢的需要,中國可以借鑒法國、英國和意大利的經驗,充分考慮未來歐盟可能采取的措施,將DST作為應對全球貿易摩擦的備選方案并完善其基本規則,加強頂層設計并將其納入我國未來稅制改革的整體框架,構建符合中國國情的數字服務稅體系。
(三)應對國際形勢構建數字服務稅儲備方案
隨著我國數字經濟不斷向全球擴展,《外商投資準入特別管理措施》等文件提出,未來我國將分階段開放數字服務領域的外國投資,包括通信和互聯網領域,國內的數字企業也必然會面臨更大的挑戰。我國在分析和研究國外DST經驗時,應加強頂層設計客觀分析數字利潤如何在企業、政府和用戶之間的合理劃分,構建我國DST規則作為應對國際稅收沖突的儲備方案。
一是重視DST的核心支柱——用戶價值創造理論。數字產品和服務的消費過程中會創造價值,在用戶所在地收集數據是穩定的,從而使得用戶數據與價值創造具備實質性關聯,而數字企業對其產生的數據進行整理分析進而不斷研發出新的產品和服務。重新定義用戶價值創造的概念,在判定數據客觀價值方面,建議將數據本身與企業對數據的再收集加工過程相分離,根據用戶對數據的貢獻率來確定利潤歸屬。對于該貢獻率的確定可以依據大數據平臺動態調整。在操作過程中,先計算出扣除企業常規利潤之后的剩余利潤,再對剩余利潤中用戶貢獻的那部分利潤分配給用戶所在地,當用戶所在地為集團組織時,由集團組織內部依據事先約定的比例來確定各自的征稅權范圍。
二是確定征稅范圍、征稅對象、稅基和稅率。在征稅范圍上,本文建議DST僅適用于有網絡效應的營業活動提供的數字服務,其價值取決于互聯網用戶規模及其積極貢獻。如用戶在社交平臺發帖、上傳照片、評論和創建組群等個性化的參與方式為數字企業做出積極貢獻。即使用戶沒有積極參與,但被定向投放廣告也應屬于DST的征稅范圍。征稅對象主要包括以下供應商:促進商品和服務銷售的中介平臺、社交媒體平臺、內容分享網站以及搜索引擎等。DST僅針對平臺所有者征稅而非用戶或廣告商,所以通過互聯網銷售普通商品或服務(廣告或數據除外)不在DST征稅范圍。提供在線內容,如音樂、游戲、電視節目和報紙等也被排除在外,其主要活動是向用戶提供信息,而不是將廣告主與用戶聯系起來。在適用門檻上,DST的全球收入門檻可以借鑒OECD國別報告要求中提到的7.5億歐元,該門檻設計對減輕中小企業合規負擔具有積極的效果,并結合我國國情來探索國內DST稅收門檻。對于稅基如何確定前文已經予以論述,針對稅率建議選擇多數國家通行的3%的稅率標準。對出現虧損或利潤率較低的企業可以借鑒英國經驗實施安全港規則,企業有權選擇簡易的計算方法納稅,但對于實踐過程中安全港規則是否能夠發揮減輕稅負的效果仍需考證。
(四)加強數字經濟國際稅收的協作
面對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在難以達成多邊共識的情況下,單邊措施DST被多數國家納入立法議程,意圖通過單邊措施盡快推進國際稅收秩序的重構,在數字經濟領域掌握優勢地位。此外,OECD和G20倡導的“雙支柱”方案也引起廣泛關注。我國作為數字經濟大國,既要積極參與經濟數字稅收秩序的制定,也要警惕可能對中國數字企業和消費者造成的潛在挑戰。一是完善國內稅收制度,立足我國國情和國際形勢控制DST的正負效應,并力圖減少其負面效果,構建DST規則儲備方案以防止對我國數字企業的沖擊,也可以在優勢領域開展DST試點先行,實現籌集財政收入與促進經濟發展的雙向平衡。同時探索建立數字經濟稅收征管體系,引入區塊鏈技術整合數字經濟共享機制,為未來推行DST完善相應的配套措施。二是要積極參與數字經濟時代國際稅收秩序的重構,針對雙支柱方案中的利潤分配和聯結點規則以及收入包含規則提出我國的應對方案;對如何完善常設機構,如何修改轉讓定價規則,如何劃分各自數字經濟利潤和管轄范圍,以及如何加強國際反避稅合作發出中國聲音,并積極影響OECD所提倡的BEPS項目的進展,以積極和靈活的方式來應對挑戰,在利益平衡之下實現國內和國際稅收的良性互動。
五、結語
疫情之下,全球經濟發展呈現斷崖式下跌,而數字經濟是全球經濟復蘇的重要驅動力。面對國際稅收利益的重新分配,合則兩利斗則俱傷。單邊主義的措施只會讓國際稅收秩序重構受阻,影響全球范圍內數字經濟的發展,對于亟需經濟復蘇的各國而言無一利好,各國在權衡其本國利益的同時也要關注整體利益。中國要把握機會積極應對,加強頂層設計以維護稅基安全和提高國際話語權,權衡國內外形勢短期內暫緩征收DST,穩步推進中完善DST的規則設計,為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謀得一方利益。
(責任編輯:王艷)
參考文獻:
[1]何明智,黃文鴻,高嬰勱.法國征收“數字稅”法案評議[J].科技中國,2020(4):27-28.
[2]黃健雄,崔軍.數字服務稅現狀與中國應對[J].稅務與經濟,2020(2):85-90.
[3]張智勇.數字服務稅:正當的課稅抑或服務貿易的壁壘[J].國際稅收,2020(4):28-35.
[4]管彤彤.數字服務稅:政策緣起、理論爭議與實踐差異[J].國際稅收,2019(11):58-63.
[5]盧藝.數字服務稅:理論、政策與分析[J].稅務研究,2019(6):72-77.
[6]李蕊,李水軍.數字經濟:中國稅收制度何以回應[J].稅務研究,2020(3):91-98.
[7]劉奇超,羅翔丹,劉思柯等.經濟數字化的稅收規則:理論發展、立法實踐與路徑前瞻[J].國際稅收,2018(4):35-42.
[8]高金平.數字經濟國際稅收規則與國內稅法之銜接問題思考[J].稅務研究,2019(11):70-76.
[9]廖益新,宮廷.英國數字服務稅:規則分析與制度反思[J].稅務研究,2019(5):7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