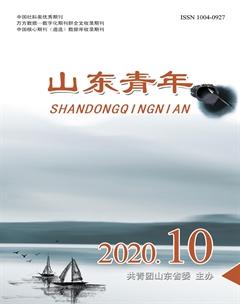蒙學教育當代價值的再思考
靳雨純
摘 要:中國古代蒙學教育,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在傳播和繼承儒家理念的過程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尤其是蒙學教育作為中國古代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擔起了教育兒童成長成才方面的重任。科學合理的兒童啟蒙教育,不僅能增長知識,促進德性,而且有利于兒童“存其心”,“宣其志”。
關鍵詞:蒙學教育;兒童;當代啟蒙教育
一、蒙學教育的概念及歷史梳理
(一)“蒙學”一詞之由來
蒙學,又稱為蒙養之學,是古代教育中的一個階段,與現代啟蒙教育相對應。《周易本義》中曾記載:“童蒙,幼稚而蒙昧。”這一物象非常形象的比喻了童蒙的狀態。[1]童蒙是指初入學的兒童,古代教育家們都崇尚“蒙養之始,以德育為先”的傳統蒙學教育。主張在兒童性情未定之時,以“做人”教育為基礎,立志、成才教育為主線,引導兒童沿著正確方向,健康成長。
蒙學教育是指我國古代教育家借助蒙學輔助教材,運用古代教育方式對兒童進行的啟蒙教育。[2]第一,主要包括基礎文化知識、修心養性、道德倫理等內容。第二,教育體制上既包括官方的學堂教育,也包括了民間家庭式私塾教育。第三,其教學內容、教育方法和教育家的教育理念也呈現出了獨特的色彩。目前,我國學者對蒙學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個時期,包括了早期蒙學、古代蒙學、近現代蒙學,蒙學教育逐漸演變為獨立的自成體系的綜合教育。
(二)早期蒙學教育
(1)西周蒙學
夏商兩代,蒙學讀本無史料可以考證,到殷、周時期才有記載。一直到原始社會末期,學界尚未形成系統的教材和成熟的教學方法。一直到西周時期,才出現了以讀書識字為主要功能的官辦小學,此時的學校才具有完備的制度。我國出現的第一本識字教材就是西周的《史籀篇》,它是史上記載最早的兒童識字課本,課本內容主要是姓氏名物的堆積,而其后出現的《倉頡篇》、《愛歷篇》、《博學篇》皆是對《史籀篇》的發展。
(2)春秋戰國時期蒙學
“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百家爭鳴”促進了私學的發展,除了官方教育機構外,民間也出現了專門的啟蒙教育機構,他們成為了普通百姓完成蒙學教育的重要場所。
(3)秦朝蒙學
秦始皇統一六國,為鞏固皇權,秦始皇實行文化專制主義,控制言論,在教育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廢除官學、私學的同時重新制定了學書內容,并且下令李斯等人合力編撰了《倉頡》、《愛歷》、《博學》三本書。
(4)漢代蒙學
到了漢代,書館、書師相繼出現,學子的數量也顯著增多。漢代對秦的學書進行了修正改編,由原先的三本合為《倉頡篇》一本,流傳于后世。由此可見,漢代對蒙學教育的重視程度。
隨后的東漢和南北朝社會動蕩,但同時給學術文化創造了良好的發展機會,形成了文化大融合的局面。
(三)蒙學教育的發展與繁榮
(1)隋唐蒙學
隋唐不僅僅是歷史上難得一見的盛世之時,也是蒙學教育的定型期。隨著儒家思想的進一步影響,以及科舉考試的推行,蒙學教育逐步完成了從早期讀書識字的功能向以學習知識為核心內容的轉變。例如,有史料記載,京師州縣創辦了官方小學,地方民間的鄉學、鄉塾也紛紛涌現。唐朝對教育事業的扶持也為后世宋元明清蒙學教育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這一時期的蒙學教育方法仍舊是以識字教學為主,但是從形式和內容上來看,隋唐的蒙學教育也有所突破,最為明顯的突破體現在蒙學讀物上,例如,識字類課本和知識類教材徹底分離,倫理類教材和歷史類讀物獨立發展。
(2)宋代蒙學
宋朝初期統治者結束了五代十國的混亂局面,實現了疆土上的局部統一。宋太祖趙匡胤在“杯酒釋兵權”的同時吸取經驗教訓,轉變統治策略,由原來的重“武”改為重“文”,開始試行從中央到地方由文官主政的政治格局,更是明確提出“宰相須用讀書人”。[3]宋代社會迅速從戰爭的創傷中恢復過來,形成了“學校之設遍天下,而海內文治彬彬”的局面,蒙學教育由此獲得了空前的繁榮發展。
由于統治者的重視,宋代的學術著作以及文化的傳承相對比較自由化。宋代蒙學教材繼承和超越了前人編寫教材的經驗,開始按照內容進行分類,按照專題編寫課本。
(3)元明清時期蒙學思想
縱觀蒙學教育的發展歷史,元朝在其中起到了過渡作用,元朝蒙學教育內容、方式和蒙學教材大多沿襲了前代,其中混雜了元代特有的崇尚經書的特點,其主要是完成了將宋代蒙學的教育機制向明清程朱理學轉化的歷史重任。
中國古代的蒙學教育在明代真正達到鼎盛。明代蒙學在辦學體制上,采取了官學和私學并舉的方式,蒙學教育也被大致概括為識字階段和讀經階段。
總之,第一,回顧古代蒙學的發展歷程,不難看出,我國蒙學教育的出現可以追溯至殷、周時期,秦漢以后,受到政治和經濟的影響,蒙學的地位逐步提高,體制不斷的完善。第二,蒙學教育大多是在私學中出現,官辦學校一般不包含蒙學教育。第三,蒙學的發展與其他事物一樣,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隨著歷朝教育實踐的深入,蒙學教育逐漸趨于成熟。當代教育改革路徑也需要遵循事物存在與發展的客觀規律,研究更多具有建設性意義的構想與方案。
二、蒙學教育的倫理教育功能
(一)不學禮,無以立
誠實信用歷來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也是中華禮儀的象征,更是中華文明的代言詞。《增廣賢文》以“許人一物,千金不移”來倡導人要以誠為貴,將“誠”作為人際交往的行為規范。[4]誠信是安身立命之根本,更是高尚道德情操的展現。要想具備誠信的品格,我們必須從小做起,讓兒童在日常生活中體會到誠信帶給我們的無限魅力。[5]
(二)明人倫,重孝悌
父母為慈,子女為孝。首先,在傳統蒙學經典《三字經》中就曾提出:“首孝悌,次見聞”,這是指人生首要學會的道理是孝敬父母和友愛兄弟,只有做好了這些,接下來才是學習所見所聞。[6]其次,在兄弟關系中,強調兄弟友愛、和睦相處,這是古代強烈的家庭認同感的體現,也是為了維護家庭同居共財制度要求。這些都是人倫、孝悌行為準則和觀念的體現。
(三)泛愛眾,而親仁
《弟子規》“泛愛眾而親仁”篇章中就提到“凡是人,皆須愛,天同覆,地同載”,這些都體現出以人為本的仁愛精神。仁愛精神是一種博大的仁愛之心,要求我們對世間萬物都充滿情感,要求我們在社會交往中以博愛的胸襟去待人處事,當時的傳統蒙學教材更是很好的繼承了這種思想,將“仁愛”精神貫穿于蒙學教育的始終,這也側面展現出了當時教育家們對蒙童教育的重視,也是告誡蒙童從小就要在心中扎下愛人之根基。
(四)頭懸梁,錐刺股
勤奮刻苦是中國人的民族特性,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留給后世的寶貴精神。在《三字經》中最具體的表現就是“頭懸梁,錐刺股”,它生動地反映出當時的學生雖家境貧寒,但卻沒有一刻停止發奮苦讀。這也與當代學生學習的狀態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在當前的學習環境、教學條件下,當代學生更應該不斷刻苦鉆研,完善自身。這樣才不會辜負時代所賦予的期待。
三、反思當代啟蒙教育失衡現狀
(一)傳統語詞的流失
在古代,人們咬文嚼字,字字斟酌,因為古代文學家、教育家將語詞視為神圣的,因此他們追求準確和精煉。而現代社會中,詞語漸漸成為人們心中簡單的交流工具,直接扼殺了語詞曾經深刻的內涵。特別是一些專業語詞僅有少數人掌握,傳授范圍受到了限制,文化傳播也成為了死循環。
(二)道德教育的滯后
在古代蒙學教育中,道德教育與知識教育始終平起平坐,培養高能人才的同時,道德教育更是不可缺失的。也就是說,在古人看來,德行是人的本分,是首要的;而學習雖重要,但處于道德之末,學習的順序應該是窮其本末,而知所先后。也就是說,沒有做到先修養德行再學習,就會分不清善惡。而現代蒙學教育恰巧忽視了這一點,他們將教育重點全部放在知識的學習之上,使得接受教育的人卻喪失了良善之心。
(三)教育意義的偏離
值得我們關注的是,當代兒童教育在更多方面發生了偏離。比如說,如何讓孩子在學前階段爭取未來成績趕超其他兒童?所有的教育都與成績掛鉤,其他與學習無關的內容全都不足為重,仁、義、禮、智、信都被輕視甚至被割除,學習成績成為了唯一的評價標準,也成為了家長和學生的自覺追求。試問,如果這種模式成為社會的常態,那么培養起來的學生對于國家和他人又有何意義呢?
四、當代啟蒙教育應從古代蒙學汲取智慧
要想將古代蒙學思想與當代教育完美結合,家長可以在兒童幼年階段就開始傳統文化的學習,在日常生活中,逐漸將蒙學精神深入兒童心中,讓其在學習生活中餞行蒙學思想與規范。
(一)構建現代蒙學理念
中國傳統蒙學仍然具有局限性,蒙學教育與其他傳統文化一樣,要想在現代教育中站住腳跟,必須與時俱進。因此,在構建現代蒙學理念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對傳統蒙學的精華與糟粕進行辨別和提煉。
比如說,我們要防止“倫理中心主義”,在傳統蒙學的內容上進行取舍。例如傳統蒙學教材中的三綱五常、尊卑有序等內容應該進行適當的改造,結合時代的特征,將現代理性和平等民主的精神滲透到傳統蒙學內容之中,構建具有新時期特色的蒙學體系。
(二)推動蒙學課程開展
現代家庭和學校對孩子的啟蒙教育往往是從《弟子規》開始的,并且社會上出現了專門教師解讀《弟子規》的現象,這也有助于兒童深刻理解內容,與此同時,《弟子規》的學習,可以幫助學生養成獨立思考的能力。因此,一方面,有條件的學校可以增設蒙學課程,比如說,《弟子規》、《三字經》、《小學》、《蒙求》等等,這些在中國歷史上對于兒童有重大影響的經典蒙學讀物。另一方面,在沒有條件的情況下,我們可以讓兒童接觸這些蒙學教材,廣泛涉獵這一領域的知識,將精讀和泛讀結合起來。
(三)加強蒙學教師隊伍建設
古代蒙學教育的傳播者大多是窮秀才,與現代教育中的教師不同,他們大多沒有接受過完整的蒙學教育,系統的蒙學知識、總體修養并不高。現階段,我國許多學校并未開設蒙學教育的內容,只是在少數啟蒙教育的德育課程里面存在。專門從事啟蒙教育的教師更是寥寥無幾,因此,要想構建現代蒙學理念,加強蒙學師資隊伍的專業化建設更是當務之急。
[參考文獻]
[1]陳亮:《淺析蒙學教育的歷史沿革》,載于佳木斯職業學院學報,2015年第5期.
[2]李影:《古代蒙學教育與當代學前教育之我見》,載于佳木斯職業學院學報,2016年.
[3]萬超:《古代教育中宋代蒙學教育發展的特點和原因探究》,載于《教育現代化》2016年第21期.
[4]趙宏欣:《傳統蒙學的教育理念——以《三字經》《千字文》《增廣賢文》為例》,載于商丘職業技術學院學報.
[5]馮文全:《論蒙學教育對兒童發展的當代價值》,載于牡丹江大學學報,2016年第11期.
[6]酈波:《論中國古代蒙學讀本的“蒙訓”意義》,載于《南京社會科學》,2015年.
(作者單位:湖南師范大學,湖南 長沙? 4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