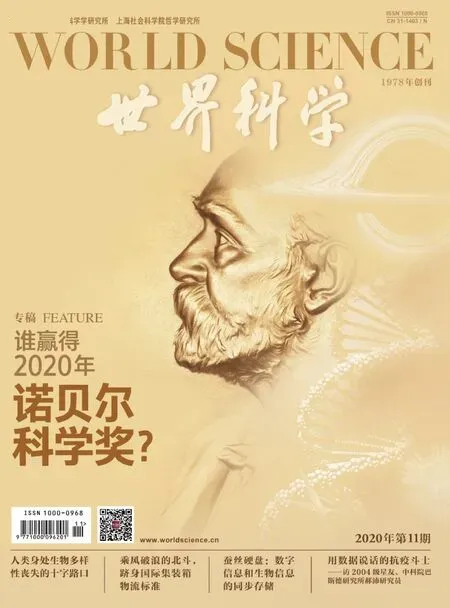朊病毒研究的前世今生

羊瘙癢病是羊群中的高度傳染性疾病,由神經毒性朊蛋白聚集而致 ①
范式轉移是科學進步的推動力,這一推動力未必在最初就獲得交口稱贊,而往往要歷經輕蔑目光。這正是斯坦利·布魯希納(Stanley Prusiner)發表于1982年的論文的寫照。他在文章中提出:羊瘙癢病是一種感染羊中樞神經系統的退行性疾病,其病因是一種“蛋白質類的傳染性物質”,稱為朊病毒(prion)。同行們回報以私下的竊笑。但布魯希納因其敏銳的洞察力獲得了1997年的諾貝爾獎,并啟發我們如何審視各種看似無關的疾病和生理過程,其深遠影響至今可循。
在布魯希納發表這篇文章前的20年中,分子生物學領域取得了長足進展:科學家攻克了基因密碼;闡明了DNA復制、轉錄和翻譯的機制;實現了基因克隆的技術。這些發現為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構建“中心法則”奠定了基礎,該法則認為信息流只能單向地從DNA流向蛋白質。不像宗教法則可能永恒不變,科學法則是無法避免其有效期的。布魯希納假設了朊病毒能夠在沒有核酸參與的情況下實現其復制周期。這一假說讓人想到約翰·格里菲斯(John Griffith)在1967年提出的觀點——具有自我復制能力的蛋白質可能存在,并能夠解釋羊瘙癢病的傳播介質對破壞DNA的射線具有抵抗力的古怪現象。
丹尼爾·蓋杜謝克(Daniel Carleton Gajdusek)證明庫魯病是通過巴布亞新幾內亞人同類相食的行為傳播的,并因此獲得諾貝爾獎。他在1959年提出神經退行性疾病如庫魯病、羊瘙癢病和克雅氏病(CJD)都是由“慢發病毒”導致的。而朊病毒確實在很多方面與嗜神經病毒驚人的一致,像是定植于神經系統外的器官后通過外周神經侵入腦。但布魯希納提純了這一介質后發現它比病毒要小得多,以至于不可能存在攜帶足夠信息的核酸與之對應。通過不斷研究,人們發現朊病毒疾病有很多種類,包括人類疾病(如致死性家族失眠癥)和動物疾病(牛海綿狀腦病,亦稱作瘋牛病或慢性消耗性疾病),但并沒鑒定出致病性的病毒,而朊病毒作為發病機制的理論已被廣泛接受。
朊病毒實際上與克里克的中心法則并非完全矛盾。查爾斯·魏斯曼(Charles Weissmann)不相信蛋白質能夠脫離對應基因而存在,他通過研究在倉鼠中發現了細胞朊蛋白(PrPC)的基因,PrPC的錯誤折疊將導致緊密聚集物PrPSc的產生。普遍認為在聚合的PrPSc分裂為更小的形式時,朊病毒便會復制。這一更小的形式會進一步滋生出更多PrPSC,這一過程類似晶體的生長,并最終再次分裂,如此將復制周期進行下去。傳染性朊病毒的“火種”如果進一步播散到周圍的細胞,就會在中樞神經系統造成巨大破壞,導致神經元空泡(海綿樣變性) 形成。
這是否意味著PrPSc就是朊病毒呢?魏斯曼在1993年發現敲除朊蛋白(Prnp)基因的小鼠不會得瘙癢病,這沒能駁倒僅有蛋白質參與的假說。當然,Prnp基因敲除的小鼠也不足以證明朊病毒存在的假說。如果PrPC是“瘙癢病病毒”假想中的受體,那么敲除它就意味著小鼠會對瘙癢病不易感。2001年克勞迪奧·索圖(Claudio Soto)發表了里程碑式的結果,為布魯希納的設想提供了更直接的證據:PrPSc聚集物在經歷反復的碎片化并不斷加入PrPC后,會發生聚集和再生,就能夠任意地產生朊病毒。這些發現為結構信息可以水平地在蛋白質間傳遞的假說提供了更多證據。
這段時間,朊病毒的概念有時被過度寬泛地應用,用以描述任何中樞神經系統中蛋白質不斷沉積的疾病,而沒有考慮傳染性是否存在——甚至應用在記憶形成的生理過程中。α-突觸核蛋白聚集物能夠在帕金森病患者的腦、培養的細胞以及小鼠中自我增殖,這是否就意味著α-突觸核蛋白是一種真正的朊病毒,并需要高等級的生物安全標準來進行實驗呢?類似的觀點還有關于β-淀粉樣蛋白(Aβ)聚集物——阿爾茨海默病的特征性生物學標志物。但是朊病毒能夠引起流行病,而沒有證據證明其他蛋白質聚集物也能夠引起流行——尤其是通過口口傳播的途徑。對于未被證實能夠連續在多代宿主間傳播的蛋白質聚集物,更好的描述是“類朊病毒”,即使它們在體外實驗中同真正的朊病毒在增殖上有相同的分子機制。
正如布魯希納在他文章結尾做出的論斷所述,“朊病毒革命”將會為阿爾茨海默病、帕金森病和許多以蛋白質聚集為特征的神經退行性疾病提供一種合理的理論框架,拓展了神經退行性疾病的研究領域。盡管現在已經發現細胞中PrPC對維持外周髓鞘的生理功能至關重要,我們對朊病毒的理解還是停滯了十多年,而落后于類朊病毒的研究水平。那么在布魯希納發現朊病毒后的40年中,我們究竟知道了哪些真相呢?
朊病毒研究的一個主要障礙是缺乏對PrPSc結構高清晰度解析的手段,其非溶解性、非晶體性聚集狀態都為此增加了難度,同時通過重組蛋白從頭合成高純度的具有感染性的朊病毒更是難上加難。這提示真正具有感染性的聚集物可能是少見的一種結構異構體。如果這樣,多數體外合成得到的就不會具有感染性,對解析朊病毒及其復制機制而言毫無價值。
縱觀現今朊病毒的理論模型,最可靠的假說認為朊病毒由一種纖維組成,這種纖維形似四階的b-螺線管,通過頭對頭或頭對尾的方式聚集在一起。通過冷凍電鏡分析純化的非糖基磷脂酰肌醇(GPI)錨定的朊病毒纖維的結果支持這一假說,這也是人類首次獲得感染性朊病毒的高倍率圖像,盡管圖像的分辨率不足以判斷纖維中單體的精確排列方式。這一結構與tau蛋白、α-突觸核蛋白和Aβ都有顯著的差別,也和重組的PrP纖維有差異,很大的不同在于這一結構不是由長纖維組成的,而是形成空腔結構的。因此,PrPSc具有其獨特的結構特征,但不明確其駭人的傳染性是否與之有關。
PrP聚集物同其神經毒性間的關聯尚不明確。大量的證據暗示PrPC是毒性的必要因素,或許由于細胞外PrPSc寡聚體能夠錨定多種細胞表面的PrPC。另一個朊病毒感染的特異之處在于其對腦傷害的特異形態學特征。在所有具有聚集傾向的蛋白質中,朊病毒是唯一能夠造成廣泛神經元內空泡(海綿樣變性)形成的,嚴重程度隨著疾病進展而加重。這一神秘的現象引起了科學家的注意。至今,我們對空泡形成的細胞和分子病理學機制幾乎一無所知,但由于這一現象出現在所有已知的朊病毒疾病中,可以推斷其可能是朊病毒毒性的一個關鍵因素——因此也就會是治療干預的一個靶向目標。
朊病毒的高分辨率三維結構解析對解決長期以來關于朊病毒毒株的問題也至關重要,這些朊病毒可能具有相同的PrP序列卻導致不同的疾病(如傳染性水貂腦病中“亢奮”和“嗜睡”的不同表型),且這些特征能夠在連續的傳染中維持不變。病毒毒株被定義為基因組的多態性,朊病毒毒株的存在長期以來被認為是其具有核酸的無可爭辯的證據。然而在超過40年的努力后,我們沒有分離得到任何瘙癢病特定的基因組,毒株也就被解釋為不同的PrPSc構象所導致的結果,而這些構象能夠通過構象敏感的熒光聚噻吩所鑒別。
朊病毒研究領域的窘境在于,至今還沒有決定性的結構證據能夠支持以上的假說,而真正具有傳染性的朊病毒“毒株”仍是由不完美的替代性生物學標志物——比如對解聚和蛋白酶解的抵抗力——所鑒別。與之相反,一些類朊病毒疾病在不同臨床表型中對應的結構異質性已被發現,盡管不同的構型在連續傳染實驗中的穩定性模型仍沒有完全建立。
那么朊病毒毒株在代代傳染中的穩定性又如何呢?RNA病毒通過形成準種來獲得最佳的適應性,許多變種處在適應性突變和錯誤后滅絕間的不穩平衡中。值得注意的是,朊病毒也能夠在人為給予不同的選擇壓力下產生準種,其單株成分能夠從培養的細胞中分離出來。這一現象的結構機制不明,也可能涉及不同PrPSc種類的構象選擇。構象選擇模型意味著單個受感染的機體中共存多種構象異構體,其中一些在特定環境中會有更高的增殖效率。不同毒株朊病毒的培養時間有巨大的差異,朊病毒發病前的潛伏期長度可能就反映了這一選擇發生所需的時間。
PrPSc異構體的特異性中或許潛藏著控制朊病毒種間傳播的障礙,朊病毒的傳播強度多變,與宿主及朊病毒毒株密切相關。朊病毒從牛到人的傳播導致了各類CJD,但羊朊病毒多數對人無害。這一種間屏障的形成歸功于接種物中PrPSc的結構差異性,以及宿主的PrPC差異,PrPC并不總會與錯誤折疊的異構體高效率地交互。
這一由布魯希納發展的概念經歷了巨大的變化。現如今,蛋白質聚集物的模塊樣聚集被認為不僅僅是疾病的基礎,也與許多生理過程息息相關,盡管可能與當初引起布魯希納興趣的現象毫無相似之處。我們已經建立了一些類朊病毒疾病的結構預測模型,但卻拿朊病毒毫無辦法。一些1982年由布魯希納提出的問題——朊病毒結構、復制機制以及毒力因素——仍是未解之謎。基于史實,我們可以認為:朊病毒研究領域的研究成果將會為更廣泛的神經退行性疾病提供全新的思路。
資料來源 Sc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