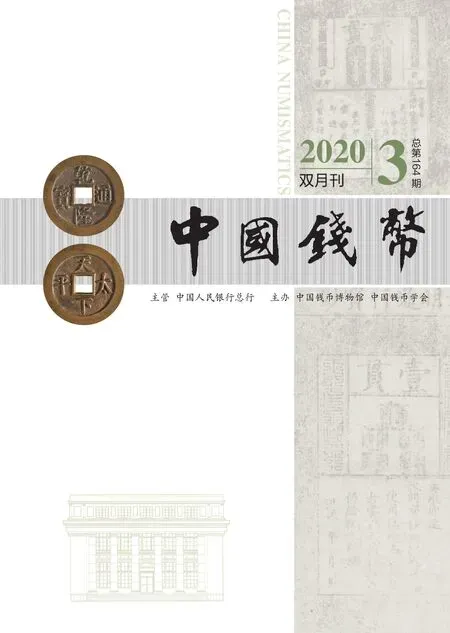宋明時期東南亞海域國家的貨幣演變
——以中國錢為中心
一 引言
眾所周知,中國的貨幣制度很早就對東南亞地區產生了相當程度的影響,宋代以降這種影響尤為深刻。中國錢的興與廢,始終影響著東南亞海域的貨幣演變。由于宋代銅錢的大量鑄造和外流,東南亞海域諸多國家相繼開始行用中國銅錢,小額銅錢在日本、爪哇等國深入民間日常交易,東南亞海域開始進入“銅錢時代”(或云“宋錢時代”)。宋元交替后,以白銀為基準的紙鈔在中國興盛,歐亞大陸的貨幣上層多流通白銀,抑或以白銀作為記賬單位,然而元明等朝銅錢的鑄造實在稀少,國內與國外銅錢同時發生“斷流”。雖然中國錢依然在流出,但流出數量大大減少,東南亞諸國不約而同地出現中國錢不足的問題。為了緩解壓力,日本、爪哇、越南等地開始仿鑄中國錢;與此同時,明代中國在大明寶鈔日漸崩壞的背景下,私錢日趨泛濫,白銀穩步崛起,基層社會出現“行錢之地”與“不行錢之地”的區別,多種地方貨幣及實物貨幣并行流通。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與地區,同時出現了銅錢質量變壞、價值分層等現象,各國趨同性地轉向私錢或仿鑄錢時期。16 至18 世紀,在全球白銀時代日益席卷的大潮之下,受中國錢影響的各種地方貨幣依然未曾絕跡。這種以中國錢為中心輻射東南亞的貨幣現象,揭示了近代早期中國對東南亞海域國家的影響,也反映出潛藏在貨幣流通背后各地逐步衍生出自律性的貨幣行用機制。
筆者最近在閱讀黑田明伸、萬志英等基礎性研究之上,結合相關資料,試圖對這一問題進行概述和歸納。需要說明的是,本文乃是一篇讀書札記式的心得體會,不足處祈請方家指正。
二 “白銀時代”與“銅錢時代”交織下的東南亞海域貨幣
13 世紀前后,由歐亞大陸“白銀世紀”與東亞海上貿易所構筑的“銅錢時代”,均見證了當時中國的貨幣制度對周邊世界的影響。各個地區也正因為中國貨幣制度的演變及其影響,邁向了各有差異的貨幣演化之路,這對于亞歐大陸的兩端地區而言更顯如此。
在遠途貿易中,不同地區間的貿易共同推動了跨地域貨幣的發展演進,各個貿易地區通過某種貨幣連接成一個又一個不同的循環回路,這個貿易環路反過來繼續鞏固著該種貨幣的主導地位,如瑪麗亞·特麗薩銀幣、蒙元時代的白銀貨幣、南亞圈內部的貝幣、東南亞海域的中國錢等。這種各地域間約定俗成的貨幣不依靠任何法定權威,甚至可能在一國鑄造卻在另外一國流通,僅依賴于貿易雙方的選擇成立,但當貨幣匱乏難以繼續供給時,貿易環路自行崩潰,并以該種貨幣為基礎,不斷繁生演化直到下一個循環回路形成。正如黑田明伸指出的那樣,當循環回路中一個正式的大型貨幣制度崩潰時,各地區內由于基準通貨大為減少,不得不自行組織交易,各地開始形成更為基礎的貨幣制度或者說非正式的貨幣習俗,這一點在東南亞、在中國都體現得淋漓盡致[1]。13 世紀以后,歐亞大陸“白銀世紀”與東南亞海域“銅錢時代”所形成的貨幣循環回路及其崩塌所造成的貨幣制度演化,足可表明此點。
北宋巨額鑄造量的銅錢不僅流通于中國境內,也隨著海洋貿易流通于日本、越南、爪哇、馬六甲等地區。由于中國的布帛、瓷器等產品深受東南亞諸國的喜愛,如何與中國商人貿易就成為了各國的重點。同時,馬六甲的香料、爪哇的胡椒也是中國商人首要貿易產品之一。隨著中國商人不斷出海,大量宋代銅錢隨著商品流通反向滲透于東南亞諸國。早在9 世紀,爪哇作為東南亞人口密集、農業發達的島國,已經在交易中對日常小額貨幣存在強烈的需求,隨著中國錢這種小額通貨的涌入,快速取代了原有的貨幣,成為爪哇最主要的交易貨幣[2]。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琉球和日本。中國江南及福建等地的銅錢率先流入琉球,然后隨著貿易深入流入日本諸領地,早期的琉球是中國與日本的連接樞紐[3]。關于越南有關資料表明至遲在13 世紀早期,中國銅錢已經充斥在越南諸多地區的市場交易中。隨著大量銅錢的外流,宋廷不斷出臺禁令禁止商人攜帶銅錢出海交換胡椒、香料等商品,雖仍無法阻止受利益驅使的商人鋌而走險,但銅錢外流的速度已經大打折扣。隨后的南宋、元、明等朝代由于銅礦不足、紙鈔興起等原因,急速縮減甚至是暫停了對于銅錢的鑄造發行,導致東南亞原來使用銅錢諸國遭遇了不同程度的貨幣短缺危機。環東南亞海域的中國錢流通圈面臨崩塌局面,各個國家遂以銅錢為基礎逐步衍生出各自自律的貨幣行用機制。與此同時,明代前葉,由于完全名目空心化的寶鈔走向徹底的式微,中國第一個“紙鈔時代”徹底畫上句點[4]。紙鈔崩潰、銅錢匱乏,導致明朝上下遭遇了與東南亞海域諸國同樣的困境。整個東南亞包括中國在內,由于宋代所維持的銅錢體系的崩潰,集體演進、分化形成各自的地方貨幣圈[5],并出現了與歐洲完全不同的貨幣現象—即由于貨幣短缺所造成的價值儲藏職能與支付手段職能的分離,形成了兩種功能不同的貨幣流通現象:標準錢與通用錢[6]。
我們調轉目光再度審視蒙元時代的中國可知,元代以銀為本位發行國內流通的中統鈔,大量閑置并被強行收繳的鈔本銀、稅銀使得蒙元朝廷有更寬裕的財力進行對外貿易。雖然沒有很多直接的證據表明歐亞大陸通過白銀形成了一個大型的貿易循環回路,但通過蒙元政權先期有大量白銀流向中西亞地區,與該地白銀供給突然充裕,以及帝國紙鈔崩潰、白銀流入下層交易的時間與英格蘭、埃及等地白銀突然短缺的時間點如此相近,以及歐亞貿易路線都可通過各自的單位與蒙元的50 兩銀錠單位建立聯系都證明,存在一個以白銀為主要貨幣的歐亞貿易通路。然而,銀錠作為大額貴金屬僅限于上層流通,與白銀一同進入流通渠道的,還有小額銅錢[7]。在蒙元帝國崩潰以后,白銀在中國從上層交易中進入底層交易,貿易通路由于白銀短缺而崩潰,第一個白銀世紀崩潰所造成的影響并不太大,可能的原因在于,白銀主要用于大額貿易,不影響民間小額交易。而與白銀一同流向歐亞大陸的銅錢、貝幣等,則成為整個環路崩潰后各個國家首選的貨幣,整個東南亞世界逐步進入小額通貨為主的時代。
早期的“白銀時代”與“銅錢時代”,分別以白銀與銅錢構筑了不同的貨幣貿易圈與貿易循環通路。當貨幣供給不足時,整個貿易環路會因為貨幣短缺而遭遇危機,乃至消亡。在歐亞大陸第一個白銀世紀,由于白銀處于交易的最上層,因此當其崩潰時,尚未引起各國劇烈的反應。反觀由宋錢為基礎的東南亞銅錢時代,銅錢的交易層級日益深入民間基層,在宋代銅錢供給中斷時,卻引起包括中國在內的東南亞海域諸國劇烈的“震蕩”。一場以中國錢為中心,長達數個世紀的基礎性貨幣演變現象在各國紛紛上演。
三 東南亞貿易國的貨幣演變
首先是爪哇,從11 世紀宋錢流入開始,中國銅錢已經成為了爪哇日常生活的必需品。隨著宋代禁止銅錢外流的法令頒布,爪哇遭遇了嚴重的銅錢危機,仿鑄成為解決危機的有力手段。在爪哇流通的中國宋錢到14 世紀以后,基本不再是中國的官鑄銅錢而是仿錢。爪哇所用的銅錢多數都是將原有銅錢熔鑄后,加入錫、鐵、鉛等材料制成,在爪哇稱為鉛幣(picis)。這種鉛錫仿錢逐漸充斥了爪哇市場,且主要是由中國商人在爪哇本土熔鑄或福建沿海等地制成。1530 年左右由于胡椒的出口需求上升,荷蘭當局甚至鼓勵中國商人購買鉛等材料仿錢,以方便胡椒的交易。胡椒等產品為季節性產物,導致與之對應的仿錢也存在季節性需求,仿錢正是爪哇解決季節性需求的最佳手段。葡萄牙人和東印度公司先后在1500 年和1600 年左右抵達爪哇,企圖使用白銀購買胡椒的舉措全部失敗,不得不將白銀兌換為小額鉛錢購買胡椒。直到1650 年,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使用武力才順利發行自己鑄造的銀幣。此時,仿錢仍舊用于爪哇當地多種產品的購買,直到18 世紀初期,聯合東印度公司才將荷蘭制造的大量銅幣投放入爪哇市場。各種來自中國的仿錢受到了巨大的沖擊,進入中國商人開設的公司內部、種植園內部,形成了一種與外部隔絕的社區貨幣[8]。
其次,越南也遭遇同樣的經歷。中國錢也曾在越南流通,日常交易都使用小額銅錢,如同爪哇一樣,越南所用的銅錢后來也多是仿宋錢,甚至還包含有日本仿錢與中國福建、廣東等地仿錢。有資料顯示,其受日本流通而來的仿錢影響較多,當1636 年日本斷絕了銅錢供給后,越南自行鑄造劣質的仿錢。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在18 世紀越南鑄造的銅錢甚至反向流入中國。由于宋錢匱乏,越南甚至出現了和中國一樣的短陌現象,何平認為,短陌是官方銅錢不能充分供給,難以形成統一貨幣流通的情形下,以私鑄地方銅錢的自組織化方式彌補官方銅錢不足從而形成多元化的銅錢體系[9],反過來說,短陌的存在證明了越南并存多種銅錢,并在宋錢的短缺下,構成了以私錢為主的貨幣體系。
最后,日本等地也深受中國錢的影響,早在12 世紀日本所用的日常交易貨幣,全部來自中國。當中國官方銅錢供給不足時日本的支付體系出現了劇烈波動。隨著福建私錢的涌入,日本銅錢的價值變得不再穩定,撰錢現象頻繁在民間出現,好錢與壞錢之間出現了嚴重的差別。在Itsukushima Shrine 和Sassi 兩個地區的爭執中,折射出兩種不同價值的銅錢所出現的內在矛盾,日本出現了標準錢與通用錢的分別,儲藏價值和支付手段職能相分離,同時在其境內,也出現了標準錢與通用錢的價值比率,不同地區的標準錢和通用錢不一定相同[10]。隨著好錢的短缺,日本各地區通過自行鑄造仿錢緩解通貨緊縮的壓力,由于各地區居民對不同私錢的選擇偏好,使日本逐漸分為了四個貨幣區,本土民眾的選擇,成為了貨幣區主要的支撐點。直到日本統一,才開始從泛濫的銅錢制度不斷過渡本土的三貨制度,最后逐步走向金本位時代[11]。
中國錢流入的銳減甚至斷流,帶來的影響不僅僅限于貨幣區塊的出現,還有貿易區位的變動與貿易中心的轉移。原本的貿易重鎮琉球由于中國銅錢供給的變動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從16 世紀30 年代起,琉球所用的銅錢已經從原來的洪武錢、永樂錢變成私鑄小錢,有江南、福建地區的私鑄錢,也有來自日本Sakai 等地的私鑄錢。隨著日本建立封鎖體制,琉球失去了在中日貿易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后逐步融入日本南九州的貨幣區域之中。在此貨幣區域中,以洪武錢為標準的仿錢十分盛行,但在另外幾個貨幣區洪武仿錢幾近消失,足見不同貨幣區域之間存在嚴重的貨幣分割特征。此外,該地區銅錢流通的結構分布也值得深思。有資料顯示,琉球多流通中國錢(明錢),可與中國本土不同的是,中國民間社會所用的銅錢在這一時期多為宋錢(或仿宋私錢)。劉光臨曾根據出土錢幣資料估算,日本和中國內地流通的宋錢是明錢數量的8 倍以上[12]。但在琉球,流通的明錢與宋錢居然一樣多,其中洪武錢與永樂錢比例大概為2:1,為永樂錢多用于賞賜和海外貿易提供了更為充分的證據[13]。
可見,宋元以降由于中國銅錢鑄量的急劇下降以及中國轉向私錢為主的現實,東南亞海域諸國均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危機。為了解決通貨緊縮的危機,各國自發性的衍生出各種私鑄小錢,以彌補原有銅錢的不足,銅錢的價值在某種程度上依托于自身的價值屬性。由于私鑄越來越泛濫,好錢與壞錢的差距越來越大,選錢、挑揀現象嚴重。黑田明伸、萬志英等人將其分別稱為標準錢和流通錢(通用錢),其中,標準錢作為由于稀少以及自身的價值屬性,具有良好的保值屬性,而流通錢則因為自身質量材質等原因僅用于日常交易。
四 中國本土的銅錢演變
宋代中國的銅錢體系最為發達,由于財政需求和市場交換的強大驅動力,銅錢作為基準價值手段的地位牢固確立,其流通的數量、范圍和深度可能超過了中國史上的任何一個王朝,堪稱耀眼的“銅錢時代”。不僅如此,宋代特殊貨幣區以及諸種貨幣形態如鐵錢、各類紙鈔、銀絹等,或需要錨定銅錢來作為價值基準,或以銅錢的計價尺度與其發生內在聯系,甚至各類衍生的信用票據,如鹽鈔、見錢鈔、見錢公據、關子等也多是以銅錢為本。不過,與之相對,元明時期中國的銅錢體系歷經低谷。蒙元國家對費時費力的鑄錢行為多無興趣,故銅錢流通已經顯現出日漸萎縮的區域化問題。而明代中葉的政府雖不斷厲行錢法,但受制于各種原因成效不顯,在政府銅錢供給急速減少和紙鈔崩潰后,民間也自行演化出多種貨幣使用方式,其中最為顯著的就是“行錢之地”的出現和銅錢的價值分層。
(1)“行錢之地”及其貨幣演化
“行錢之地”主要指仍在使用銅錢的地方,該名詞最早見諸于成化年間。“行錢之地”大概流通的范圍僅為南北兩京之間以大運河一線為中心的狹長地帶,其他原本使用銅錢的地方紛紛出現銅錢消退的問題。后來,甚至連原本向海外輸送銅錢的重鎮福建、廣東等地多不見銅錢流通,轉向行用白銀。“行錢之地”出現的成因主要有明代反復無定的貨幣政策、大運河一線市場的恢復發展、宋金元以來銅錢作為基準價值地位的消退等因素[14]。為了保證寶鈔的流通,在洪武年間頒布的禁令徹底破壞了銅錢信用。行錢之地的肇始出現在正統時期,史載:漷縣迤南,直抵臨清、濟寧、徐州、淮揚等處,軍民買賣,一切俱用銅錢[15]。
隨著寶鈔體系的崩潰,政府亦沒有及時供應銅錢來適用經濟成長,導致民間貨幣體系無法適應日益發展的社會經濟,此時,地域內自律性的貨幣使用方式出現,私錢就是民間解決銅錢短缺問題的重要方式,民間和地方官府通過仿鑄宋明錢牟利,市場依靠仿制宋明錢發展來維系。明代中后葉,社會經濟日益蓬勃發展,江南地區分工細化,底層交易數量增加,江南也成為私鑄錢的重鎮[16],包括日本、爪哇都有江南私錢存在的痕跡。
私鑄錢的泛濫,反過來不斷侵蝕著良好的宋錢,宋私錢的質量價值越來越低,逐漸被民間拋棄,適逢明代解除海禁,海外白銀不斷流入福建,在一系列貨幣角逐后,白銀成為福建的通用貨幣,“閩、廣絕不用錢,而用銀低假,市肆作奸,尤可恨也”[17]。低銀取代銅錢流通于民間下層,如同第一個白銀時代一樣,當時紙鈔崩潰后,白銀潛至底層交易市場。明代的情況也如從前,當紙鈔和銅錢相繼式微之后,白銀分化出低銀代替私錢維持交易。其他地區或因為銅錢匱乏而消退,或因為私錢劣質,多棄而不用。
(2)銅錢的價值分層
私錢所用銅料有限,基本使用鐵、錫、鉛等材料替代而成,此情況從爪哇銅錢匱乏時,本地商人大量售賣錫料給福建商人以求鑄幣即可證明。由于私錢濫鑄,其本身作為單位商品貨幣的價值也不斷下降,市場中魚目混雜,不同金屬含量、不同年代和做工不同貨幣各自具又不同的價值,典型的如史料顯示那般:
以臣所聞見,諸省直用錢,其銀錢相權也,則有以錢五六文當銀一分者,有以錢十文當銀一分者,甚有以十五六文、十七八文當銀一分者,其新舊雜行也,則有專用青錢、黃錢者,有兼用雜錢者,甚有用唐宋古錢,至窳爛不成樣而亦用之者,淆亂若此,豈圣朝能同九域之文,而不能同一錢之文[18]。
宋應昇詳細描述了當時市場中存在的貨幣分層現象,好錢(主要是官鑄制錢)價值較為穩定,銀錢比價大約在1:700 左右,但最差的劣質錢比價幾近達1:6000 的懸殊價格,足見市場之混亂。不同地區使用的貨幣和貨幣價值也不盡同,處于大運河兩端的兩京地區銀錢比價就顯示出很大的不同。黑田明伸認為,可能是由于北方軍隊駐扎在前線,軍人軍餉通常發銀,但在地方購買生活所需物品時,則需要將白銀換成銅錢,加劇了銅錢的需求量,因而造成巨大的南北差異,南京的錢銀比價幾乎是北京的兩倍[19]。不過,相關研究顯示,南北銀錢比價的不同主要源自鑄錢成本的不同,南方成本更低、行錢更廣帶來的錢價遠遠低于北京[20]。
在兩京市場中,不同的年號的銅錢其價值相差很大。為了能夠讓這些不同價值的貨幣同時流通于市場,民間自發形成了不同貨幣的兌換比價,并將“好錢”作為標準錢,用于儲藏財富;“劣錢”作為通用錢,不斷的流通于市場。明清易代后,隨著政府銅錢供給量的增加,以及舊錢、私錢大量存在,致使各地形成了具有地方習俗的地方錢,例如東錢形成了制錢160-165 文兌換小數錢1000 文的比價慣例,另有“京錢”“宣錢”“東錢”“津錢”“灤錢”“保錢”等各色名目的地域貨幣形式[21],其源頭就是明代銅錢價值分層所形成的地方兌換習俗,加上地方性的貨幣短缺,致使民間自律性的形成地域社會內部貨幣行用機制。
五 結論:以中國錢為基準的貨幣制度構架
當宋代銅錢供給大大減少時,處于漩渦之中的中國,在數朝鑄幣稀少的情況下,也經歷了嚴重的通貨緊縮、銅錢缺乏等問題。由于貨幣不足,中國在明代逐漸分化出行錢之地與不行錢之地,且行錢之地遠遠小于不行錢之地,不僅如此,行錢之地內部出現了私錢泛濫、價值分層、各地比價不一的情形。到了清代前期,在國家力量逐漸加強、市場需求不斷擴大等背景下,銅錢流通體制歷經兩漢、唐宋繁榮階段以及元明低谷后,在清代又一次興盛開來。清廷幾近在全國范圍內開爐鑄錢,并以政府力量作為推手來保障制錢的流通,銅政之嚴密發達、制錢管理之嚴格、制錢投放量在康乾時期的猛增等俱體現了錢法復蘇期的到來。不過,對于廣闊的疆域、日益擴大的市場而言,本身面臨幣材制約的低值小額制錢供應量與市場需求的矛盾一再存在,在東北、新疆等地產生了相應的地方錢。而且,此時白銀雖已經成為廣闊性的基準貨幣,在其日益流通的背景下,小額銅錢也占有一席之地。結合東南亞諸國的貨幣演變,不難看出自宋以來東南亞海域諸國所歷經的貨幣演變,都可以在中國本土找到真實存在的影子。
距離中國越近受中國的影響越深,爪哇所使用的銅錢多數為福建或日本運輸過去的私鑄小錢,因此尚未出現明顯的貨幣分層現象。在越南,由于中國宋錢和私錢共同流入,致使越南各地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短陌現象,以緩解好錢與壞錢之間的矛盾。受中國影響較深的日本,則出現了與中國相同的情形,不同貨幣區的形成、通用錢與標準錢職能屬性的分離,加之各地與中國聯動出現仿鑄私錢替代好錢等現象,都揭示出東南亞地區一直存在一個以中國錢體系為中心,通過多鐘貿易渠道連接,向四周不斷擴散的貨幣區域。
由宋錢所構建的環東南亞中國錢貿易圈出現危機后,為了維持貿易和地方日常的交易,各地自發演變并組織起以中國錢為基礎的貨幣體系。在環東南亞中國錢圈之下,一套潛藏在貨幣流通背后的非正式貨幣制度逐步搭建起來。當宋錢難以持續供給時,這套非正式貨幣制度自發組織交易,如明中葉中國紙鈔崩潰后,在長時間錢法難振的情況下,民間仍能自行解決通貨不足的問題,這套看不見的基礎性貨幣制度誠如黑田明伸所論,潛藏在大型而正式的貨幣制度之下,當正式的貨幣制度崩潰時,會在各個地方自發出現,并解決該地地區內部的通貨不足與價值不穩問題[22]。
注釋:
[1][6][22](日)黑田明伸著,何平譯:《貨幣制度的世界史——解讀“非對稱性”》,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18 頁。第2 頁。終章第193 頁。
[2][8]徐冠勉:《南洋錢法:近代早期荷屬東印度的中國貨幣,1596—1850》,《清華大學學報》(哲社版)(待刊)。
[3]Richard von Glahn,Chinese Coin and Changes in Monetary Preferences in Maritime East Asia in the Fifteenth-Seventeenth Centuries,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Vol.57,No.5 (2014),p.639.
[4]邱永志:《戰爭、市場與國家:正統景泰之際通貨流通體制的變遷》,《中國經濟史研究》2017 年第6 期。
[5]萬明:《15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貨幣新探》,《外國問題研究》2018 年第3 期。
[7]Akinobu Kuroda,The Eurasian silver century,1276-1359:commensurability and multiplicity,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2009,vol.4,no.2,pp.245-269。
[9]何平:《傳統中國的貨幣與財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73 頁。
[10]同[3];Kuroda Akinobu,Copper Coins Chosen and Silver Differentiated:Another Aspect of the ‘Silver Century’in East Asia,Acta Asiatica: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astern Culture,88 (2005)。
[11]周愛萍:《日本德川時代貨幣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年;Richard von Glahn,Chinese Coin and Changes in Monetary Preferences in Maritime East Asia in the Fifteenth-Seventeenth Centuries.
[12]劉光臨:《明代通貨問題研究——對明代貨幣經濟規模和結構的初步估計》,《中國經濟史研究》2011 年第2 期。
[13]邱永志:《論明前期的禁錢政策及其影響》,《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18 年第3 期。
[14]邱永志:《論明代的行錢之地》,待刊。
[15]張學顏等:《萬歷會計錄》卷41《錢法》,《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53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 年版,第1303 頁下欄。
[16]邱永志:《國家“救市”與貨幣轉型——明中葉國家貨幣制度領域與民間市場上的白銀替代》,《中國經濟史研究》2018 年第6 期。
[17]謝肇淛:《五雜俎》卷12《物部四》,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第357 頁。
[18](明)宋應昇:《方玉堂集》文稿卷7《代擬疏稿》。
[19]Kuroda Akinobu,Copper Coins Chosen and Silver Differentiated:Another Aspect of the ‘Silver Century’ in East Asia,Acta Asiatica: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astern Culture,88 (2005),pp.70-1;
[20]萬歷四十六年,給事中官應震提到京師錢銀比價為600:1,而南京則為1200:1。參見李義瓊、邱永志:《錢法與鹽法:從董應舉致仕事件看明末財政貨幣體制》,《南京大學學報》2019 年第5 期。
[21]趙士第、邱永志:《東錢問題再探》,《中國經濟史研究》2019 年第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