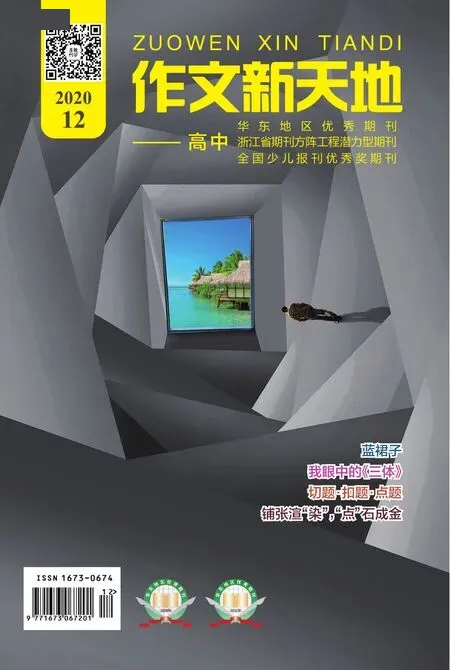讀《場所原論》有感
◎浙江省紹興魯迅中學高二(1)班
《場所原論》本是日本建筑師隈研吾用于指導建筑設計的一本小書,我卻有幸從清華大學建筑系畢業的舅舅那兒得到了它。我想建筑學作為一門工科,絕非單純是一門應用科學,而是藝術、人性與大地的結合。
“我相信,再次將人類與大地聯系是后工業化社會建筑的一個最大主題。懷著這種心情,我開始寫《場所原論》。”隈研吾在緒論中如是寫道。我由是知道,他正試圖在高樓林立的世界撒播一地建筑革命的種子。
自一百多年前法國建筑師勒·柯布西耶提出了多米諾生產體系后,水平結構的混凝體樓板取代了厚重的磚墻,在世界各地密密實實、層層疊疊地競相攀上天空,就連我所生活的古城紹興也已然沒有半點古城的面貌。人們總是習慣于認同素來所聽聞的、所看到的,因此,為人類幸福而發聲就顯得極為可貴——隈研吾略顯激進地指出,批量生產的、商品化的混凝土盒子是人與大地的割裂,工業化社會將白色盒子強加于人類,于是人類變得不再幸福。在這個人口爆炸的世紀,亞洲的自然環境因郊區化而被破壞,亞洲的城市因高層與超高層建筑而被破壞。
離開我所居的小小一隅,讓我們先飛過地中海,來到文藝復興的發源地佛羅倫薩。許多年前,我曾沉醉于其金黃色石磚所鋪成的街頭巷尾,仰視那日光普照時燦燦如龍鱗的紅色屋瓦。雄偉而深邃的高大穹頂透下幾束圣潔的光,我仿佛能聽到中世紀修士們悠揚的禮贊頌詩;在路面坑坑洼洼又狹長彎曲的小巷中撫摸墻上細膩而有質感的羅馬石雕,我仿佛看到掙脫了人性束縛的工匠畫家們正愉悅地沉浸于這座城市的質地、光、影與愜意中。那一刻,我看懂了與我擦肩而過的路人、拐角處品雞尾酒的歐洲人臉上流淌的喜悅之情。我看到了我呆立于街角的小小的身影,正像第一批走向世界的中國留學生一樣,久久佇立,心里沉沉的。
如今我要發聲,如今我有一個夢想。某些口口聲聲要弘揚中華文化而為混凝土大樓加上中式斜頂的人,就應該去安徽的農村看一看。穿過丑陋單調的灰白水泥平房,你也許還能找到幾進幸免于拆毀夷平之難的百年徽派建筑。那斑駁石墻正中的一道小小的石門,那天井四周雕工精湛的高梁細柱,那質樸的屋瓦勾勒出的四方的藍天,以及淅淅瀝瀝的雨中古老木材的氣息、光影與氛圍,會讓人明白什么是中國人所信仰的天、地、道與落葉歸根、無盡長江、秦時明月漢宮秋。美感的觸發依賴于人的細膩情感,這也許恰恰是工業社會所缺乏的。急功近利、自以為能征服自然,也許是一種病態心理。這來源于對自然或人世美好細節的漠視與麻木不仁,來源于童心褪去后注意力集中于自我的塵俗野心與視而不見。然而,種種駭人聽聞的事正發生在我們身邊。街坊鄰里的笑談不再,寬闊的水泥路將幢幢方方正正的高樓分隔成方塊,遙見幾個路人卻行色匆匆,與你毫不相關,視若不見,擦肩而過便是一生的相別;野草野花不再,只剩一排排園藝化的香樟與單調的方形紅綠灌木或不停更換的時令花卉;濕地白鷺不再,盡將湖岸用巨石壘起,鋪上單調的草坪,灑上滅絕昆蟲的藥劑。每當我坐車從郊區駛向城區,便總是眺見地平線上盡是一架架吊車正侵蝕著中華的土地,聳立起與大地割裂的商品盒子。
康德說過,美是一種多樣性的和諧,崇高卻不自然的事物就是怪誕。我以為碩大的高樓正是怪誕。羅素說過,單調的事物使人厭煩。我以為單一的所謂綠化與光滑無質感的石灰水泥墻使人厭煩。而厭煩的反面是興奮、刺激,而不是優美與細膩的情感——這恰又助長了許多城市人麻木地追求刺激或過度工作成為工作狂而最終遠離了現實的美好。如今,多災多難的2020年,大自然正用病毒、山火、洪水、地震、極地升溫等極端現象來懲處人類對地球生態系統的破壞。然而,白衣天使不僅要醫治病魔的受害者,更要醫治逐漸在整個社會充斥的競爭之風、自大之行、盲目追求、急功近利、重物質而輕精神等一切所歸屬的脫軌了的生活哲學。我們雖然只是時間長河中一閃而過的微塵,卻有創作、享受美的權利,何必非得受世俗觀念的框定來賦予生命價值與意義?今天,我有一個夢想,在不久的將來,當中國成為生產力高度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人們能生活在彌漫著溫馨、愉悅、美與自然的城市環境中,與不相識的人微笑招手,與所愛的人漫步于美麗的城市,與街坊鄰居開懷暢談,在美中感受時間,在時間中感受生而為人的美好——那么慢,那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