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莊說藝隨札(七)—格局
朱天曙
北京語言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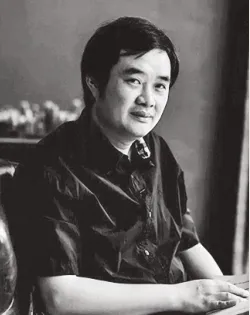
《莊子·逍遙游》開篇就講了這樣一個氣勢雄渾而壯觀的故事:
北海有一條巨魚,名字叫作鯤。鯤的體積之大,不知道有幾千里。變化而成巨鳥,它的名字叫作鵬。鵬的巨大脊背,也不知有幾千里。它奮翅而飛,翅膀就像天邊的云。當海動風起時,就遷飛到遙遠的南海,那南海是個天然的大池,高遠深邃。
水若積聚不深厚,那么它負載大船就沒有足夠的浮力。把一杯水倒在堂前的洼地,那么放進一根小草便可當作船而浮起;倘若放上一個杯子,那就要被粘住,這是水淺而“船”大的緣故。如果風力積聚得不強勁,那么它承負鵬的巨大翅膀就沒有力量。所以,大鵬只有飛上九萬里的高空,大風才能積聚在它的身下。然后乘著風力,背負青天,再沒有什么可阻遏它飛往南海。
蟬和小鳩卻譏笑大鵬,說:“我們用盡氣力飛了起來,撞到榆樹、檀樹梢頭,有時或許還飛不到,投落到地上也就算了,為什么要到九萬里的高空再往南飛呢?”
到郊野去的人,只要吃下三團飯出行,回來后肚子仍然很飽;到百里之遠的地方去,頭天晚上便要備好干糧;到千里之遙的遠方,就需要出行前三個月備集干糧。蟬和小鳩這兩只蟲鳥又知道什么呢?
小智不會了解大智,短壽不能了解長壽。那朝生暮死的菌蟲,不懂得早晚之分;那春生夏死、夏生秋死的寒蟬,不知道什么是一年的時光。楚地的南方有一只靈龜,以五百年為一個春季,五百年為一個秋季;荒古時代的一棵大椿樹,以八千年為一個春季,八千年為一個秋季。世人只知道有個彭祖以長壽而聞名,一說到長壽大家都拿他來比,這豈不是太可悲了嗎?
學習藝術的人都應該想象一下這個鯤鵬展翅的場景。在天高海闊的浩瀚背景中,鯤鵬展開它那遮天蔽日的巨大翅膀,水擊三千里,扶搖直上九萬里,由北海向遙遠的南海飛遷,這樣的形象、意象和境界是何等的令人心胸開闊、意氣昂奮啊!
大鵬能夠壯飛、遠徙,不僅僅在于它有“圖南”的遠大志向,還在于它憑借了翼下厚積著的強勁風力。“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這就是“積厚”的重要意義。學藝的人要有高遠的志向,才有“積厚”的動力。大鵬憑借翼下巨大風力而凌飛的形象,正是講這個道理。歷史上著名的大書畫家,無論是東晉的“二王”,唐代的顏真卿、張旭、懷素,還是近代的吳昌碩、黃賓虹,哪個不是像鯤鵬一樣,在書畫藝術的世界里積累著個人的藝術實踐和學養,最終取得杰出的成就。
與大鵬的壯飛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蟬與鳩可笑的態度。這兩只蟲鳥自我滿足于榆、枋上下的騰躍,譏笑大鵬海天萬里的壯飛,表現出封閉和淺薄,可笑又可悲。這個故事是莊子中開篇的故事,讓我們以大鵬自勉,立高遠之志,蓄“積厚”之力,行壯飛之舉,勇往直前,遨游在藝術的天空之中。
《莊子·秋水》還有“望洋興嘆”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
故事里說,秋汛應時到來,百川之水都匯流到黃河。主流河道變得極為寬闊,兩岸及河中水洲之間,連牛馬的形狀都分辨不清了。這景象令河伯揚揚自得,以為普天下的盛美都集中在這里。他順著河流向東而去,抵于北海,向東方縱目瞭望,竟看不見大海的邊際。
這時河伯收斂起揚揚自得的笑容,仰望海神而感嘆:我看見您這樣浩渺無涯、博大深邃,倘若我不是來到您的門口,可就太危險了,我要永遠被曉悟大道的人所取笑了。
北海之神說了一段話,很深刻。他說:井底的蛤蟆,之所以不能和它談論大海,因為它拘囿于自己狹小的天地里;夏季的蟲子,之所以不能跟它談論冰雪,因為它受到生存時間的限制;孤陋寡聞的書生,之所以不能跟他談論大道,因為他所受的片面教育桎梏了他的思維。現在你從河岸下走了出來,看到了浩渺無涯的大海,才認識到自己的渺小和鄙陋,這才可以跟你談論大道。
天下的水沒有比海更大的,然而四海存在于天地之間,不就像蟻穴在大澤里一樣嗎?九州存在于四海之內,不就像小米粒在太倉里一樣嗎?莊子的討論汪洋恣肆,“海波連天,浪花無際”,他的哲學也有一種含江負海之氣。《秋水》中河海氣象的描寫以及河伯與海神的對話,顯示了其哲學博大、深邃的視野和境界,這就是格局。藝術創作和研究的人需要有大格局,不計較一時得失,不與小人爭一時名利,潛心藝事,才能真正走遠、走高。
海神若與河伯的對話,把我們的視野和思考引入一個時空無窮、認知無涯的世界。藝術表達個性,很多人取得某一方面的成績,或入展,或得獎,或在某一方面有所建樹,常常目中無人、自以為是,不知山外有山,樓外有樓,格局狹小,不容易突破,從莊子的故事中,我們要有所悟。
莊子巧譬妙喻,善于將紛然雜陳的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聯系起來觀察和思考,特別是《秋水》中把海的氣息與有關時空無窮性的哲學聯系起來,這種深邃思想和超越精神值得我們反思。
大海意象和藝術精神的超越具有某種相似性。黑格爾說過:“大海給了我們茫茫無定、浩浩無際和渺渺無限的觀念。人類在大海的無限里感到他自己有限的時候,他們就被激起了勇氣,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對于我們學習書畫而言,超然的精神和格局尤其重要。
《莊子·秋水》中井底之蛙的故事是格局小的典型。住在淺井里的青蛙對東海的大鱉說:“我真快活啊!出來活動,就可以在井欄之上蹦蹦跳跳;進去休息,就回到井壁的破磚之間。入水而游,水架著我的兩腋,托著我的下巴;踏入泥中,深泥只能淹沒我的腳背。環視那些螃蟹啊,蝌蚪啊,有誰比得上我呢?況且我獨占這一坑子水,叉開腿站在淺井里所感受到的樂趣,也可以算是達到極點了。先生你為什么不經常到我這里看看呢?”
東海大鱉的左腳還沒踏進淺井,右腿的膝蓋就被絆住了,于是猶豫了一陣只好退出來,把大海的情況告訴青蛙說:“千里的遙遠,不足以表述它的廣大;千丈的峻高,不能窮究它的幽深。夏禹時候,十年九澇而海水不增多;商湯時候,八年七旱而海水不減少。不因時間的長短而改變,也不因雨量的多少而增減,這就是住在東海的最大快樂!”
淺井里的小青蛙聽了這一番話,惶惶不安,手足無措,茫茫然像失了魂一樣。坎井之蛙與東海之鱉各有不同的天地,但坎井之蛙居然向東海之鱉炫耀自己狹小的天地,真是可笑。這個故事和上面望洋興嘆的故事道理是一樣的。藝術家小有成績就沾沾自喜,頭上長角,很可能是在思維與認識上走進“坎井”,要有大海的氣象,才能有所大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