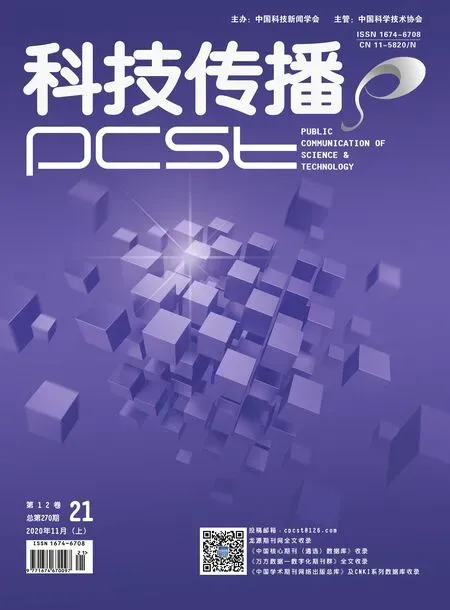近年好萊塢電影中的華人角色分析
1 好萊塢電影中的華人角色嬗變
1.1 默片時期:排他
默片時代,由于神秘東方對整個西方世界不同尋常的吸引力,好萊塢就已經開始著手對華人角色的刻畫。1894 年,無聲片《華人洗衣鋪》問世,以一種夸張式的呈現方法講述了,中國人是如何在警察的窮追不舍中想辦法逃脫的。在此時期的亞裔角色,多是惡棍、罪犯等反面角色,長辮子及留長指甲等細節被無限夸大。
1.2 20 世紀之初:探索
當然,一個值得人注意的細節也是發生在默片時代。作為移民美國的第三代華人,黃柳霜因1919 年參與了電影《紅燈籠》的拍攝,踏上了她星光熠熠的電影人生,成為第一位美籍華人好萊塢影星。1921 年,黃柳霜參與了由韋斯利·巴里執導的電影《人生》(Bits of life,1921)的拍攝,她在戲中飾演一個妻子與母親的角色,至此開始,她自然生動的演技和“清湯掛面”式的中國娃娃造型逐漸被大眾所熟知,并多次作為封面人物出現在英美多國的報刊畫冊上。這一時期華人角色的塑造,以黃柳霜所演繹的角色為主,大多是從西方人“他者”觀念中衍生出的逆來順受、懦弱以及充滿屈辱感、歷盡折磨的華人角色,且在她42 年的演藝生涯中,極大多數角色在影片的最后都難逃死亡的命運。美國亞森普遜大學教授理查德·厄爾林認為,華人角色的自殺結局是好萊塢在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描述亞洲角色共同點的一種慣用手法。
1.3 轉折時期:武打熱
黃柳霜之后,也是真正令中國人角色開始發生轉折的重要人物——李小龍的出現,致使這一時期好萊塢的華人形象一度好轉。1972 年,以愛國鋤奸為內容、徒手搏擊為特征、李小龍主演的《精武門》,不僅打破了早前西方人眼中的“東亞病夫”形象,而且使以李小龍真功夫片為代表的中國武打電影以及武術在西方盛行。但與之相伴的,也使得其在好萊塢電影的角色選取以及多元化發展受到了限制。至20 世紀后期,以楊紫瓊、劉玉玲為代表的闖入好萊塢的華裔影星,武術功底依然是他們在好萊塢生存與發展的唯一依仗。
1.4 發展時期:多元
20 世紀后期至今,隨著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盡管美國對中國的敵視、尤其是對共產主義的敵視并沒有解除,但是他們逐漸意識到中國正在成為亞洲的后起之秀,且中國擁有廣大的市場及消費人群,這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美國在70 年代所提出的“后殖民主義”。為快速入侵中國消費市場,搶占亞洲電影市場發展先機,好萊塢電影中的華人形象開始呈現出多元化發展趨勢,我們可以看出由“他者”觀念衍生出的華人形象正在被不斷的修正,如災難片《2012》中所塑造的華人形象善良、英勇且充滿正義感,擔負起了拯救全世界的責任。
綜上所述,華人角色在好萊塢電影這一百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大體經歷了四個時期。從19 世紀末期默片時代的歧視,20 世紀初期的好奇與探索,到20 世紀中后期李小龍時代的認同與敵視,再到如今的多元化發展。可以說,華人角色正在經歷由“惡棍”到“紳士”、由“蕩婦”到“俠女”、由全盤負面逐漸向友善化發展的這一特殊的過渡時期。
2 好萊塢電影中華人角色現狀
發展至今,好萊塢電影中的華人角色在不斷演變的過程中,也開始呈現出一些具有穩定性的共同特征,主要表現在華人角色的演員選取、角色的多方面定位的方面。
2.1 演員選取
電影作為一種表現性藝術,極為注重對客體的塑造與表達。而演員作為塑造角色的主體,對于表現客體角色和傳達電影主旨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在近年來的好萊塢電影中,演員自身對中國本土的影響力以及女演員的相貌是否符合好萊塢對東方女性的傳統認知,這兩方面是演員能否成功進入好萊塢的主要指標。
1)國內影響力。近年來,歐美消費市場的低迷間接影響了好萊塢電影產業的低迷,相反,以中國為代表的廣闊亞洲市場異軍突起,諸多好萊塢導演、投資商將眼光轉向了擁有強大消費群體的中國。就目前好萊塢選角模式,華人演員的國內影響力是很大的決定因素。從近年來包含有華人演員的好萊塢(含美國獨立電影公司)作品來看,能夠成功從角色試鏡中突圍而出的華人演員,在具有一定的演技之外,其在中國的票房實力以及粉絲號召力也是能否入選的絕對指標。
2)女性演員相貌。除了華人演員的吸粉實力以及武打水平,作為眾多想要躋身好萊塢的中國女影星,自身相貌也是競角的重要標準之一。對于整個歐美市場來說,中國人形象,尤其是中國女人的形象帶有極具特色的異域風情,就如同上個世紀早期在好萊塢名聲大噪的黃柳霜,以及本世紀之初王家衛電影《花樣年華》中張曼玉身著旗袍、富有濃郁東方韻味的中國女人形象。電影是一種思考活動,也是一種審美性活動。一些華人女演員憑借著自身相貌條件,也躋身到這個行列中來。外媒對她們的評價多為中性偏負面,但這并不影響華人女演員前仆后繼地進軍好萊塢“打醬油”。
2.2 形象定位
一部好的電影,需要優秀演員全身心的投入角色、塑造形象,然而真正能夠打下成功基石的還是劇本本身對人物形象的刻畫。近年來,好萊塢對華人形象的定位呈現出三大特點:適合角色少、演員串用,角色單一化、人物性格扁平化以及負面形象仍存、總體態勢好轉。
近些年在好萊塢出現的華人形象,大多依舊是李小龍時代所定下的基調:身手不凡的傳統中國人形象。這就導致了華人角色的單一,以及人物性格不夠飽滿。華人形象的出現大多僅僅是作為一種文化符號,并沒有進行立體的人物塑造,又或者僅僅是為了襯托美國精神與形象,或者說是整個白人文化的襯托物。
3 華人角色發展趨勢及反思
藝術作為一種發現美、生產美的特殊社會意識形態,除了受到自身規律作用,政治、經濟、文化等其他意識形態以及歷史地理因素都對其有重要影響。好萊塢電影發展至今,華人形象的演變同社會領域的發展變革聯系密切,由此,我們可以從社會因素出發,聯系華人形象在好萊塢電影中的現狀,窺見到其未來的發展趨勢,并且從自身角度考慮,求新、求變、求發展。
3.1 趨勢
1)“他者”觀念根深蒂固,文化偏見難以根除。1848 年,美國開始對西部進行大開發,加利福尼亞“淘金熱”興起,大量華人前往加州淘金或參與鐵路修建,美國工人階層認為這觸動了自身利益,于1882 年促成了《排華法案》的出臺,且在1886 年掀起了西雅圖排華騷亂事件[5]。20 世紀70 年代,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普遍興起后殖民主義思潮,強調文化霸權以及他者與自我的身份認同。以此來看,無論是從歷時還是共時的角度,西方的反華、反亞情緒是有跡可循且影響范圍深遠的;反映在文化領域,西方文藝工作者以此來塑造的華人形象,充滿對華人的刻板印象,也恰恰切合了其國家對華人的一種政治情緒。
從眾多在美國公映的國產電影的叫好程度中不難看出,大多數影片所表現的時期都是民國或更早以前,基本沒有新中國成立之后的時期。這反映出美國甚至于整個西方世界對中國的印象還停留在曾經的舊中國。例如《大紅燈籠高高掛》《紅高粱》等影片中,女主人公的扮相基本上就是20 世紀初黃柳霜扮相的翻版,這十分符合美國對華人形象的認知。在這近一個世紀的時間里,即使中國的綜合國力已經躋身世界前列,這種認知在整體上也并沒有得到改善。頑固、死板、迂腐和落后的華人形象已經在美國人心理根深蒂固,且如今的中美關系并不明朗,華人形象在好萊塢電影中的出現更多的是這種思維上的轉變仍然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2)表面“全球化”,實質文化入侵。美國政治學家、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在《軟實力——國際政治的制勝之道》中率先提出軟實力概念。當今社會,電影作為國家文化軟實力的一個重要領域、文化傳播中影響深遠的一環,它不僅僅具有文化宣傳的作用,對美國人來說,它更是表面進行文化交流與傳播、實則為實施文化滲透、開展文化入侵的有力武器。很顯然,好萊塢作為武器持有者,有著無法比擬的優勢。以超級大國的國際影響力、雄厚的經濟實力為依仗,擁有成熟的產業機制、雄厚的經濟實力、豐富的國際化運作經驗,以及最重要的是近百年來對世界范圍內大眾文化潛移默化的熏陶。這些優勢使得美國打著文化“全球化”的旗幟,用掏空了精神內涵裝入美國精神的中國形象進行著以文化侵略為本質的傳播活動。
從備受矚目的迪士尼動畫電影《花木蘭》,到名聲大噪的夢工廠動畫電影《功夫熊貓》,是影片的人物原型、道具服飾設計、背景選取等都依照中國特色進行了原汁原味的呈現,如花木蘭就是一個典型的華人形象代表。然而在故事情節設計等電影內核方面,卻充滿了“美國式”的表達。好萊塢主流電影極力秉承著表達民主、自由和英雄拯救的所謂美國精神的目標,這種表達隱藏在極具落地性、能夠引起他國受眾共鳴的故事情節中,通過世界電影產業的交流與傳播,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其他國家的文化意識與價值取向,增強其與美國精神的融合度,繼而開創有益于美國進行多方面多領域發展的生態環境。
3.2 措施
1)借鑒成功經驗,加快“走出去”步伐。如何有效的拔除文化偏見?如何打破他者觀念中的刻板印象?如何面向世界、向世界展示真正的華人形象?加快中國自身文化的“走出去”步伐是必由之路。在落實過程中若能借鑒好萊塢電影產業的成功經驗,潛移默化地改變刻板印象,對今后世界范圍內電影中的華人角色的塑造更是利大于弊。
想要走出去,必須獲得他國人民在文化上的認同度。而認同度的建立又必須在表現人類所共有的普世價值觀,以此為母題進行創作。縱觀好萊塢電影的輸出,成功之處皆在于此。《阿凡達》的主題是保衛家園,敬畏自然。《泰坦尼克號》的主題是在災難面前的人性光輝和愛情的偉大。以漫威影業為代表的英雄類系列電影都是以維護世界和平、保護人類安全為主旨。以此來看,華人角色的重新確立,需要借助于具有普世價值取向的、中國電影的海外傳播。
除了表現人類的“共同美”,還可以捕捉他國人民熟悉的意象融于自身的作品之中。由約翰·卡蘭執導的電影《面紗》中,加入了中國演員夏雨的精彩演繹。中國電影也陸續開始借鑒此法,《北京遇上西雅圖》《泰囧》《唐人街探案》等影片都奔赴國外取景拍攝。此外,中外合作制片模式也興盛起來,阿里影業與曾執導經典電影《西西里的美麗傳說》的導演托納多雷簽約合作,中國導演陸川執導的電影《我們誕生在中國》也是中、美、英三國聯合制片。
2)堅守文化自信,增強文化軟實力。站在中國消費群體的角度,我們很樂于見到好萊塢電影中的華人角色從愚昧、冷酷、呆板變得多元和有層次性,從全盤否定、妖魔化逐漸轉變為正面、有自身獨特的魅力。但是,這些變化大多只是文化滲透戰略的淺層表現,或者說是屈于現實利益的壓迫,而非標志著在兩國人民交流過程中,美國人在看待華人角色方面有了實質性的改變。面對當今意識形態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只有全面擺脫舊認識、舊面貌的影響,將文化入侵和霸權主義的發展策略扼殺在搖籃中,確立平等的對話模式和互惠互利的文化產業往來,才有可能對好萊塢電影中的華人角色進行重新確立,塑造現代華人角色和如今真正的中國面貌。
1999 年,韓國政府迫于電影人對開放外國電影配額不滿,而發起的“光頭運動”的壓力,調整了放映本土電影天數的政策,并突出了編導的重要性。而后韓國電影界力求創新,并借鑒好萊塢電影以及中國香港電影的成功經驗,立足本國國情和自身生活經驗,打開了煥然一新的韓國國產電影市場,并為世界輸送了諸多優秀電影作品和優秀電影人。結合韓國電影的發展歷程,求新、求變才是發展的基石,文化軟實力的加強以及文化自信心的建立離不開文化創新。
中國電影界應站在理性的立場上去看待進口電影,尤其是競爭力極強的好萊塢電影。多從自身考慮,尋找國產電影的突破口,而不是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大肆宣傳落后的舊中國形象時保持緘默。我們應以自身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蘊對抗此等文化入侵,使謠言或不實的宣傳在文化交流中不攻自破,讓華人形象在文化傳播中得以重生,展我中國大國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