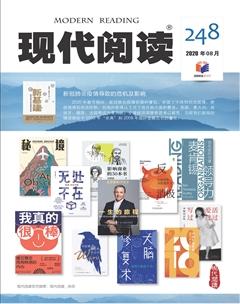橫跨大西洋的海底電纜是怎樣接通的
快速現代化的19世紀,需要運往大洋彼岸的并非只有貨物和乘客。起起伏伏的汪洋正日益被視為一條信息的高速公路——被大洋兩岸以及更遠的人們用來互通情報、新聞、情侶誓言、出生公告、船舶往來通告、股票價格,以及政府更迭和國王去世的消息。大西洋海底電纜成功接通前,歐洲和北美之間的通訊常要耗費數周。但是,海底電纜的建設將耗時縮短至幾秒鐘。當時這條電纜主要用于發電報,然而,它的建設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簡單,前后耗時12年,經歷了5次嘗試才得以成功。
19世紀初的世界已經發生了變化,走上了向今日巨大地球村轉型的道路:費城和彼得伯勒之間,又或是巴西和比利時、莫斯科和蒙得維的亞(烏拉圭)之間的信息交流,變得跟曾經的鐵匠和警察、旅店老板和教堂執事之間的往來一樣重要了。為了運行順暢,社區內的相互聯系素來至關重要:隨著世界人口在移民浪潮中混雜融合——尤其是19世紀大西洋兩岸,歐洲和埃利斯島之間的移民——一種全球社區的感覺也建立起來了,需要不斷增長的信息和情報的流動。
1760年,喬治二世國王去世的新聞在波濤洶涌的海上顛簸了6個星期才到達殖民地時期美國的臣民耳中,顯示了跨洋傳遞信息是多么緩慢,令人懊惱。一個世紀后,消息傳遞還是沒快多少。美國內戰期間,電報已經發明出來,使得大陸上的通信變得容易,因為陸地上可以通過豎電線桿來建立線路。而要隔海獲取消息則需要全部的創造力:倫敦報紙要發布來自北美公告,要先送到紐芬蘭外圍的海岬,然后劃船把手寫的副本帶給即將東去的輪船,接著匆匆抵達對面愛爾蘭北部外圍的海岬,然后由捕鯨劃艇將它們送到最近的電報收發室,把它發往倫敦。這個耗時又笨拙的過程還不是什么巨大的進步:這僅僅意味著北美安蒂特姆或葛底斯堡戰役的消息,或謝爾曼大軍打過格魯吉亞的情況,兩周之后才可以在倫敦白廳或蓓爾美爾街的俱樂部里讀到。
速度在一點一點地提升:1864年7月4日,有關弗吉尼亞州戰役的細節,僅僅兩周后就見諸倫敦《泰晤士報》。1865年4月,當林肯總統被刺身亡時,電報新聞——也是從手寫的信件轉錄而來的——被裝在一個密封的牛皮袋子里,借“新斯科舍”號輪船去愛爾蘭多尼戈爾的機會被送到了郵局,又在那兒被送去印刷,然后震驚而沮喪的倫敦了解到了這個消息——在刺殺事件發生12天以后。
顯然,需要一種新的更快速的通信方式,而新發明的電報將是關鍵。而在隨后的解決方案中占據關鍵地位的,是一個幾乎未被探索過、海風呼嘯的海島,唯一的特別之處就是它是大西洋上的第四大島,僅次于格陵蘭島、冰島和愛爾蘭——英屬殖民地紐芬蘭。19世紀中葉,一小群企業家想了解如何加快消息跨洋傳遞的速度,便開始把目光聚焦在這個島上——這是因為紐芬蘭可提供北美到歐洲距離最近的地點:從圣約翰斯的海港到康尼馬拉的懸崖只有區區1600英里(1英里約合1.61公里)。
海底電纜——歐洲已經有了這項發明:1850年8月,英國和法國之間已經鋪設了一條電報電纜,不久之后,英國和荷蘭之間、蘇格蘭和愛爾蘭之間的海域也有了電纜——或許也可以從圣勞倫斯灣橫跨卡伯特海峽。如果能再有一組地上線路把這條水下電纜連接到圣約翰斯和哈利法克斯,再另鋪一條線路連接波士頓——天哪,那就只需要在紐芬蘭與愛爾蘭之間設立一支快輪船隊定期往返,即可讓信息在短短7天之內到從紐約傳遞到倫敦。
就在這個時候,35歲的賽勒斯.維斯特.菲爾德走進了這個傳奇故事。他出生于馬薩諸塞州西部伯克希爾山一個富裕的造紙世家。紐芬蘭計劃的主要支持者來見他,希望能說服他投資。菲爾德禮貌地接待了這個人,說他會考慮一下——然后,當天晚上他在藏書室讀書時,正巧用手轉動了一個地球儀。它是那種適合放在紳士的藏書室里的大型地球儀——菲爾德注意到,他的手能跨越紐芬蘭和愛爾蘭,還有倫敦和紐約之間的距離。
于是他馬上意識到,為了節省幾天的電報傳輸時間,不能在紐芬蘭和新斯科舍的荒野里建電纜線路,但人們可以在整個大西洋的最窄處,直接從紐芬蘭鋪設電纜到愛爾蘭。如果他能做到這一點,就可以把19世紀全球最重要的兩座城市之間傳遞消息的時間,從幾天減少到幾秒鐘。
菲爾德既沒有技術頭腦,也不是海洋地形專家,但他立即給兩個人寫了信,他們是:發明了電報代碼的塞繆爾.摩斯和美國海軍的馬修.方丹.莫里,后者對大西洋的考察確證了廣闊的海底高原“大西洋中脊”的存在。兩個人都告訴菲爾德,他的想法是可行的:摩斯10年前就已經試驗過在紐約港下面走電纜,并曾寫信給美國政府,大意是“肯定可以利用電磁方案建立跨大西洋電報通信”;莫里——盡管是因為絲毫不知道大西洋中脊是一片和落基山一樣鋒利又不穩定的高山幽谷(也就是說,根本無法從空中盲目地空投電報電纜下去)——這樣寫道:“那片高原……似乎就是專為承載海底電報電纜,保證它們免受傷害而擺在那里的。”
于是1854年5月,紐約、紐芬蘭和倫敦電報公司成立了;兩年后,大西洋電報公司也同樣在倫敦成立。兩家都致力于籌集項目資金。美國公司的董事長彼得.庫珀——紐約庫珀聯合學院的創始人——相信,他要做的事將“會為世界的福祉提供一份巨大力量的可能性”。
英國政府對這項計劃尤其興奮,表示愿意勘測路線,甚至提供船只幫助鋪設電纜,并支付一定的費用——唯一條件是,能讓英國官方的消息擁有絕對優先權。美國人則對同一問題進行了更加激烈得多的辯論。
并不是每個新大陸的人都想與舊世界有這樣的親密接觸。美國作家梭羅,這個一貫脾氣暴躁的厭世者,就刻薄地評論說,如果第一個到達美國的消息只是“阿德萊德公主得了百日咳”的話,那么在大西洋底下鋪通信電纜基本沒什么價值。而且,美國還存在一種鮮明的革命后、燒毀白廳后的仇英情緒,特別是在南方,任何英國的東西在那里都會受到廣泛的厭惡和鄙視。盡管如此,經過在國會一番艱苦游說,終于通過了必要的法案;1857年3月,在跟下任總統詹姆斯.布坎南交接之前,富蘭克林.皮爾斯總統簽署了法案,開出的條件和倫敦之前同意的方案完全一致。建設——有史以來可以想象的最雄心勃勃的建設項目——現在可以開工了。
媒體有非常多的宣傳:大洋兩岸的報紙上充滿了該怎么建設這些電纜的建議——用氣球吊住,有一個通訊記者寫道;用浮標串成鎖鏈,將電纜拴在上面,在海面下晃動,船舶可以在這兒停泊,就像今天的汽車停在路邊服務站一樣裝滿消息;維多利亞女王的丈夫認為應該用玻璃管把它套起來。還有一些人認為——海洋有不同的密度分層,會影響各種物體下沉的深度:馬會比青蛙沉得低,胖子會在瘦子的下面,而電纜只能下沉到海洋中的一定深度,然后就懸在那里,就像今天噴氣式飛機噴出的尾跡一樣。
科學家們為電纜該有多粗而爭吵不休——粗銅線可以傳導進行長途通訊所需的大電壓,但也意味著它可能在下降到海底時在自身重量的作用下斷裂。最終,人們決定制造一個和男人的食指差不多粗的電纜,銅芯外面加杜仲膠絕緣,然后涂上大麻和焦油,最后用鋼絲包裹起來,每英里重約一噸(雖然懸在水中時只有約1340磅)。在1857年初夏,2500英里電纜——如果把所有組件的電線算上,總長有34萬英里——在倫敦和利物浦的工廠里生產出來,并被精心盤繞成大鼓狀,裝上兩艘帆船USS“尼亞加拉”號和HMS“阿伽門農”號,一條船上載一半:約1500噸重。
8月,兩艘船在護送下駛往愛爾蘭西南部的瓦倫蒂亞島,一群魁梧的水手拖著電纜的一端,穿過浪花走向岸邊,進了名字聽來十分大氣的“金箔灣”。人們紛紛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講和無比虔誠的祈禱,并點燃了煙花爆竹。然后,在海軍護航艦隊的陪同下,兩艘運輸電纜的船只退回了海上,一邊走一邊放電纜——由此開始了一段充滿了意外、挫折、煩躁和沮喪的傳奇,一直持續到第二年,因為事實顯示,只要放入電纜,它就會一再斷裂,要讓它永遠沉入海底,似乎不太可能實現。
船員們想了各種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們選擇不從海洋兩岸開始,而從中間開始,先讓兩艘船在距離兩邊海岸各800英里的地方會合,再把電纜拼接在一起,然后彼此駛離,駛向相反的海岸。但他們后來又遇到了無數的問題——尤其是一場前所未有的盛夏風暴,幾乎把載著電纜的沉甸甸的英國船掀翻了。而且,和以前一樣,電纜依然會斷裂、損失。技術故障持續困擾著鋪設工程——包括一個著名的瞬間:在船尾要放下電纜的那一刻,一艘船上的工程師注意到電纜上有個問題,瘋狂地沖過去,在電纜沿著甲板往下滑的時候進行修復,趕在它入水造成短路前搶修。他們當時成功了——但電纜終究還是出了問題。
隨著成本日漸攀高,遠在倫敦的公司董事們越來越氣惱。有人說,這個項目在技術上是不可能實現的,并希望放棄它。媒體也開始冷嘲熱諷。還有人寫詩調侃這次行動。人們的信心動搖了,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
但隨后,在1858年夏末,在經歷了3次失敗的嘗試之后,兩艘船最后一次會合,在7月29日把電纜接到了一起,并駛離對方,然后,這次居然奇跡般地一帆風順,沒有遇到任何問題。USS“尼亞加拉”號在8月4日駛入了紐芬蘭的三一灣,RMS“阿伽門農”號僅僅一天之后到了600英里外的瓦倫蒂亞島。它們之前在大洋中間接在一起的電纜還在工作;甚至在兩頭的水手拖起電纜被連接到已經建好的電纜基站上時——紐約和倫敦的陸上線路正等著被連接——它仍然看起來完好無損。
大家全都欣喜若狂。當倫敦第一次聽到傳來的消息,說電纜已經完成連接,并保存完好時,《泰晤士報》激動得幾近窒息,簡直讓大多數讀者覺得有失以往的穩重:
……自從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后,再沒有什么可以媲美這次項目給人類活動領域帶來的巨大拓展了……大西洋干涸了,我們如愿以償地實實在在成了……一個國家……大西洋電報把1776年的《獨立宣言》撤掉了一半,再一次讓我們不由自主地融為了一個民族。
8月16日,人們采用現在著名的塞繆爾.摩斯電碼,將第一批消息送過了大西洋——維多利亞女王首次向布坎南總統表示她誠摯的祝賀,并“熱切期待”新的“電纜”跨越大洋,以鞏固兩國之間的友好關系和兄弟情誼,布坎南不久從華盛頓回復了類似的官樣話語。很快,第一條商業訊息出現了——從丘納德公司傳來了兩艘船,“歐洲”號和“阿拉伯”號在加拿大入港時相撞,但未造成人員死亡的消息;然后是一系列的新聞事件。兩大洲之間最早的一批電報消息,要么像梭羅擔心的那樣,完全是些雞毛蒜皮(“普魯士國王病重,無法拜訪維多利亞女王”),要么就能轟動一時。
但是好景不長。慢慢地,不到兩個星期,水里的電纜開始顯示出莫名其妙的痛苦跡象。傳輸的信號開始變成亂碼,最終徹底癱瘓,什么都收發不了了。公司董事們萬分悲痛地宣告電纜患上了某種未知的“水下疾病”,已經無可挽救。
它堅持了15天。這是一次失敗。新誕生的“超級大陸”現在又分裂了,又變成了兩塊。而大海贏了。公眾萬分失望,官方也無比沮喪,于是在之后8年里沒再鋪設電纜。但最終,那些堅持信念的人說服了大家。1866年,布魯內爾的新巨輪“大東方”號,從破產和閑置中被召來,征用為電纜鋪設船。盡管有8年的技術進步,它還是遭遇了一些困難——但是最終,它駛入了紐芬蘭一個有可愛名字的小村莊——哈茨康滕特,“它身后拖著一串2000英里的‘鎖鏈,只為將舊世界連接到新世界”。
成功了。電纜表現完美,來自伯克郡的菲爾德先生,雖然由于美國人的身份而不能像其他人一樣被維多利亞女王授予爵位,但是很快被英國媒體取了個“電纜爵士”的綽號。他的創造很快就獲得了巨大成功,取得了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以至于在接下來的10年里,海底,不管南方北方,都交織起了細密的電纜之網。第一條電纜鋪好之后4個星期,第二條也鋪上了。到1900年時已經有了15條,包括阿根廷和巴西之間的電纜。歐美兩洲之間的交流——每一個歐洲國家和每一座美國城市之間,南方與北方之間——幾乎變成了一瞬時的事,然后漸漸被人們習以為常。
(摘自化學工業出版社《大西洋的故事》 ?作者:[英]西蒙.溫徹斯特 ? 譯者:梁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