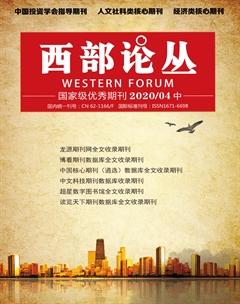體育賽事直播著作權保護的困境和出路
李力衡
摘 要:體育賽事直播節目能否構成《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雖說大部分的學者、法院都達成了基本的共識,但是仍然存在不少的爭議。這些爭議由于《著作權法》規定的不夠詳盡,一直無法得到實質性的解決。《著作權法》目前也在進行第三次修訂,體育賽事直播節目的性質能否在此次修訂中得到明確,如果明確又將如何認定其性質,成為了學界關注的熱點。
關鍵詞:體育賽事;體育賽事直播;著作權;鄰接權
一、體育賽事和體育賽事節目的概念和區別
1、基本概念
體育賽事是包括組織者召集參賽者和組織比賽活動的過程,比如CBA籃球賽、中超足球賽等賽事本身就屬于體育賽事的范疇。體育賽事節目是由制作者制作的以體育賽事為內容的節目,以體育賽事為基礎,綜合了專業的拍攝、編導、剪輯、解說、采訪等一系列的過程。體育賽事節目中又包含了常規體育賽事節目和體育賽事直播節目,前者一般需要通過后期的剪輯在節目中非即時性播放,而后者一般都是以直播的形式即時傳播,在活動進行的過程中,加入了解說、評論、回放、特寫等內容,制作和播出同時進行。
2、二者在著作權上的區別
對于體育賽事,目前學界的普遍觀點都認為“競技無版權”,即體育賽事本身并不受《著作權法》保護,因為體育賽事既沒有在《著作權法》中被明確規定為“作品”,也不滿足《著作權法》中對于“作品”的獨創性要求,因而不能作為作品得到著作權保護。但是也有一部分學者主張將體育賽事分為競技性和藝術性兩類,對于競技性體育賽事,因其達不到獨創性要求,所以不受著作權法保護,而對于藝術性體育賽事,例如藝術體操、花樣滑冰等項目,它們主要表現的是技術動作的美感或者藝術價值,有著對于“美”的追求,因此這一類賽事本身可以達到獨創性的標準,因而是可以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的。
而對于體育賽事節目,學界和司法界就有許多的爭議了。不可否認,雖然大部分人都認同體育賽事節目應當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但是應當根據哪一個條款進行保護,就眾說紛紜了。具體的爭議將在后文中體現,此處不再贅述。
二、我國近年來相關案例的司法判例對體育賽事直播節目的性質認定
筆者查閱了近10年來的相關判決共7件,其中審理法院將案涉節目定性為錄像制品的案件5件,定性為作品的案件1件,還有1件審理法院雖然沒有給案涉節目定性,但是承認了案涉節目擁有著作權權利,受到《著作權法》保護[1]。
可以發現,目前大部分法院在審理該類案件的時候都認為體育賽事節目無法構成《著作權法》中的作品,只能作為錄像制品保護其信息網絡傳播權,其裁判理由大致如下:
涉案賽事節目受賽事本身的客觀性、賽事直播的實時性、對直播團隊的水準的要求、觀眾的需求等客觀因素限制,使奧運會賽事節目所呈現的連續畫面在素材選擇方面難以有太多個性化選擇,而在對素材的拍攝、對被攝畫面的選擇及編排等方面的個性化選擇空間也相當有限。電視導播從大量的圖像、攝像角度和特技效果進行選擇、編排,有一定智力成果的投入,但其所體現的獨創性,尚不足以達到我國著作權法所規定的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的高度。
而將涉案節目認定為作品的法院,裁判理由如下:
從賽事的轉播、制作的整體層面上看,賽事的轉播、制作是通過設置不確定的數臺或數十臺或數幾十臺固定的、不固定的錄制設備作為基礎進行拍攝錄制,形成用戶、觀眾看到的最終畫面,但固定的機位并不代表形成固定的畫面。用戶看到的畫面,與賽事現場并不完全一致、也非完全同步。這說明了其轉播的制作程序,不僅僅包括對賽事的錄制,還包括回看的播放、比賽及球員的特寫、場內與場外、球員與觀眾,全場與局部的畫面,以及配有的全場點評和解說。而上述的畫面的形成,是編導通過對鏡頭的選取,即對多臺設備拍攝的多個鏡頭的選擇、編排的結果。而這個過程,不同的機位設置、不同的畫面取舍、編排、剪切等多種手段,會導致不同的最終畫面,或者說不同的賽事編導,會呈現不同的賽事畫面。就此,盡管法律上沒有規定獨創性的標準,但應當認為對賽事錄制鏡頭的選擇、編排,形成可供觀賞的新的畫面,無疑是一種創作性勞動,且該創作性從不同的選擇、不同的制作,會產生不同的畫面效果恰恰反映了其獨創性。即賽事錄制形成的畫面,構成我國著作權法對作品獨創性的要求,應當認定為作品。
在學界和實務界,主要的觀點分為兩個流派:“作品說”和“制品說”。
1、作品說:
一部分學者認為,體育賽事直播是通過有選擇地對現場表演、人物、動作的拍攝,并經過現場解說、并且配以字幕之后形成的節目,應該被歸類于“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2];一部分學者認為,雖然體育賽事直播的制作無法像電影一樣復雜,沒有辦法達到電影的獨創性,但是由于其拍攝手法、機位、導播選取畫面的專業性,加上現場解說和字幕,也達到了國際上對于視聽作品的獨創性要求,因此體育賽事直播應當作為視聽作品保護[3];還有少數學者認為,體育賽事直播是一個經過選擇、編排、剪切、播出等環節所形成的的有機整體畫面,應當將其定性為匯編作品進行保護[4]。
2、制品說:
制品說是目前大部分學者和實務界的觀點,就如前述判決理由中所寫,體育賽事直播的獨創性受到了客觀因素的太多限制,并沒有辦法達到《著作權法》中對于作品的獨創性要求,觀眾在對何種時間看到何種角度拍攝的畫面有著較為穩定的預期,體育賽事直播的制作者也只能既定的程序和規劃進行一場賽事的直播[5],因此不能將體育賽事認定為作品,只能將其認定為錄像制品,保護其信息網絡傳播權。
除此之外,許多法院在進行案件審理時,都會一并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內容對案件進行裁判,這也是學界比較流行的觀點。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的理由有三:一、盜播者和權利人大多都是同類從業者,二者之間具有競爭關系;二、盜播者通過播放、投放廣告等行為,形成了一定的觀眾群和市場格局,產生了一定的市場效應;三、盜播者的盜播行為對權利人的合法權益造成了損害,同時破壞了市場秩序。基于以上三個理由,盜播者的行為已經構成了不正當競爭行為,應當受到《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規制,在適用《著作權法》的同時一并適用或者在無法適用《著作權法》的時候單獨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都可以更好的保護權利人的合法權益。
三、我國體育賽事直播的保護困境
1、體育賽事直播節目的著作權保護困境
由于我國在《著作權法》立法時采用了二分法的立法方式,將著作權和鄰接權加以區分,因此我國和大陸法系的國家一樣,對于作品的獨創性,有著比英美法系更高的要求。正如前文所述,學界和司法實務界的絕大部分人士都認為體育賽事節目的獨創性達不到我國《著作權法》的要求,因而無法按照“作品”給予體育賽事節目以著作權保護,只能作為“錄像制品”給予其鄰接權保護。
2、體育賽事節目的鄰接權保護困境
目前學界和司法實務界大多都是將體育賽事直播節目作為錄像制品基于鄰接權予以保護,但是作為錄像制品,鄰接權也無法完美地契合并且保護到體育賽事直播節目。在我國目前的法律體系下,錄像制作者所擁有的信息網絡傳播權只能保護交互式傳播行為,而“盜播”這一行為在司法實踐中更多地被定性為非交互式傳播,這就意味著,錄像制作者對自己的信息網絡傳播權進行保護的主張將無法被法院支持[6]。
而如果以廣播組織者的轉播權對體育賽事直播節目進行保護的話,又存在主體上的瑕疵。根據《保護表演者、錄音制品制作者和廣播組織的國際公約》(又稱《羅馬公約》)的相關規定,轉播是指一個廣播組織對于另一個廣播組織的節目信號進行同步廣播,而我國立法也基本上沿襲了《羅馬公約》的立法規則,根據我國《著作權法》中關于廣播組織權的相關規定,我們可以發現,我國《著作權法》將廣播組織限定為了廣播電臺和電視臺。由此可見,一旦直播和盜播有一個行為是通過互聯網進行的,則將無法構成“轉播”這一概念,自然而然也無法受到廣播組織權的保護。
四、我國體育賽事直播節目保護的出路
1、對于廣播組織權的完善
正如前文所述,目前學界、司法界大部分人都認為體育賽事直播節目達不到《著作權法》的獨創性要求,因而無法成為作品,也無法獲得著作權保護,對此,筆者持相同的觀點。既然通過著作權保護的路走不通,那就只能通過其他方法對其進行保護。筆者認為,與完善錄音錄像制作者權相比,對于廣播組織權的修改和完善更不失為一條捷徑和目前《著作權法》體系下的最優選。
隨著時代的推進,互聯網早已經成為了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雖說我國在廣播組織權的規定上基本沿襲了《羅馬公約》的規定,但是由于《羅馬公約》簽訂時的技術條件的限制,也無法通過互聯網對于直播信號進行傳播。而當科技發展到如今,互聯網對于各種節目、信號的傳播起到了比廣播電臺、電視臺更大的作用,因此,將互聯網傳播寫進法律規范,是適應時代和科技發展的必經之路[7]。
2、在《著作權法》完成修訂之前,可通過司法解釋、指導案例進行規范
雖說對于《著作權法》日后的修訂,已經有了明確的方向,但是,法律的修改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在法律修訂完成之前的這段時間內,就可以通過最高法院發布司法解釋或指導案例,對于這期間的法律空白進行一定程度上的彌補,也可以一定程度上減少目前司法實踐中出現的同案不同判的現象的發生。
參考文獻
[1] 祝建軍,體育賽事節目的性質及保護方法[J],知識產權,2015(11):27-34.
[2] 戎朝,互聯網時代下的體育賽事轉播保護“兼評”新浪訴鳳凰網中超聯賽著作權侵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J].電子知識產權,2015(9):14-19
[3] 盧海君,論體育賽事節目的著作權法地位[J].社會科學,2015(2):98-105
[4] 叢立先,體育賽事直播節目的版權問題析論[J].中國版權,2015(4):9-12
[5] 游凱杰,著作權法體系下體育賽事直播畫面的權利保護[J].武漢體育學院學報,2019(02):55-59
[6] 姚鶴徽,論體育賽事類節目法律保護制度的缺陷與完善[J],體育科學,2015(05):10-16
[7] 趙杰宏 馬洪,賽事直播節目網絡盜播的規制困境與出路[J],武漢體育學院學報,2019(03):3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