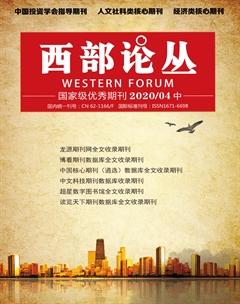組織法則中的“義利之辨”
周其
“義利之辨”是中國傳統管理哲學中的核心命題之一,其爭論的焦點在于“義”與“利”何者在組織法則的制定中起決定性作用。
“義”者宜也,意為事物本應有的狀態,在實踐中表現為一種絕對的道德律,并對個人所承擔的責任與義務作出明確規定。當“義”成為組織法則時,道義與使命感便成為組織成員行為的深層驅動力;“利”泛指物質利益,滿足自身物質層面欲求、追求收益最大化是以“利”為組織法則的特征。總體來看,“利”追求物質層面需求的滿足,而“義”則重視非物質層面的追求,但“義”與“利”并非絕對對立的矛盾關系,在具體管理實踐中領導者應根據組織實際情況進行權衡。
組織法則首先服務于組織目的,并體現組織的深層價值追求。“義”以道德規范組織成員行為,并強調個體的責任感與使命感,在這種價值導向下,組織成員將自己視作整體中的一部分,因而樂于分享和奉獻自我,因此適用于公益性質的社會組織中,無論是紅十字、“希望工程”或是教師、醫生等公益性職務都以造福他人、服務社會作為自我實現的主要途徑。此外在宗教組織中,同樣表現出“義”為原則的組織法則,維持成員信仰穩定性的根本依據在于對宗教價值觀念的認同,因此無論是佛教、基督教或是伊斯蘭教的教義中都包含了對應群體所具有的“先天道德”內容,而組織成員依據這些“義”的部分行事便是對教義的自覺遵循,無形中強化了宗教的權威性。“利”以物質利益為最高追求,而這種價值導向會引發組織整體對效用的追求,伴隨現代工業文明的建立,科學管理主義應運而生,科學管理專注于提升組織內部運行效率,降低管理成本,以實現組織整體利益的最大化。而西方國家盛行的“效用論”即以總體效用作為行為評價標準的理念同樣是“利”取向下建立起的組織法則。相較于“義”而言,“利”更適用于強調效益的企業、工廠、金融等社會組織中。
組織法則是組織運行所遵循的基本邏輯,并決定了組織成員之間的相互關系。“義”將道義作為最高標準,要求組織行為必須符合價值和道德規范,因而組織整體運行穩定有序,而身處其中的個體因組織制度的穩定性與道德法則的教化,能夠與其他組織成員建立持久、和諧的社會關系,組織自身與組織成員之間表現為系統與要素之間互相依存、共同發展的關系。在具體組織行為中,對于矛盾同一性的追求高于斗爭性,“和合”成為組織追求的最高目標。“利”則傾向于將組織內部成員的關系“物化”為一種經濟關系,物質利益構成維系人際關系的根本依據和組織價值判斷的邏輯所在,而對于有限物質利益的無限欲求必然會最終導向組織內部矛盾的激化,矛盾的斗爭性成為矛盾主要方面。斗爭性在組織中表現為雙刃劍,一方面能夠激發個體不斷競爭、發展的行為,使組織內部形成積極進取的文化氛圍;另一方面又異化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使組織成員之間互相敵對和斗爭,構成極大內耗的同時也帶來心理層面的焦慮等隱性問題。組織內部逐利性的另一影響在于增速了人員的流動性和制度變更的頻率,在自由市場環境下,逐利性會使資源自動向資本靠攏,而缺乏資源的組織往往難以留住人才;而人才的流動又使制度需要應對不同的群體進行頻繁的變更,這不利于維持制度自身的穩定和權威。
“義利之辨”對組織法則的影響同樣體現在組織制度構建上。“義”所依據的是道德的力量,需要組織成員能夠自發自覺的遵守組織規范,以道義約束自身行為,因此與之配套的組織制度就會接近于傳統社會中“禮”的模式,以柔性的、非強制的規范提倡和鼓勵符合道義的行為,批判錯誤的行為與價值觀念,但往往缺乏強制性的制約手段,組織制度能否順利施行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組織成員自身的個人修養,因而建立在此基礎上的組織對于人性的預設也是傾向于樂觀和向善的。而“利”以“利益至上”的法則構建組織內部關系,能否保障自身利益不受侵害便成為行為是否正當的評價依據。而要實現對自身利益的保護需要有強制性的手段與制度,因此“利”所對應的組織制度更接近于“法”的性質,具有強制執行力,對于哪些行為應被禁止作出明確規定,并對違反“法”的行為具有相應的懲戒措施,因而“法”本身也相較于“禮”更具有“效力”。
以“義利之辨”為導向,組織內部同樣可能演變分化出不同的決策模式。在“義”的觀念中,每個個體都共同承擔相應的組織責任與使命,而依據權責對應的組織原則,以“義”為基礎建立的組織會更傾向于權力的扁平化和民主化,決策的民主可使更多組織成員參與決策進程中,從而強化其責任意識形成良性循環;而在“利”為主導的組織中,為保障自身利益的同時謀求更多物質財富,必然會依據所處利益地位和所擁有的財富資源進行層級的劃分,且層級之間隔閡不可逾越,越居于高層的管理者會越強調自身權威并集中管理的職能,因為所擁有的權力會直接影響到自身所占有的物質利益。
最后“義利之辨”會體現在組織的分配制度層面。以“義”為取向的組織會注重分配的公平性,因為公平本身就是“義”所包含的,孔子說“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均”是使組織內部成員能與組織目標保持一致性,同時緩和組織內部矛盾、維持良好人際關系的基本前提和保障;而在“利”為主導向的組織中,分配制度往往會呈現“兩極分化”的趨勢,擁有越多資源和財富的人享有越大的權力,因而能夠占據更多的組織財富份額;而具有越少財富的人在組織內部的地位就越低。作為領導者既要重視“義”所包含的公平,避免組織內部的兩極分化,保障組織成員的基本權利不受侵害;同時也要遵循市場經濟下的基本分配規律,實行按勞分配,鼓勵成員多勞多得。
總結來說,“義”重視穩定、公平,在人際關系中表現為“和”,在行為規范上表現為“道義至上”,鼓勵分享與奉獻,具有“利他性”;而“利”重視效率與收益,推崇競爭性的社會關系,以效益作為行為價值評價的唯一標準,傾向于“自利”。當一個組織需要維持穩定時,“義”具有更高的價值導向性;而當一個組織缺乏活力或亟需改革時,“利”能夠提供更大的發展動力。“義利之辨”的核心不在于價值觀念的絕對的對或錯,而在于如何合理的運用與權衡,而這正是領導者能夠充分發揮自身領導藝術的地方。